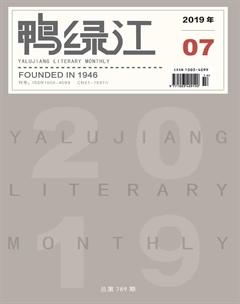風從花里過來香
張萬忠
應關嶺縣縣委宣傳部及關嶺縣文聯之邀,安順文藝界一行十人今早(2018年11月12日)驅車于八點三十許趕到了關嶺縣委黨校。要參加的是一場難得的文學講座。他們有幸請到的是我國著名散文作家史小溪先生。
講座九點開始。這位年事稍長的作家精神矍鑠,比較溫和。穿戴屬“返樸歸真”型。典型的陜北純樸味。幾句寒暄幾句謙遜后,開始進入主題——關于散文創作的靈魂。他普通話的確不夠好。好在我對語言有天的敏感,基本能自動“銜接”他講的核心要義。老作家畢竟閱歷豐富,加之有很好的文學素養,所以盡管普通話差強人意,但傳遞的內容還是相當有含金量和感染力的。
我個人特別贊同他關于散文“重情”的觀點。一篇散文,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打動,還想打動別人是自欺欺人;當然,他也強調文采,散文失去了文采,便不成其為散文。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美。這是他隨口朗誦的。還有,地域文化是生于斯長于斯的作家們應該特別關注的。正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那種不接地氣的純粹抽象文學、想象文學,最終也是空中樓閣,早晚要成為孤魂野鬼的。
但今天最打動我的不是這些精彩的寫作內容,而是老作家的幾度落淚…
老作家在談及選材要有深度的時候,復述了一篇優秀散文的主要內容,說的是一農村母親故事——這位母親幾十里山路給在縣城讀重點高中的兒子徒步送飯,順便用零錢買了幾個桃子給兒子。她看著兒子吃飯,傻笑著;她穿的又臟又破,蓬頭垢面,還有一股難言的臭味。盡管同學們投來鄙夷甚至嘲笑的目光,但這個懂事的兒子沒有半點嫌棄母親的神色。他的任何一個細微動作,都包含著對自己母親的由衷愛戴和尊重。這顯然是倫常中最優美的一道風景、是人性中最溫潤澄澈的一束迷人光輝、更是天地萬物間最撩撥柔軟心魂的眼眸。母親問兒子桃子好不好吃,兒子說,又脆又甜,估計是山上的野桃,好吃極了!
母親聽完后又傻傻的笑了。笑的特別開心。
那一刻,人們無法知道這位母親原來是一位神經失常的女性。
母親和往常一樣,又神情呆滯的趕往了回家的路上……
第二天,這位兒子接到從老家打來的電話,問她母親是否來過學校,說村里已不見他的母親。聰明的兒子立刻感到事有不妙,于是立刻請假回鄉,和同族鄉人一起尋找失蹤的母親……
找了幾天,終于在離村不遠的一座大山上發現了母親的尸體,此時已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不難揣測,這位母親聽兒子說野桃子又脆又香,且她也親自看到兒子吃得那樣甜美開心,于是回家途中,這位母親神經質般的跑入了山中……她死的大山上果然零星有些野桃樹。為了摘那棵斜長在懸崖上的桃樹果子,不慎跌下了懸崖……
人們抬眼看,那棵桃樹上的桃子果然又大又紅……母親臨死前眼睛仍然眼睜睜的看著懸崖上的桃樹……
史先生復述到這兒,終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摘下了眼鏡,用手背去擦拭眼角滲出的淚水……
這一幕,讓我潸然淚下。老人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文人,他定然是那個用心、用情、用愛、且是大愛去關注生命及靈魂的人。他對弱勢群體、對邊緣人群對“失常”的“善良”有著強烈的人文感知。我覺得,他才是用自己的純粹、良知,甚至脆弱去詮釋文學旨意的人。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過度物質化的消費時代,也有人概括為娛樂至死的時代,在崇高抑于低谷、美德驅于邊緣、純粹掩于紛亂的時候,堅持與守望顯得更加可貴和重要。”這是史先生2011年主編《中國西部散文精選》“內容簡介”里的話。我想,史先生這里所“堅持”的自是人文世界里的那份良知道義以及對純文學追尋的那份持之以恒;所“守望”的自是靈魂世界里的那份尊嚴與瑰麗。
任何浮躁的時代都有一批力挽狂瀾的文化引領者,都有一批高瞻遠矚的有識之士。他們注定會大聲呼吁、極力倡導。這些文化引領者骨子里承載著文化傳播的使命,有著深厚的人文積淀和對現行文化扭曲變異的極度敏感;他們語言內核所傳遞出的應是對個體心靈的熨帖。他們注定會關照這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沉重當下;注定會讓更多的心魂虔誠反思,沉淀過濾,進而讓他們通過熏陶、通過感染、通過感動去尋覓一方真正屬于自己生命意義的綠洲。
遺憾的是,每次講座,都會有部分人提出講座者的所謂的“不足”。是的,不足肯定有,所謂“金無足赤”,又怎能去苛求?很多文學愛好者常常會在一點上發生誤解,他們把作家視為完人、超人。其實,作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才對,他們只不過是用靈魂在行走罷了。 從這位資深的前輩作家身上,我完好的窺探到了他豐足的靈魂世界。
這位老作家在講臺上紅紅濕濕的眼睛,是一所佛門的進口吧,不然,臺下怎么一下子少了人們幾世的浮華和焦躁呢?高貴者的眼淚是良知世界的絕代風華。
此時,關嶺黨校里政令瀟瀟的氛圍仿佛化作了“水從石邊流出冷,風從花里過來香”的詩境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