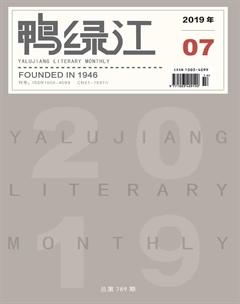淺析《童子問》中的“道”與“性”
錢曉彤
摘要:《童子問》是日本江戶時代古義學開創者伊藤仁齋的代表作,是以童子和師父的問答形式闡釋其思想的儒家書籍。“性、道、教”是儒學的重要概念,仁齋批判朱子學輕易地遠離日常人倫,反對將“道”與“性”本末倒置,強調“道循人性之自然”。本文從《童子問》中的“道”與“性”的關系出發,進一步探究伊藤仁齋的儒學思想。
關鍵詞:《童子問》;伊藤仁齋;道;性
日本近世儒學源自于室町時代五山禪僧的宋學研究,到了德川時代,歷代將軍對于朱子學者的重用使得儒家學說興盛起來。古學是江戶時代否定朱子學說的一派,伊藤仁齋開創的古義學是其中之一,主張追求實踐躬行。《童子問》是伊藤仁齋的代表作,是以童子和師父的問答形式簡明易懂的闡釋自己思想的儒家書籍。《童子問》大致成書于元祿六年(1693年),直至去世前仁齋持續對此書加以修訂,可以說此書為伊藤仁齋的晚年儒學思想的集大成之書。“性、道、教”是儒學的重要概念,伊藤仁齋在《童子問》中說道“夫性道教三者。實學問之綱領。凡聖人千言萬語。雖不堪其多。然莫不總括於此。”,本文從《童子問》中的“道”與“性”的關系出發,進一步探究伊藤仁齋的儒學思想。
何為性?朱子學觀點為“性即理也”。仁齋激烈地批判道“宋儒之説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又曰。性即理也。然不能以一理斷天下之事。”“若程朱論天道。專以理斷之。可謂殺卻天道也。”《童子問》中可以看到仁齋對“性”的清晰定義:“夫性者。天之賦予於我。而人人所固有。”強調“性”原本就是天所給予的,每個人各自持有的東西。簡言之,“性”與“理”不同,不是萬物的本體,是人生來所具有的性質。
由于仁齋與朱子學對“性”的理解存在差異,兩者對于“性”與“道”的本末的理解自然也產生了分歧。在仁齋的觀點中,“道”為最上,“教”次之,“性”是接受“教”的基礎。正如前文所述,“性”是人生來所具有的性質。仁齋說“若不論循性與否。則無以見道之邪正。故中庸先舉性而言耳。非以性貴於道也。”《中庸》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篇,最先列舉出“性”,并不意味著“性”比“道”尊貴,仁齋列舉的順序雖然與《中庸》不同,但內里是一樣的。《童子問》中,仁齋對“道、教、性”的順序有如下見解。
道至矣大矣。固不待論。然不能使人為聖賢。所謂非道弘人。是也。其所以使人為聖為賢。開來學而致太平者。皆教之功也。所謂人能弘道。是也。故道為上。教次之。然而使人之性。頑然無智。如雞犬然。則雖有百聖賢。不能使其教而之善。惟其善。固其曉道受教。不啻若地道之敏樹。故性不可不貴。此性道教之別也。漢宋儒先。多以此顛倒錯說。
首先,仁齋認為“道”毋庸置疑是最上的。然而,“道”并不能使人變為圣賢。要使人變為圣賢,啟蒙有志于學習之人并且創造太平之世的話,“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道”為最上,“教”次之。然而,僅僅依靠“教”,是很難培養出賢人和圣人的。人生來的性質如果像雞犬一般的頑固又愚鈍,即使有百名圣賢也不能引導他走入向善的道路。《中庸》言“人道敏政、地道敏樹”,人生來性善,所以才能明白“道”為何物,受“教”才有顯著的成效。所以,“道”是至大至上的,“性”是追究“道”并且接受“教”的基礎。如若按朱子學的“性即理”的觀點,“理”是上天賦予萬物的固有存在,成了比“道”更加尊貴的存在,明顯顛倒了順序。仁齋的觀點中,《中庸》的“性、道、教”的順序僅僅是展開邏輯說明的順序,并不是價值觀的順序。仁齋在《童子問》說“本與中庸之理無異。但注家錯說耳。”仁齋的“道、教、性”排序與《中庸》的道理并沒有相悖的地方,錯在宋學者的注釋說明。
仁齋認為“聖人之道。本循人性之自然。而不相離。非若諸子百家之自私用智。而遠人倫日用。以爲道也。”,批判諸子百家輕易地遠離日常人倫。又說“茍循人之性。不可得而離。則為道。否則非道。”“若不論循性與否。則無以見道之邪正。”強調“道循人性之自然”。仁齋在《童子問》中說道“道者何。在父子謂之親。君臣謂之義。朋友謂之信。昆第謂之序。朋友謂之信。”可見,在仁齋的觀點中,“道”充斥于日常人倫之中。諸子把自己的學說當做正道,不去論“循性”這一要素,這是他們成為異端的理由。倘若一個人遵循自己生來具有的“性”并且保持不與“性”相離,這便是“道”,反之,則不是“道”。所以,圣人之道不是與“性”相離而獨立的東西,也不是“循性”而生出的東西。
朱子的《中庸章句》對于“率性謂之道”的理解是“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所謂道也。”朱子學主張“性即理”,認為“性”是萬物的本體。人與物各自遵循其性之自然,日常生活中便會存在各自應該走的“道”。也就是說“道”是從“性”生出的東西,“性”為本“道”為末。在仁齋看來,這是本末倒置的誤說。“性”是人生來具有的東西。“道”應是天下皆有,無處不在的東西。仁齋在《童子問》中說道,“有人則有性。無人則無性。道者不待有人與無人。本來自有之物。滿於天地。徹於人倫。無時不然。無處不在。豈容謂待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後有之耶。”“道”是本來就存在的,“道”滿于天地且徹于人倫,絕不是后于“性”而產生的。所以說,朱子學的以“性”為本“道”為“末”是本末倒置的說法。
總結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朱子學與仁齋在“道”與“性”之間的不同觀點。朱子學認為,“性”是“理”是萬物的本體,“道”由“性”衍生而來。“性”的價值比“道”更高,如果保持自己的“性”并且行動的話,自然有應走之“道”存在。仁齋則認為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仁齋認為《中庸》開篇“性、道、教”的順序僅僅是邏輯說明的順序而非價值的順序,諸子按自己的理解實則曲解了《中庸》的本義。在仁齋的觀點中,“道”為最上,“教”次之,“性”是接受“教”的基礎。“道”滿于天地且徹于人倫,“道”不是由“性”產出的,不能脫離“性”而存在,“道”必須遵循“性”之自然。
參考文獻
[1]高山 校注《大學 中庸》(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
[2]家永三郎、清水茂 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97近世思想家文集》(巖波書店 1978)
[3]陳戌國 校注《四書校注》(岳麓書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