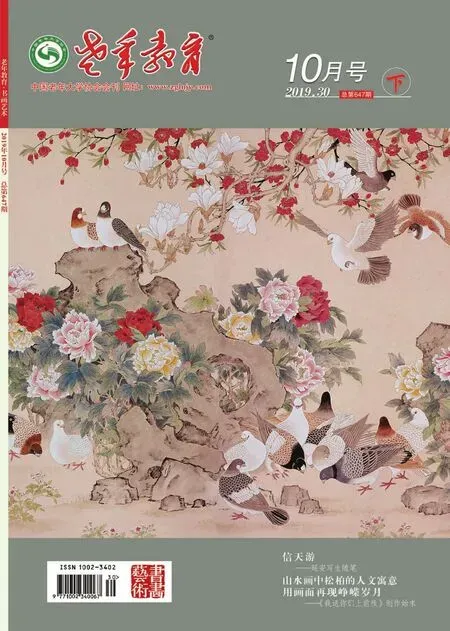折射出理念輝光的圖式
——解讀謝振甌的繪畫
□胡敬德

《絲綢之路》之二 謝振甌
謝振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舉家遷往西安,在那里待了七年,是西北文化積淀的吸引,還是審美理想中漢唐情結的驅使,我們無法簡單地給出回答。但是這人生和藝術途徑的選擇,至少透露了他的取向和視域的獨特。他的一系列歷史題材的作品多半產自這個時期,這些畫奠定了其作為畫家的堅實基礎并填補了中國當代重大歷史題材創作的空當,給予歷史畫以“歷史性”。
《絲綢之路》《長安西市圖》《大唐伎樂圖》等等的出現,就是他對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必要的張力存在,以及這張力對中華民族活力的激活和文明提升的證悟。進而,他又把體悟推向東西方文明之間必要張力的錯落處。我以為,這樣的追求就是對道性的向往。作為藝術的“道”,它在包含普遍性的同時又無條件地要求絕對的獨特性,這就是某一獨特的藝術語言能稱為有意味的形式而決不可任意搬用的原因所在。
“畫家最終還是要回到案頭上來的”,這是謝振甌經常提到的一句話。說“最終還是要回到”說明有一個前段蓄積,這便是對生活場景、生活意識和具體語境的體悟和把握,這是創作欲望和精神力量的來源和依托。例如,他幾番去寧夏西海固探尋“蕭關”,事前他翻閱了大量的圖文資料,并就歷史事件、人物、時間等方面做了卡片、畫了有關創作的草稿,但正式的創作卻遲遲沒有開始,似乎最關鍵的一把開啟創作的密鑰一直沒有到手。于是,他踏上西北的長旅。當他終于查找到了古“蕭關”的遺址時,狂喜難言,空曠千年的歷史時空的通感一陣陣襲來,苦苦尋找的某種圖式的結構和隱喻的精神指涉如種子植入心田。
我曾經看見謝振甌抱著厚厚的《中國絲綢史》,很認真地品讀出土的古代絲綢的紋式。后來通過《錦繡文章》系列,才發現他的用意。畫家希望通過不同文明交合產生的精神性象征符號傳達以下信息:中華文明與邊緣異質文明的交手,孕育出新的價值理念、注入新的血液、生出新的力量。此外,我還想指出:圖案紋飾在謝振甌的創作中有一個漸顯突出的過程。實際上,他前期的創作如《絲綢之路》《大唐伎樂圖》,已經廣泛地在地毯、帷幕、氈蓋、旌旗等畫面物象中運用了圖案紋飾,不過它們純粹是烘托真實場景的手段。到了《山川河岳》系列,圖案紋飾的作用就不同了,它們的繪畫語言感被凸顯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是對形式語言及其精神內涵“驀然回首”的發現。

《山川河岳》之一 謝振甌

《杜工部麗人行詩意》 謝振甌
一個畫家在藝術上的衍變,不能僅僅看作“文本”意義上的推進。它毋寧說是有銳度的生命在體驗了歷史和現實的無限內涵后,人生境界浸染了蒼涼與雄健、廣闊與通透、深邃與自由的一種見證吧。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審美理念的確立,統攝了傳統和現代視覺藝術的種種手法,轉化歷史文化構件并孕育出新的圖式語言,讓精心構出的圖式折射出理念的光輝,這就是我眼中的中國畫家謝振甌。

謝振甌,1944年生,浙江溫州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工筆畫學會副會長、廈門大學藝術學院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其作品曾獲第五屆全國美展銀獎、第六屆全國美展金獎,出版有《謝振甌——唐人詩意圖》《中國美術家檔案——謝振甌卷》《錦繡文章——謝振甌工筆畫精選》《絲綢之路繪事錄》《絲綢之路經行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