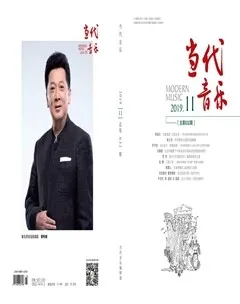卡巴列夫斯基《二十四首前奏曲》的俄羅斯民族音樂特性分析
摘要
本文以20世紀蘇聯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鋼琴作品《二十四首前奏曲》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作品中所呈現出的俄羅斯民族音樂特性,從作品創作背景的角度,逐一探討了音樂形象、和弦結構、樂句結構、節拍等方面的特點,并對此曲給予音樂創作上的啟示進行了說明。
[關鍵詞]卡巴列夫斯基;《二十四首前奏曲》;俄羅斯;民間音樂;特性
[中圖分類號]J6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9)11-0014-02
收稿日期2019-07-19
作者簡介(范佳寧(1992—),女,下諾夫哥羅德國立格林卡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下諾夫哥羅德603000)
卡巴列夫斯基(1904—1987)是前蘇聯著名作曲家、鋼琴家,在20世紀鋼琴音樂創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其生活的年代看,20世紀正是西方音樂走向多元化發展的時代,特別是現代音樂的發展給予古典音樂很大的沖擊,最為明顯的就是體現在創作技法上。卡氏在最初的鋼琴音樂創作如《第一鋼琴協奏曲》等就具有現代主義特征,但是由于受到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卡氏的創作傾向于社會現實主義發展,而民族性特征成為他的音樂核心風格。鋼琴作品《二十四首前奏曲》(Op38)創作于1943年,由于其創作背景的原因,在這部作品中表現出了卡氏鋼琴音樂的民族性傾向,并充分體現出了俄羅斯民間音樂的特性,因此本文以此部作品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俄羅斯民族音樂元素在作品中的體現。
一、《二十四首前奏曲》的創作背景
前奏曲作為一種音樂體裁,其前身為16—17世紀器樂組曲的第一首,具有引子的形式,從17世紀末開始,前奏曲成為一種獨立體裁,從巴洛克時期開始,很多音樂家都非常關注這一體裁的運用與發展,如巴赫的《前奏曲與賦格》,浪漫主義時期肖邦、李斯特等人創作的鋼琴前奏曲等,都是音樂史上的經典作品。卡巴列夫斯基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賦予了前奏曲更為深刻的含義和民族主義特色,其創作背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歷史背景,主要是受到俄羅斯民族樂派的影響。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強力集團”為代表的民族樂派開啟了俄羅斯民族音樂的發展道路,他們深受歐洲各國浪漫主義音樂的影響,從俄羅斯音樂發展的角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于是在創作中結合俄羅斯民間文學、民歌、民間舞蹈創作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樂作品,這為20世紀俄羅斯民族主義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二是時代背景。有兩條主線:其一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象主義音樂、十二音音樂的發展,打破了西方音樂的古典常規,完成了從調性音樂向無調性音樂、古典音樂向現代音樂的嬗變,多元化、現代性成為這一時期音樂發展的主流;其二則是從當時蘇聯的社會背景看,40年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蘇聯政府號召音樂家們要從政治因素的角度用音樂來表現和歌頌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從社會現實主義的角度進行創作,因此民族性的音樂表現再次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度。由此卡氏的《二十四首前奏曲》正是承接歷史、順應時代的一部充滿民族性的鋼琴作品。
二、俄羅斯民歌旋律的音樂形象表達
俄羅斯地域寬廣,民族構成復雜,各民族在長期的生存繁衍中,產生了眾多的民間歌曲。也正是在這種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俄羅斯民歌在體裁、風格等方面都異常豐富,也決定了音樂形象的多元化特點。3所謂音樂形象,指的是以音響為載體,表現出相對獨立性的音樂內容和情感,音樂形象可以細化人的形象、事物的形象等不同的方面,在民歌中,則主要是以旋律作為依托和表現手段,以此來展現出獨特的俄羅斯民族精神氣質。以作品中的第20首《c小調前奏曲》為例,此曲的原型為一首復樂段民歌,表現了一位俄羅斯少女不幸的婚姻,整體節奏慢板、情緒壓抑,采用小調式寫成。作曲家為了能夠保持原民歌的風格特點,運用了主調織體的聲部手法,上聲部以單音旋律表現民歌主題,突出線條感,下聲部采用柱式和弦與和弦音的結合為伴奏,襯托主旋律的發展,在c小調上進行,表現了少女對自己不幸婚姻的一種輕嘆和訴求,由此可以看出,此曲基本上再現了原民歌的風格特點,同時對音樂形象也進行了深入的刻畫。作品第十五首《降D大調前奏曲》是一首明快、詼諧的樂曲,表現人們在豐收的季節中愉快勞動的心情,充滿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原民歌為中板,4/4拍,采用C大調寫成,以四分音型與八分音型的結合作為節奏組合,具有較強的律動性。作曲家在借鑒原民歌風格的基礎上,采用了明快的小快板速度,2/2拍,在降D大調上進行,為了能夠把這種積極向上的音樂形象和情感表現出來,使旋律在降D調的高音區呈現,歡快的節奏與高音區明亮的音色相結合,勾畫出了一番充滿和諧與歡快的勞動場景。
三、多元化和弦結構的民間調式音階基礎
和弦是構成和聲的基礎,從浪漫主義時期音樂發展的角度看,在前期由于受到古典主義音樂的影響,屬于調性音樂時期,和聲的進行突出功能性和弦的運用,到了中期及以后,西方音樂的發展最為明顯的標志就是在和聲的變化上,注重半音化和弦與非功能性和弦的運用,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和聲效果。4在《二十四首前奏曲》這部作品中,在和聲風格上呈現出兩種特征:一是在調式基礎上的傳統和聲運用,這二十四首作品都屬于調性作品,具有古典主義時期以來的共性音樂特征,因此在調性音樂背景下,其和聲具有傳統性,這也就是決定了和弦在結構方面的共性特點;二是從時代背景上看,這部作品同樣受到了20世紀和聲發展戰的影響,具有和聲的現代性,因此決定了和弦結構方面的個性特點,這種共性與個性的結合構筑了和弦結構的多元化。在這部作品中,多元化和弦結構與調式音階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同時又與俄羅斯民間音樂和調式音階特征有著共通性。以《D大調前奏曲》為例,此曲的主題建立在D大調上,其調式音階為自然大調七聲音階,因此為了能夠明確調性,采用了常規的三度疊置和弦,強調了功能性和弦的運用,和聲進行為Ⅰ/D-Ⅳ/D-V/D-SⅡ/D-V/D,最后以和聲的半終止結束。在俄羅斯民間音樂中,無論是民歌還是舞曲,在大調的運用上以自然音階為主,這就決定了在和聲的運用上突出大調功能性和弦的運用;無獨有偶,在小調樂曲中,則突出升七級音的表現,注重升七級音的導七和弦到主和弦的進行,如在《g小調前奏曲》中,以升F音為根音的導七和弦與轉為和弦隨處可見,這與俄羅斯民間音樂中的和聲小調因素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四、非對稱特點的樂句結構與節拍變化
俄羅斯民間音樂在結構上最為明顯的特點就是樂句結構的非對稱性,在樂句結構上常以三、五、七小節作為結構基礎,這也是與中國民間音樂在結構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二十四首前奏曲》中,很多樂曲的樂句結構都呈現出這種非對稱的結構特點,以《e小調前奏曲》為例,樂曲開始部分的主題由三個樂句構成,樂句的結構為7+7+3,其中第一樂句為3+4小節,即三個小節為動機,四個小節為旋律的發展,第二樂句也是3+4小節的結構與第一樂句表現為呈遞關系,可以看出,這兩個樂句都是以三小節動機作為旋律發展基礎的。這種非對稱樂句結構非常容易造成節奏、節拍上的不規則變化。如《g小調前奏曲》的中段部分,其節拍為2/4與3/4的交替拍子,在2/4拍子的小節中,由于十六分音符的符尾相連,改變了原來的拍子律動規律,在下一小節中就造成了重音位置的變化,形成3/4拍子的重音效果。因此可以看出,非對稱樂句結構是對俄羅斯民間音樂特點的繼承,由此而產生的節拍變化則體現出對俄羅斯民族音樂的發展和運用。
五、對俄羅斯民族樂派音樂元素的模仿
在19世紀60年代之前,在俄羅斯盛行的音樂主要是以歐洲音樂為主,以“強力集團”為代表的民族樂派的音樂創作為俄羅斯民族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后柴可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拉赫瑪尼諾夫等人的創作為20世紀俄羅斯民族音樂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從《二十四首前奏曲》中就能夠看出作曲家對俄羅斯民族樂派作曲家作品的借鑒和間接運用。如《D大調前奏曲》在以層次化的聲部交叉與對比和八度旋律的運用與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中的“基輔大門”一曲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兩者在風格上都體現出輝煌宏偉的效果。《B大調前奏曲》中引用的民歌旋律與普羅科菲耶夫的《大提琴奏鳴曲》第二樂章所引用的民歌旋律幾乎相同,其區別在于前者的樂句結構變化較為豐富。在《降e小調前奏曲》中,整體音樂處于一種無窮動的進行狀態中,尤其是強調小調半音階的級進與模進的反復進行,這種創作手法非常明顯地參考了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的《野蜂飛舞》一曲,具有高度的模仿效果。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卡巴列夫斯基的鋼琴曲《二十四首前奏曲》在音樂創作上呈現出了明顯的俄羅斯民間音樂特色,尤其是在音樂形象、和弦結構、樂句結構、節拍變化這幾個方面有著明顯的體現;其次就是從民族性的角度看,除了以上在音樂特點方面的體現外,此曲在創作上還參考了19世紀60年代以來俄羅斯民族樂派的創作特點,體現出了對俄羅斯民族樂派的傳承與發展。因此從此部作品的意義上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啟示:一是在音樂創作上要堅持走民族性的發展道路,民間音樂是作曲家創作思維的源泉,它為作曲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音樂材料,無論是采用哪種創作手法或者音樂體裁,堅持民族性都是音樂創作的生命力所在;二是在創作中堅持民族性的同時,還需要考慮到時代性,在這部作品中體現出的是作曲家的社會現實主義思想,這與當時蘇聯的現實狀況是相吻合的,而作品中所具有的20世紀音樂創作手法,也是音樂創作時代性的具體表現。由此通過以上兩點可以看出,只有堅持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發展道路,才能體現傳統、創造經典。
注釋:
1(#牛藝臻.卡巴列夫斯基《24首鋼琴前奏曲》和聲形態特點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19(05):49—50.
2王婕斯.卡巴列夫斯基《二十四首前奏曲》及其調式形態J.人民音樂,2011(06):81—83.
3陳國威.卡巴列夫斯基前奏曲Op.38,No.1解析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09(03):24—27.
4龔迅.卡巴列夫斯基鋼琴作品的和聲語言探討J.音樂探索(四川音樂學院學報),2006(S2):26—32.
(責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