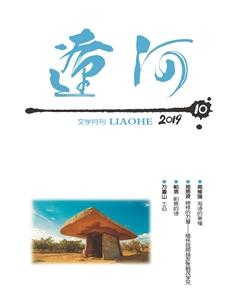翻看一塊泥土
閆耀明
黃昏
我在已經收割了的田地的邊緣走過,手里拎著一把彎鐮。
我不知道自己走路的樣子像不像一個正統的農民,因為田地里的農活我幾乎沒有干過。但是,我有一顆敬畏土地的心,正如眼前這正在降臨的黃昏,讓我無法忽視。
黃昏的村子是最美的,那是我的靈魂棲息的地方。我拎著彎鐮走進村街,先后與一條黃狗、三只回家的母雞、一群排著隊扭來扭去的鴨子相遇。在這些小生靈面前我很有禮貌,我的臉上呈現出的是愿意與它們共同分享黃昏的美好的表情,真誠而親切。
娘正在灶間做飯,巨大的蒸汽一團一團地從鍋蓋下擠出來,迅速地在灶間彌漫。我把手里的彎鐮掛在墻壁上。我看到不大的一面墻上已經掛有一只籮筐、一頂草帽、一把亮閃閃的鋸子、一張落著塵埃的蛛網,還有娘深深的咳嗽聲。
灶堂里的火正在燃燒,娘的臉便被耀得明明亮亮的,無比生動。
我想幫助娘做些什么,可我伸不上手。
放眼望向院子和村街,只見黃昏正抖著碩大的暗色長衫無邊無際地降臨,將整個小村罩得嚴嚴實實,如同母親摟著自己心疼的孩子。
娘還在忙碌,我無言地站著。蒸汽一涌一涌的,讓整個屋子以及黃昏都忍不住搖晃起來。
獨坐河邊
夜晚的每一個細節,都是那么的細膩而安詳。秋蟲在起勁兒地歌唱,秋月的清輝溫柔地灑落在村莊,河水流得無聲無息,仿佛是怕打擾了誰。
我一個人,坐在女兒河邊。靜靜地坐著,竟然驚起了許許多多的往事,鳥兒一樣紛紛起飛,撲棱棱拍打著前額。這讓我小小地吃了一驚。
我從小村走出去,走到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常常為自己見了世面而沾沾自喜。這不是壞事情,一切都那么平常、自然,就像眼前這細膩而安詳的鄉村夜晚。
現在,我獨自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故鄉的河邊,安靜地回想那些往事。往事紛繁,讓我的經歷漸漸膨脹、豐滿。然而,我心里仍然隱隱地覺得,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無論我走到哪里,故鄉,總是在我心里裝著。
因為,故鄉,是我一生都無法割舍的寶貝啊!
我放長目光,望見小村里的點點燈火正眼睛一樣看著我,平靜而溫暖。
當我獨坐河邊,在心里默默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驚喜地發現,我的文字正在一深一淺地呼吸,與小村的脈搏相吻合,一點不差。
玉米茬
玉米被農人掰下來了,玉米桿也被農人割下來了。它們都被農人用大車拉走了。
剩下的,就是玉米茬了。
這枯萎的生命,個子矮矮的,靜默地站著,站在空蕩蕩的田野里。
它是在回味曾經的輝煌嗎?
它是在炫耀為農人奉獻的果實嗎?
它是在感嘆時光的飛逝嗎?
它是在獨自默默地憂傷嗎?
我說不清。我無法了解玉米茬那低矮的心事。此時我就走在已經收割完的田地里,看著玉米茬,看著這雖然低矮卻依然堅定站立的莊稼的根。我看到我是這片田地里的第一高度,玉米茬的高度只及我的腳踝。可我的心,卻對玉米茬充滿了敬畏。
陽光明朗朗地照著,風在淡淡地吹著,我靜靜地站著。玉米茬,正將自己小小的心事藏進泥土里,藏進風兒吹不到的地方,藏進秋天的最深處。
無人關注的玉米茬是低矮的,卻可以詮釋生命的艱辛歷程,可以讓風雨擁有高度,可以讓黃土更厚實,可以讓農人的期盼落地生根。
奔跑
男孩子去上學,出門才發現風正在刮。刮起來的風并不是一股一股地吹過來,而是一片一片地涌,很有一種劈頭蓋臉的味道。
男孩子走出村街,走到女兒河邊。他看到河水已經被風刮得泛起一長串一長串的波浪,像姐姐的麻花辮子。
向學校走,男孩子走得很急。他好像不習慣在風中行走。走著的時候他還聽到了聲音。那是一種很陌生的聲音,沉沉的,悶悶的,帶著讓人心緊的氣勢。男孩子的心真的緊了起來,回頭看。
他只看到河面很寬,河灘很開闊,目光所及之處一個人影也沒有,甚至連一只鴨、一條狗、一只鳥兒也沒有。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大了,而他,正處在世界的正中央。
男孩子有點害怕了,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走的速度。
后來,他干脆奔跑了起來。書包并不太重,在他的屁股上一下一下地顛著,好像有人在嬉笑著拍打他的屁股。
男孩子越跑越快,厚厚的棉衣使得他的汗水變得澀重而尖銳。他死死地咬著嘴唇,不讓自己的嘴巴張開。
那個奔跑的男孩子已經長大了,現在他正走出村街,走到女兒河邊。他看到河水已經被風刮得泛起一長串一長串的波浪,像姐姐的麻花辮子。
回憶完這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已經長大的男孩子的心開始急跳。他奔跑起來,像男孩子那樣奔跑起來。
我知道自己奔跑的樣子很認真,雖然步子已經有些拖沓。我出汗了,實在跑不動了。我仍在努力堅持著。
只是,我早已經咬不住自己的嘴唇,我早已經淚流滿面。
樹林
女兒河邊的樹林靜靜地站著,那么像我守望的母親。
遠遠的,我望著那片樹林,恍惚中仿佛看到一個鄉村少年在林子里走來走去。對于少年來說,那片林子就是個安靜的世界,如天堂一般,讓少年的心事可以靜靜棲落。
樹林里的靜謐讓少年驚訝,少年的每一個心事都是在樹林中想清楚的。這里也是少年盡情玩耍的好地方,藏貓貓,捉秋蟬,躺在草地上瞇起眼睛透過樹的枝葉望斑駁的天空,望那細碎的深藍。這一切都是那樣愜意,那樣舒坦。天堂一樣的樹林讓少年的心變得安靜而溫柔。
少年常常是坐在樹下,將脊背倚靠在粗大的樹干上,在陽光暖暖的撫摸下沉沉睡去,醒來時少年意識到,樹林的懷抱是如此的巨大而溫暖,那么像自己的母親。
把樹林當作母親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呀!這幸福降臨得是那么的猝不及防,讓少年站在樹林里,良久無言。
那個迷戀天堂般的樹林的鄉村少年就是我。許多年過去了,我的母親早已去世,而樹林猶在。當我重新站在這片樹林前的時候,隱藏于內心深處的記憶便水鳥兒一樣紛紛起飛,讓我的心一下一下地溫暖,溫暖得眼睛里情不自禁地盈滿了淚水。
向日葵
我固執地以為,向日葵的顏色,就是我家鄉的顏色。
那圓圓的花朵那么像爹得意時微笑的模樣。
向日葵一生勤勞,一心向往光亮,這讓懵懂的我們覺得既有趣,又新奇。
于是,我和小伙伴們在樹林一樣的向日葵中穿行時總是小心翼翼,我們都在盼著秋天,盼著品嘗向日葵帶給我們的歡樂和對身體的滋養。
在那個生活清苦的年代,果腹之欲總是那么頑強地在我們的眼前搖晃,像一股股吹來拂去的風,揮之不去。我們這些淘氣的鄉村少年曾躲過大人的監視,偷偷采來嫩嫩的茄子,也曾匍匐于紅薯地邊,扒開土層,弄幾根比拇指粗不了多少的紅薯吃。我從不把嘴饞視為缺點,那種樸素的愿望支配著我們去做那些讓大人頭疼的事。
然而,惟一例外的是,我們從不打向日葵的主意,即使向日葵已經成熟了,在沒有正式收割之前,我們一下都不去碰。
這讓大人們很不解。就是我們自己,也一下子說不清,只是依稀覺得有些東西是應該珍惜的。
多年后當我行走在家鄉的田野邊時,當我與依舊燦爛著的向日葵面對面時,我猛地想到,這悠然開放著的金燦燦的花朵,早已將我過于清貧的童年映照得一片明亮。
我暗自慶幸自己在童年的時候就與向日葵相識,我暗自慶幸自己的家鄉能擁有向日葵的顏色。
年事
年的腳步踩著北方滿地的雪,“咯吱咯吱”地響著,一路走來,響到了小村的街。
鞭炮聲比馬兒打出的響鼻更為清脆、喜慶,讓小村紅火得比姐的嫁妝還要鮮亮。孩子們美滋滋地穿上了花花綠綠的新衣服,在街上跑呀跳呀,追逐著鞭炮的聲響。老人們樂呵呵燙起了醉人的熱酒,即使西北風吹得再大,也擋不住小村人迎春的腳步。在小村,沒有人懷疑,年是那一陣響過一陣的鞭炮喚來的。
年來了,光放鞭炮是不夠的,家家戶戶還要貼窗花。有了窗花,喜慶的氣氛才更濃一層。于是,最忙碌的,便是六嬸了,家家的窗花都是她親手剪出來的。那把小小的剪刀,從白天忙到夜晚,不辭辛勞地加班。
加班也高興呢。因為六嬸是大方的,可以賣錢的剪紙,今天就白送啦。讓每一戶人家的窗子都貼滿喜慶,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呀!
三叔也很風光,他請來了鄉里的秧歌隊,一路吹吹打打,從前街扭到后街。村里人追著秧歌隊,個個臉上洋溢著喜悅。秧歌隊的表演也不含糊,旱船推得左右搖擺,蝴蝶舞得上下翻飛,彩扇搖得連天空都跟著打顫。整個小村呀,喜慶而紅艷,像喝了一壺燙得滾熱的高粱酒。村里人也不客套,更沒有向三叔道謝。他們理解三叔的心思。三叔這個種糧大戶,連鄉長都給他送來大紅的喜報呢。
春聯是一定要貼的,而且要在年三十的上午貼在屋門邊。雞窩前要貼“金雞滿架”,豬棚上要貼“肥豬滿圈”,糧囤上要倒貼“福”字。那紅色的春聯,既是一年收成給小村人帶來的喜悅,更是小村人對新一年的祝福與憧憬。
放鞭炮、剪窗花、扭秧歌、貼春聯,把小村人的心情打扮得花枝招展,也讓年變得越來越豐滿。
寫毛筆字的任務,六嬸就指名讓我來寫。六嬸說:“大侄兒在城里工作,有文化,會寫水筆字。”
墨研好了,散著年的香味兒;紙裁好了,紅紅的,溢著年的喜慶。可我拿著毛筆的手,卻忍不住發抖,仿佛全村人的心事,都在我的手里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