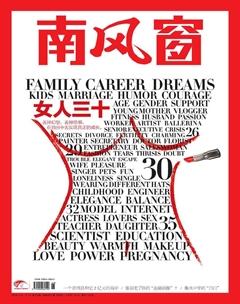女人三十,別怕
董可馨

將到而立之年的第一批90后,是怎么快要吃完青春飯的?關于“青春末端”這類詞匯的文章標題,最近被頻繁地推送在我們眼前。
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熱衷于提醒人在意自己的年齡。
販賣焦慮是這個時代的惡習。但媒體不是焦慮的源頭。
知識分子、體制內工作者、農民工、自由職業者、企業職員、個體經營者,無論生活軌跡相距多遠,所有人終將在三十歲相遇,共享籠罩于頭頂的巨大不安。
與其說年齡形成了這團不安,毋寧說年齡是一條繩索,一記推手,將現代人的結構性困境收攏、擠壓,將人生必得平衡的沖突、解決的矛盾推到當事人面前。
三十歲有什么特別的?并非真老,也不真嫩,離一切塵埃落定的四十歲尚有時日,又確實告別了明媚執著的二十歲,人到了此時大多要開始面臨并正視人生中的重大問題,不安和焦慮集中爆發,而爆發的烈度在當下的中國尤甚。
而三十歲的女人所受到的擠壓遠比男人劇烈。
結構性困境
如今概括女人三十,并不想當然的那么容易。
自從中國女性一步步從家庭、宗族、計劃體制中釋放出來,個人化選擇獲得了理直氣壯的正當性,三十歲的女人,就再難以描摹出同一副面孔。
但與這般年齡的女性談論人生后,我發現,盡管在家庭背景、經濟條件、社會身份、知識氣質的不同排列組合下,每個人的故事各不相同,感悟卻是相似的。
依舊單身的體制內工作者、新婚的企業職員、剛生下寶寶的中學老師,她們來到了(或說被逼到了)相同的境地,一個必須要做出選擇的境地。家庭與事業、生育與奮斗、互斥的生理角色與社會角色就在天平兩端,無論向哪邊加碼,都不能再忽視或拖延下去,盡管選擇一方并不以全然犧牲另一方為代價,但天平必須傾斜。
很多人相信,功能即責任,生育與否,即使在可以容納多元的今天,也沒有被輕易劃入女性的個人選擇范圍,它依然有著一種普遍的社會期待(不少人會說,否則上帝干嗎讓女人生孩子呢)。在這種期待下,有利于生育的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仍主導著對女性的評價系統。
所以,整容業和美妝業為女性而繁榮,溫柔賢惠是女性的專屬KPI。
各城市的相親公園也是一例。在這里,男女雙方都是商品,但男性的價值公式和女性的價值公式顯然不同,學歷、工作是共通的加分項,但女性的價值公式里,年齡前的負系數一定更高。
當我與一位29歲的友人通電話,談到年齡對心態的改變時,她突然提高音量,反復強調了三次:“皺紋啊!皺紋啊!皺紋啊!”
但一位同齡的男性,則驕傲地把胡子蓄到了聞一多的量級。
同樣代表著年歲增長,女人的皺紋和男人的胡子,一個帶來焦慮,一個象征成熟。
弗洛伊德老師有句名言 :“生理結構就是命運。”以生理差異為表征的結構性沖突,無論中西,都是支配女性焦慮的核心矛盾。
之所以說它是表征,是因為結構性矛盾雖然往往以兩性差別的形式表現,但卻未必是生理差異本身造成的。
同樣代表著年歲增長,女人的皺紋和男人的胡子,一個帶來焦慮,一個象征成熟。
達沃斯論壇每年會發布一份《全球性別差距報告》,評估各國女性在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政治賦權以及健康生存狀況四個維度上相對男性的大概情況。可能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即使在女性已廣泛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國,2018年該指數在世界范圍內的排名也只有103,無論是女性收入、工作時間收入比、職業機會,都與男性相差甚遠。
性別不平等本身倒并不直接導致困境焦慮,因為在古代不平等同樣存在,也沒見有人對這種社會結構提出異議。所謂困境,只是現代的產物。現代革命使女性從各種依附性關系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同時作為權利和義務的工作,但因為生育角色和不平等的存在,女性又無法公平獲得作為權利和義務的工作。
對此經典總結可以是:正是自由了的女性需要平等參與社會分工與實際社會機會又無法滿足女性需要之間的矛盾,造就了女性的困境。
這個矛盾又是如何而來的?現代之后,一波波女性主義研究者試圖給出答案,男性、父權制、資本主義等。
舉兩個經典的代表。
存在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暫且貼上標簽)波伏娃認為,他者性質是女性困境的根源。在兩性關系中,男人是自由的、自我決定的存在,而女性是他者,是被決定的。作為他者的女性對作為自我的男性是威脅,因此,欲保持自由的男人要使女人屈從于自己。
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則跳出性別框架,認為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合謀,一起壓迫著女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原本可以成為女性作為人的完整性之資源的各種因素—一切事物 (工作、性和游戲),一切人 (家庭、朋友)—都反過來分裂著女性。
為啥花費筆墨討論性別理論,女人三十,若作為一種困境來理解,首先是女人的困境,而以上,直指問題的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與《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的數據可作為理解理論的一種參考。30年前,中國城鎮就業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77.5%,在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和資本要素后,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與之并存的另一結果是,女性收入與男性收入的差距卻不斷拉大,到了2010年,女性工資只有男性的65.8%。前述2018年中國在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排名103,而在2008年是57,之間十年連續下降。
這是為什么?
時間變了
“女人三十”的話題本不新鮮,如前所述,對現代女性來說,三十歲本就是生理角色和社會角色集中沖突的時候。那為什么我們今天還要來討論?
因為新的變化發生了。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一個是人對年齡的實際感知,一個是對年齡的心理評價。
先看對年齡的感知。
我們總拿孔子的“三十而立”說事,孔子這話本是對男人講的,意思是男人到了三十歲,該立身、立業、立家了,但現在三十歲的男人還自認是“黃金單身漢”呢。
同樣的,在古代,女人至多十幾歲就成家了,三十多歲可能已經有了孫輩。可現代,女性因為普遍接受教育,參與社會工作,結婚年齡大大推后。江蘇省民政廳的數據,2017年江蘇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甚至已經到了34.3歲,三十歲可是女人風韻正盛的時候。
這說明什么?在社會迭代演進的過程中,時間的含義,以及人對時間和年齡的感知,都在變化,而且這個變化還在加速持續,因為不斷有新的催化劑加進來。
我們對心理年齡的說法不陌生,一個人的實際生理年齡、心智成熟度和社會化程度,以及他對自己年齡的感知與判斷未必處于相同水平。
舉一個例子,明星易烊千璽只有19歲,但他的言談表現,遠遠超出我們所理解的19歲少年“該有的樣子”。另一個大多數人恐怕都會承認的直觀感受是,現在的孩子似乎比自己小時候早熟多了。
這不是一個孩子變好了或變壞了的問題,而是現代技術社會改變了社會時間后帶來的客觀結果。
解釋起來不難。借用媒體文化研究者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的觀察,社會時間變化的關鍵節點在電子媒介產生時。在這之前,兒童要經過識字教育,通過系統閱讀才能掌握知識、邁向成年,可是電子媒介瓦解了書本對信息的壟斷,兒童可以輕易通過網絡接觸到海量信息,通過圖片和視頻看到成人世界真實的、暗黑的那一面,因此童年與成人之間的界限也就此模糊了。為什么現在的十幾歲孩子聊起天來像大人一樣,因為他們真的什么都懂。
少年見識了成人世界,可真的會敬畏并喜歡嗎?
可現在,年輕人雖然沒有政治經濟權力,但是掌握著互聯網啊。其中誰最活躍?不是被工作和家庭拖累的三十一代,而是那些沒錢卻有閑的學生黨。
在此刻的中國,你可以看到基本代表社會文化的網絡空間里,那些關乎中老年的詞匯是如何被使用的。無論“大媽”還是“中年油膩大叔”,都指向一種無法明言,又意有所指,所指非善,且意味深長的調侃與嘲諷。
本來也是,少年視角下,“大媽”“大叔”并沒有作出什么好表率,他們所代表的成人世界實在毫無吸引力,也無怪被少年鄙夷、逃避、反抗。
事情不止這么簡單,“大媽”“大叔”們的年代,知識和技術更新沒有像現在這么快,他們過去憑借經驗和知識具有的優勢在今日已大大喪失,很難對晚輩作出有效指導,在很多方面,年紀小的倒是年紀長的老師。
年紀小的倒也當仁不讓,古代社會“尊老敬長”的傳統早就被不斷的革命和運動顛覆了,肇始于五四又被激進革命所定義的現代氣質深植于中國社會之中,年輕人所代表的反叛、進步、求新、求變,正面又強勢。這一切的一切加起來,讓“越小=越好”。
分析至此,好像仍有說不通的地方。
想想看,十年前、二十年前,80后、90后是怎么被頻頻唱衰為“垮掉的一代”的,那時候的年長一代,似乎也能在輿論上對年輕人形成一定“碾壓”之勢。但現在,鮮有對00后的集體不滿。
一個重要的變化在于,形塑社會文化的主要力量改變了。哪怕在十年前,社會文化在相當程度上也還是由傳統媒體所影響并塑造的,話語權還攥在年長者手里。
可現在,年輕人雖然沒有政治經濟權力,但是掌握著互聯網啊。其中誰最活躍?不是被工作和家庭拖累的三十一代,而是那些沒錢卻有閑的學生黨。
就在90后自以為依然可以驕傲地和00后并肩調侃“大”字輩時,殊不知冷箭早從背后射來,他們也被打入了“老年宮”。原來,已經不是友軍了!
年輕人主導著網絡,也就塑造著社會文化,干預著其中人對自己的心理評價。網絡流行語過去看不懂沒關系,投之以不屑和鄙棄就好了,如今不懂,怕是不敢輕易張嘴,生怕被人家嫌棄過時。
這種漩渦式的社會文化已經擴大、蔓延至整個社會,在這個氛圍里,指向負面年齡評價的話語占據著絕對的優勢,生理年齡尚小的人就已開始早早哀嘆人到中年,年齡的緊迫感變得愈發急切。而這種緊迫感傳導到女性那里,只會加倍。
別 怕
似乎很悲觀?不必。
之前說過,女人三十作為一種現代困境,開始于女性從依附性關系中解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女人三十AB面,這一面是困境,那一面,其實是自由。
自由是好東西嗎?是的。
現代的核心特征就是自由,現代人類的進步史也是一部不斷擺脫附著在個體身上的各種權力依附關系的斗爭史。新教改革把信徒從對教會的依附中解放出來,資本主義把農民從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女性權利運動把女人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致力于把人從一切束縛人的關系中解放出來。
可以說,對自由的追尋,造就了現代世界。
但自由也是有AB面的。以上只是自由的A面。
它的B面是,自由作為一種后果,也把現代人都變成了孤獨的個體,須得忍受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所謂的焦慮,主要也是這兩種感受。
所以擁有自由的人也會懼怕自由,為了消除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擁抱歸屬感,人們投向宗教神祇,投向民族主義,投向偉大目標,投向強大權威。這是心理學家弗洛姆的意見,適用于集體,也適用于個體。
對女人來說,自由賦予她們以獲得社會角色,實現獨立的可能。但也把她們拋到了一個必須自己作出選擇的境況之中。最后的結果,一定包括以下兩種。
一種,無法忍受孤獨和焦慮,急著把自己交付出去,以進入一個可以依靠的關系,去消除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大多數沒有經濟能力的女人,就會投向男人。
另一種,不愿以破壞自由和個人完整性為代價與外界相連,她們可能就要面對“大齡剩女”“女漢子”“滅絕師太”的指責。
一個人總要作出選擇,事情也總會有一個結果。糟糕的不是選擇了某一種結果,因為任何一種結果,都會有相應的代價和補償。
女人的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終歸也是人的問題。
真正糟糕的在于,看起來的個人選擇太多地被不健康的社會結構所決定,而是否明白這一點甚至已不重要,因為不論如何,人還是要面對自己,認知調整成功與否,差別只在于是自怨自艾,還是自我欺騙。

至此,稍作總結。自由釋放了女人的社會空間和心理空間,但不健康的社會結構把空間扭曲成了困境。身處自由的困境中,女人又該怎么辦?要么向外尋找支點,要么向內建設自我。
這兩者,并不截然分開,也需要健康互動,彼此成就。但它的前提依然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堅實的自我。對于女人來說,就是先做她自己,然后再是一個妻子,一個員工,一個母親。
電影《少年的你》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在警官鄭易無力對曾遭受霸凌的陳念給予實質性幫助后,他們在車里,陳念獨自念念有詞:
—什么時候才算大人?
—沒有人教給過少年怎么才能長成大人。
熒幕之外呢?無論是高考之后,還是年滿18,還是結婚,答案依然要從自我的成長中去找尋。
三十,別怕,丟掉恐懼,在自由中去實現真正的成長。
說了這么多,好像并不只專門討論女人。因為女人的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終歸也是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