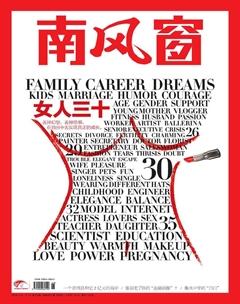哪一種收入差距更值得擔憂?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在每年秋天的第一課,我都會用下面的問題調動學生:在富國當窮人好,還是在窮國當富人好?
這個問題通常會帶來大量沒有結論的爭論。但我們可以把位于收入分布頂端的5%定義為“富”,底端5%定義為“窮”。在典型的富國中,5%最窮的人大約可獲得1%的國民收入。窮國的數據較少,但八九不離十的假設是最富的5%獲得25%的國民收入。
類似地,假設富國和窮國也分別是位于人均收入分布頂部和底部5%的國家。在典型的窮國(如利比里亞和尼日爾),人均收入大約為1000美元,而典型的富國(如瑞士或挪威)人均收入為6.5萬美元。
現在,我們可以計算,窮國的富人收入為5000美元,富國的窮人收入為1.3萬美元。以物質生活水平衡量,富國窮人的境況比窮國富人好一倍多。
這讓我的學生大吃一驚;大部分人認為應該反過來。當他們想到窮國的富裕個體時,心里的形象是生活在莊園里的大亨,有豪華車隊和眾多家丁。但是,這樣的個體固然存在,但每個窮國中代表性的頂端5%個體,可能只是中層政府官僚。
這一比較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強調了國家間收入差異相對于國家內部不平等性的重要性。在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之前,即工業革命以前,全球不平等性幾乎完全來自國家內部不平等性。但隨著19世紀西方步入發達,世界經濟也經歷了工業化“核心”與生產初級商品的“外圍”之間的“大分化”。在二戰后的大部分時期,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了大部分的全球不平等。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兩大趨勢開始改變這一情況。首先,以中國為首,后進地區的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開始顯著快于富國。歷史上首次,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居民以比歐洲和北美居民更快的速度變富。
其次,許多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性開始升高,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監管較少、社會保障較弱的經濟體。美國不平等性急劇升高,美國“窮人”的生活是否比最窮國家的“富人”更高,已成疑問。
從全球不平等性的角度,這兩大趨勢呈現此消彼長之勢。但它們都提高了國家內部不平等性占總不平等性的比重,逆轉了19世紀以來從未被打斷過的觀察趨勢。
由于數據過于零散,我們無法確定國家內部和國家間不平等性分別占當今世界經濟總不平等性的比重。但在一篇基于世界不平等性數據庫的未發表論文中,巴黎經濟學院的盧卡·尚塞爾估算,高達3/4的現有全球不平等性可能來自國家內部不平等性。另兩位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布爾吉翁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指出,自19世紀末以來,國家內部不平等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那么大。
這些估算如果正確的話,就表明世界經濟已經邁過了一個重要的門檻,需要我們修訂政策重點。長期以來,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一直在說,降低全球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快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富國的大同論者—通常是富人和高技能職業人士—占領了道德高地,貶低那些抱怨國內不平等性的人的擔憂。
民粹主義在整個西方崛起的部分原因,便是富國的平等目標與窮國的提高生活水平目標之間的矛盾。發達經濟體與低收入國家貿易的增長,帶來了國內工資不平等。而強調國內平等的發達經濟體的政策,未必會對全球窮人造成傷害,哪怕是在國際貿易中。提高勞動力市場底層收入、消除不安全的經濟政策,對于國內平等和保持世界經濟健康、為貧窮經濟體提供發展機會,都是好事。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權《南風窗》獨家刊發中文版。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貿易直言:對健全世界經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