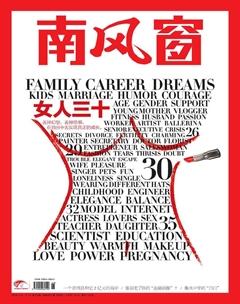江南智造,尋回工業文明的時間鐘擺
譚保羅

“世界時間”的鐘擺
在20世紀,史學界有一個獨領風騷的年鑒學派。和過去的歷史學家相比,這個學派有兩個著名創建,可以說“一橫一縱”。
“橫”是跨學科,研究歷史的大事件,除了探尋事件本身的邏輯和英雄人物的意志之外,還必須將其放置在經濟、社會的宏大背景之下來分析。歷史的颶風,歸根結底起于經濟和社會的青蘋之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順應歷史大潮還是被歷史拋棄,絕非因為一個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基于經濟社會的生機或者潰敗。
“縱”是長時段的歷史觀,審視歷史,不可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將人類社會變遷看作一條長河,每個河段有各自的文明構建任務,從而把人類文明不斷推向更高階段。這個任務你不來完成,總有人來替你完成。學派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世界時間”的概念,這也是該學派最廣為人知的標志性符號。
在世界時間的滴答聲中,人類前進永不停歇,時間不會等待所有民族。因為,總有人趕上世界時間的節奏,成為地球上那兩三點迸發智慧之光,代表同時代最高文明的發達地帶,即世界時間的鐘擺指向了它們。
羅馬、秦漢,以及中國的唐宋曾是文明之光,但鐘擺最終又離開了他們,并重新垂青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進取民族。
13世紀后半程,南宋被蒙古攻滅。從此,鐘擺逐漸偏離中國,指向了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熱那亞。在此后的數百年時間內,工商文明的光輝被播撒到低地國家和英倫三島。當西方工商文明席卷全球,中國卻選擇背對世界,陷入政治經濟的全面停滯。
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在差不多經歷了“失去的600年”之后,中國再次走入“世界時區”。彼時的中國人充滿對工業文明的渴望,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封疆大吏和地方士紳開始全面擁抱近代工業。在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以及京津唐,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工業時代徐徐展開。
1865年,在長三角的心臟地帶上海,江南制造總局(也稱“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或“江南制造局”)創立,每年經費40萬兩白銀,來自淮軍軍費和海關收入。
它是洋務派創辦的最大兵工廠,也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工業企業之一,全面引進了最頂級的普魯士和大不列顛軍工技術。一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軍人依然用它生產的岸防炮和后瞠槍來抵御日本人。
以江南制造總局為代表的洋務工廠,代表了中國人走出農耕,去擁抱工業文明的決心。從此之后,中國人的智慧和企圖心再次對“世界時間”的鐘擺發出了強大的引力。但路很長,長達百年。
與英美體系的“競合”
新中國成立,在蘇聯的援助之下,中國構建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但由于意識形態的全面對抗,全球市場割裂,這個體系并沒有融入全球分工,并不具有國際性競爭力。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很大程度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才真正擁有了與全球同步的工業化。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G2時代到來。
人類前進永不停歇,時間不會等待所有民族。因為,總有人趕上世界時間的節奏,成為地球上那兩三點迸發智慧之光,代表同時代最高文明的發達地帶,即世界時間的鐘擺指向了它們。
但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競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開始超出我們當初的預想。尤其是近年來,一個強大的國際政治經濟集團開始浮出水面,它是“英美體系”。它包含英美加澳等核心國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圈內”之國。它們的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是全球頂級的富人俱樂部。
請注意,“英美體系”絕對不是貨幣戰爭或其他國際政治領域常見的“陰謀論”。它是基于價值認同、地緣政治和產業協作等因素,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利益同盟,并且經過了20世紀后半葉多次國際政經巨變的檢驗。它們利益紐帶很牢固,同盟內部一直都有著不可低估的凝聚力。
和這個體系之間,中國應該繼續“競合”,而不是對抗。因為,英美體系依然是全球工業和科技領域暫時難以挑戰的霸主。不妨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2019年的科學領域諾貝爾獎(除文學獎、和平獎與經濟學獎),幾乎全為美日科學家獲得。另外,有一位來自長期奉行中立主義的瑞士。
拉長歷史,我們更容易發現最近20年,即那段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間通道,但凡那些有著劃時代科技進步意義的諾獎,也絕大多數是英美日的科學家獲得。還必須注意,猶太科學家多數早已融入英美體系。
可以說,這是一個和中華民族同等優秀的群體,產生過牛頓、達爾文、圖靈,還有愛因斯坦、馮諾依曼,他們都是曾經點燃人類文明之光的一流人物。而且,這樣的人物今天依然還在英美體系不斷涌現。
第二個例子:中國是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市場,這讓對公業務增長一度陷入疲軟的華為,得以憑借著國內出貨量而重振雄風。但全球智能手機的“大腦”:安卓和iOS系統,其創新中樞在大洋彼岸。
不管是開放的安卓,還是封閉的iOS,他們并非只是美國人的智慧,而是全球成千上萬最優秀程序員和應用開發者共同的智慧結晶—這剛好體現了英美對全球智慧資源的超強配置和掌控能力。
這些年,華為的互聯網文案和市場營銷愈發出色,但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國產系統依然不是硅谷的對手。
顯然,中國還需要經歷一場范圍更大、影響更深的技術革新,才能真正站在工業和科技的頂峰,與競爭者煮酒論英雄。這是挑戰,也是改革者和創新者的機會。
三重背景下的機遇
人類的工業文明大致經歷過蒸汽、電氣和信息時代。中國以高識字率的勞動人口和穩定的國家治理,擁抱全球化,快速習得了電氣和信息時代早已處于成熟階段的技術和模式。
而現在,競爭格局已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依靠后發優勢,通過外部技術引進,對接“中國市場”和“中國要素”,從而生成一個行業的模式已成為歷史。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工程和精密制造等新興領域,未來的競爭會有三個不可忽視的背景。
一是:多中心創新的可能性。
“世界時間”的鐘擺在13世紀的擺向歐洲之后,全球技術創新的核心發源地是歐洲和后來的北美,這是“單中心”的。而未來,技術原創可能將更趨于“多中心”模式,中國也將成為更多技術的發源地。
以人工智能為例,其底層技術離不開機器學習,而數據是機器學習的“糧食”。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生產地,13億人的消費數據(交易數據)和作為“世界工廠”的工業數據是人工智能天然的深厚土壤。
實際上,在基于消費數據的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已不遑多讓,比如移動支付帶來的金融科技革命;在基于工業數據的工業互聯網等領域,創新也在加碼。位于長三角的杭州和無錫正是這兩大領域的先行者。
二是:積聚和協同的重要性。
當下,中國的產業地帶早已完成初步積聚,北京、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強勢地帶日漸成形。其中,長三角范圍最廣、人口最多,且潛力巨大。兩個數據,足以窺豹一斑:
一是它以全國1/26的土地面積、1/6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5%左右的GDP;二是三省一市(蘇浙滬徽)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32.4%,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22.85件,遠高于全國9.8件的平均水平。
西方的工商文明發軔于自由城邦的獨立,而它的快速發展則得益于區域的積聚與協同。從地中海北岸的工商萌芽,到低地國家和英國的資本主義成熟文明,再到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權力的塑造,以及硅谷對全球信息時代的革命性推動,所有的變革無不是一個基于空間的積聚和協同過程。
從地中海北岸的工商萌芽,到低地國家和英國的資本主義成熟文明,再到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權力的塑造,以及硅谷對全球信息時代的革命性推動,所有的變革無不是一個基于空間的積聚和協同過程。
要素的積聚,產業的協同,將讓財富增長發生神奇的“乘數效應”。在這個意義上講,對高端要素密布、文化認同度極高的長三角來說,現在的富庶還只是一個開始。
三是:政府角色的創新性。
中國經濟的奇跡,很大程度源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改革開放本身,即代表著社會在經歷某些動蕩之后對產權的重新尊重。此外,以中央政府信用作為根基,構建起人民幣為本幣的大國金融體系,并向境外投資者背書,提供一個對資本相對善意,且運行良好的營商環境,這更是中國崛起的“非市場因素”。
“非市場因素”,未來可能更加不可或缺。當創新進入“無人區”,資本和市場的力量很可能勢單力薄,齟齬不前。實際上,互聯網技術最初在美國發軔,乃是源自大國軍備,而非市場競爭需要。因為,電話公司具有自然壟斷屬性,它們根本沒有發明互聯網的商業動力。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未來,公共治理的創新依然將繼續,地區和城市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講,不過是政府治理水平、公共服務供應質量、營商環境改善情況的競爭。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正是中央給予三省一市探索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改革重任。
以上三個背景,在某種意義上講,將決定著長三角經濟未來的走向,也會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它們正是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和“江南智造總局”公眾號要觀察和探索的重點。
作為觀察者,我們將繼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關注新技術的發軔與應用,以及它們會如何重構產業和城市。
作為記錄者,我們將記錄城市、企業和人的故事,記錄新時代的“長三角經驗”,并將其總結歸納,提煉為時代變革的智慧結晶。
作為探索者,我們將和改革者、創新者和勞動者同行,探索新的經驗和模式,用一流的智庫服務,助力長三角一體化和中國經濟的新一輪轉型。
我們必須永遠選擇面向世界,而不是相反。必須從江南繁盛的歷史中走出,懷揣近代化探索者對先進工業文明的敬畏之心和開放姿態,堅定地擁抱全球化,從“制造”到“智造”,在“世界時間”的滴答聲中重新書寫屬于中國人的才智輝煌,創造新的文明高峰。
我們每個人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