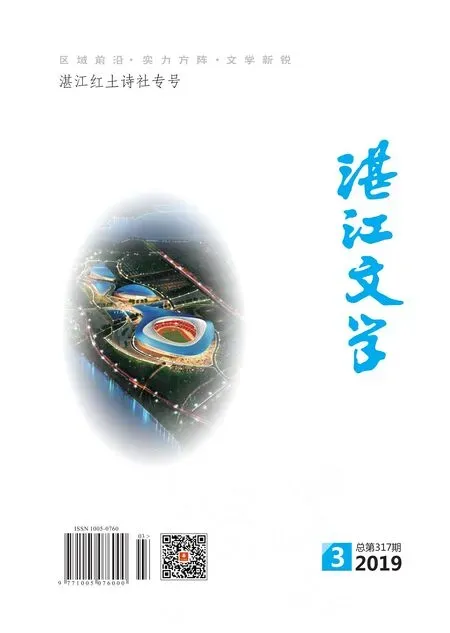饑餓的童年
◎ 吳洪偉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面對滿滿一桌美味佳釀,我跟兒女們聊起那遙遠的童年生活。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時期。那時,我家住在黎明場南朗隊,我童年的生活就是在那里度過的。
與其說南朗山是孩子們的樂園,還不如說是解決饑餓的好去處。每逢仲夏或初秋之際,滿山野果飄香。一樹一樹的山竹,一叢一叢的稔子,茫茫然不著邊際,黃一搭紫一搭,把整個山坡都染成了色彩繽紛的水彩畫。我們一大群山野孩子,像一陣過路的山風,刮向山旮旯,凡是能吃的,見者不拒。待下山來,個個肚子脹如皮球,回家省了許多口糧。但問題來了,第二天一個個光著屁股,呼天搶地憋紅著臉,那拇指般大小的山竹核,沙子似的稔子粒排著隊堵在肛門出不得。母親要來了花生油往屁股上抹,用小樹枝往里撬,出是出來了,肛門皮層組織滲血,囁啊囁,囁了又囁,好幾天收縮不回原形!
釣魚是孩子們的樂事。那年月,肉食的主要來源是向大自然攫取。終于盼到了放假,我們迫不及待地拿著釣桿往山塘河邊里跑。通常,釣得最多的是滄浪魚(俗稱走水佬),鯽魚,有時也有難得一見的白鱔和花星。那天中午,我們下完釣,玩著石子,三哥釣桿上的浮標猛被拉沉。“好家伙!”三哥喜出望外,執桿往上抽,一尾肥碩蠟黃的塘虱凌空而起,掛到了榕樹枝上。三哥個子不高,夠不著,踮起腳跟往上跳,魚是抓到了,食指反倒被釣勾著,哇哇直叫。我們慌忙抱起他,搬來了石塊磚頭墊腳,然后我一溜煙的跑回家。父親呼呼的趕來,剪了線,用單車載著他去農場醫院做手術。魚總算是吃到了,也解了饞,但付出的代價著實不小。
兒女們聽到這里,睜大了眼睛。我叫他們邊吃邊聽,菜都快涼了。
接下來我又講了湛江知青打賭吃白糖餅的鬧劇。
我還依稀記得,那晚天時忒熱,周遭一片黑,南朗山上吹不來一絲兒涼風。同住一室的家偉叔和庚雄叔叫我和阿桶去公里開外的西朗村供銷社買白糖餅。好處是每人一角錢的腳路費,還承諾,如果誰輸了吃不下的白糖餅也歸我們所有。這么大的誘惑,誰能抵擋得住!
比賽開始,家偉叔來勢洶洶,喧聲奪人,咔嚓咔嚓眨下眼十只白糖餅下了肚,接著是一陣咕嚕咕嚕的牛飲,待到二十只時,就像一臺沒了油的推土機失去了馬力,嚼勁松垮了下來,并時不時打著飽嗝,攤坐在板凳床上。而庚雄叔人高馬大,實力雄厚,像廉頗老將尚能飯,二十八只下肚還舔舔嘴唇,一臉的白吃的得意表情。我們站在一旁,眼珠子滴溜溜轉,盯著剩下的白糖餅暗自竊喜。最后,當然是每人分得了四只,拿回家藏在米缸里慢慢地吃。
我在家中排行老五,父母寵著,哥姐們凡事也都依著,自然,父母親割膠留下的夜粥大多是我獨享。記得有一次,二姐從稻田拾遺穗回來,餓得像一團剛搓好的面。她四下里找吃,打開鹽盅,把白花花的鹽粒幻化成香噴噴的米飯,一把把往嘴里送,又是一瓢瓢舀水喝。母親割膠回來,質問鹽哪兒去了,我終是做了“叛徒”,“出賣”了二姐。后來,母親流著淚說:“阿二腌壞腎了。”
兒女們聽到這里緊皺眉頭,百思不得其解。
“二姑媽真的吃了那盅鹽,又喝了半缸水嗎?”
我說:“那年月,餓了什么事情不可以發生,古代有易子而食的故事。你們聽說過寒不擇衣,饑不擇食的成語吧。”
你們知道嗎,那時的農場為了積糞肥,在各個山頭都養著許多牛。我爺爺叫錫友,但大家都喜歡叫他“一公”。他的工作就是住在六號高山看守牛舍。白天趕著牛群在山坡上放牧,傍晚趕著牛群回欄看守。冬夜里,北風嘯嘯,吹得茅屋檐嗚嗚作響,野地山溝狼狗嗥叫,到處結著白白一層霜。爺爺半夜起來,穿著破棉襖,顫巍巍來到牛舍旁生火。但還是有初生的牛犢捱不過冬夜的。爺爺發現后提著煤油燈連夜趕回隊里,叫父親去宰牛。我醒來也鬧著跟去。因為是小牛犢,兩袋煙功夫便弄好煮熟。那牛肉味滲著生姜八角味從鍋中飄出,絲絲縷縷彌漫在低矮的茅房里,哧撲哧撲的肉汁滾沸聲在耳鼓中回響,我忍不住吃了三大碗,撐破肚皮還想要,最后在父親的喝斥聲中停下了碗筷,我撅著小嘴,舔著嘴角,慢慢回味著這肉味的美好。
最爽還是過年吧。年一到,我們就能穿上新衣裳,戴上紅五角星帽,吃著平時難得一吃的肉食。頸都望長了,目光都盼瘦了好幾斤,除夕夜終是到來,我們歡天喜地,臉上蕩漾著幸福的笑容,一種驕傲和自豪感從心底里油然而生。
過年的重頭戲是走親戚,這也是小孩子最渴望的。除了有好吃好睇好玩的外,最關鍵是有利是。
大年初一,父親穿著簇新的解放鞋,唱著紅歌,踩著心愛的“黑加路”,載著我哥弟倆探外婆。大年初二,母親又牽著姐姐,挑著藤蘿竹籃探阿姨姑婆。
那年月,日子過得緊巴,走親戚時,一刀五花肉,一袋煎堆,兩斤木薯餅就算是體面的“三大禮”了。親戚接禮后也拿捏分寸,一刀肉只切一小截,煎堆木薯餅各取小半,回禮時另贈對等的禮品,永遠保持著雙不虧的物質守恒定律。飯飽茶足聊談挨尾時送出村口,又客套一番,你推我讓給孩子派利是,探親接待總算劃上了完滿的句號。這樣,一個正月下來,我們姐弟每人都能領到四、五元的利是,一下子變成了“富翁”,美得好幾晚翻來覆去睡不著。女孩子最愛扮靚,姐姐們用這些錢買了頭花和紅頭繩,扎著羊角辮子戴著花,格外的好看,直到正月十五才舍得摘下來,待明年再戴。而我們這些帶茶壺柄的最貪玩,買來鞭炮,一直燃放到散元宵……
兒女們聽到這里又是一陣的唏噓,望著滿桌子的佳釀美食,似有所悟……
是啊,那饑餓的童年已黃鶴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