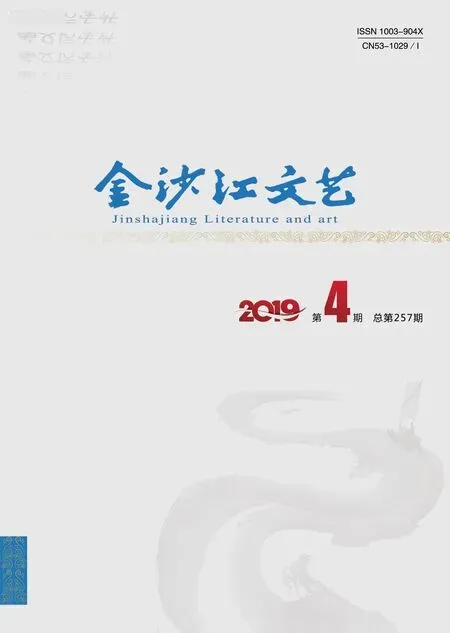鄉(xiāng)路的變遷
2019-11-13 19:35:19郎開喜
金沙江文藝
2019年4期
郎開喜
我的故鄉(xiāng)在一個偏僻的漢、彝、白、苗族聚居的小山村,我家住在村東頭第一家,是村里的東門戶。我家門前一直以來只有一條狹窄的毛毛路通往村外,它便是我們村里的主干道。
小時候我經(jīng)常爬在窗臺上看路上村里來來往往的人群,老氣橫秋的阿公阿婆,爺爺奶奶,下地干活的爸爸媽媽,村里青壯年勞動大軍,披蓑戴笠的叔叔嬸嬸,走親串門的各路鄉(xiāng)親。劁豬的,買雞買蛋的,補鍋的,收廢鐵的,做木活的,換竹籃的,換洋芋的,換豆腐的等等,一天到晚在我家門前這條不到兩米寬的灰土路上來來回回,出出進進,上上下下,煞是熱鬧,成為兒時記憶中的一道抹不去的風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那時人們出行的真實寫照。如果下大雨,全身上下都是泥水。晴天呢,塵土漫天飛,行人路過得捏著鼻子避到路邊田埂上行走,一不小心前仰后翻是常有的事。閉塞的交通成了制約家鄉(xiāng)解決溫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 “瓶頸”。
要想生存,要想脫貧致富,就得修條平刷刷的山區(qū)道路。1974年,我所在的大隊要修一條通往各生產(chǎn)隊的道路,各村各寨積極行動,村民熱情高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乘著月光在各自的路段上甩開臂膀大干起來。那時我讀小學二年級,也去湊熱鬧。晚上挖路光線暗淡,我挖的鋤頭木銷子與鋤頭把連接處脫落了,我又把木銷子捎上,鋤頭把朝下支平,挖土的鋤頭一頭朝上,叫三姐用他的鋤頭使勁敲木銷子。天黑看不清楚,才敲了兩三下,三姐一不小心就敲在我右手大拇指上,頓時就腫起來,紫紅紫黑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