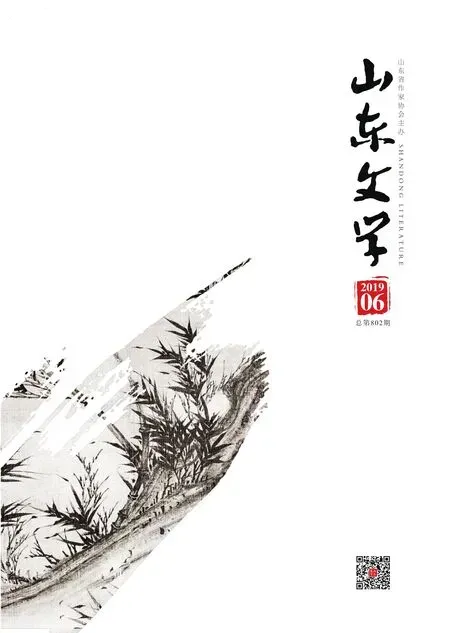風景三章
厲彥林
銀杏王
萬物有靈,樹能成“神”,這樣的樹山東莒縣有一棵。
2018年國慶佳節,我和妻子沒去名山大川,執意去沂蒙山區東部、位于黃海之濱的莒縣浮來山,謁拜那棵被譽為“天下銀杏第一樹”的“銀杏王”。
深秋的沂蒙大地, 秋意漸濃,金風送爽,山川、河流和田野如一幅幅彩色版畫,繽紛斑斕,一派繁忙的豐收景象。
我一直在捫心追問:“為什么中華文明源遠流長5000年,而銀杏王卻頂天立地陪伴4000年?”“為什么2018年9月28日‘至圣先師’孔子誕辰2569年,而銀杏王4000年巋然屹立、依然蓬勃鮮活?”“為什么銀杏王能縱覽‘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親眼目睹亙古未有、翻天覆地的滄桑巨變,成為舉世無雙的生命傳奇?”
馬克思在《中國紀事》中早就指出:“中國是一塊活的化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545頁),進化論奠基人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稱“銀杏樹是‘活化石’”。中華文明5000年、近代中國由衰到盛170年、中國共產黨建黨近100年光輝而曲折的歷程,都儲存鐫刻進浩如煙海的歷史教科書中,能和天宇與大地共鳴、高山與大海合唱、歷史與未來交響,真正活在世上作為見證的“活化石”, “銀杏王”當之無愧!
山不在高,有樹則名。浮來山海拔不足300米,的確不算高,卻因銀杏王蜚聲海內外。站在遠處眺望,整個定林寺被一棵茂盛的銀杏樹所遮掩,它像一把巨型的綠傘,每片樹葉都像小扇子,繁蔭數畝透出深邃與神秘,透出一股仙靈之氣。十時許,我們跨進定林寺的山門。只見銀杏樹周圍石碑林立,詩詞萃集,最顯眼的是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王丙乾題寫的“天下銀杏第一樹”,字體蒼勁渾厚。幾根虬勁粗壯的枝干已用水泥柱子輔助支撐著。那樹圍、樹齡、高度和氣節,實屬罕見,讓人肅然起敬。樹圍就有“七摟八拃一媳婦”、“大八摟、小八摟”的趣聞。屏息抬頭仰望,只見老銀杏峻拔奇崛,稠密的枝椏遮天蔽日,嶙峋斑駁的樹干刻滿滄桑,蓬勃而有力的枝條直插蒼穹、蔭覆廟宇。站在老樹下,身心被樹蔭庇護,伸出手掌接一束透過枝葉棲落、雕鏤人心的陽光,感覺特別珍貴與溫暖。閉上眼睛側耳細聽,分明聽到風吹銀杏葉簌簌的聲音。樹下游人如織,佇立、觀賞、拍照、思考,時而發出驚奇與感慨,流連忘返。攝影愛好者抱著“長槍短炮”紛至沓來,咔!咔!咔!隨手一按快門,眼中的美景被定格成萬千幀永恒。
此樹一年四季,景色各有春秋,美不勝收。尤其是深秋黃葉凋零時,天空猶如無數黃燦燦的蝴蝶飄飛舞動,地面上鋪滿黃葉地毯,唯美驚艷,堪稱奇觀。黝黑粗大的樹干皮上時常能看到幾葉簇一果,這樹老枝干上不長枝條,葉子竟然能直接結果,令游人交口稱奇。萬壽無疆的銀杏樹象征吉祥平安,因而該樹四周的護欄上掛滿了老少婦孺祈福的紅絲帶。這時風吹落了幾片銀杏葉,竟然被一位年長的游客小心翼翼地撿起來,當寶貝收藏了。這狹小的空間,儲藏著老銀杏和劉勰這自然與人文兩大世界級國寶,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當地那位傾盡心血研究這棵銀杏樹的老同志興奮地介紹說:“今年這棵樹長得特別茂盛,至今葉子都沒變黃呀”,“此樹每年都碩果累累,果實既小又圓,味道特別純正”。我一直在追問:“此樹為什么生命力這么旺盛呢?”“從橫空出世的幼苗到長成巨樹,從洪荒蒙昧的遠古時代活到文明開放的新時代,這棵樹到底經歷了什么?”
莒縣是一片歷史悠久、涵養文明的沃土。這地方大約在四五億年前,還是汪洋大海,后隨地殼抬升成為陸地;是三代古國故都,夏代城邑初見端倪,商為姑幕國,周為莒國。莒國立國近700年,在春秋戰國時曾與齊魯并雄。《左傳》中記載:“魯隱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當年會盟就在這株大銀杏樹下,那時這株銀杏已是參天大樹了。遙想當年,狼煙四起,諸侯爭雄,歷史巨輪在亂世浮華中曲折前行。這棵銀杏樹根須深扎沂蒙大地,吸天地靈氣與精華,納大自然神秘之力量,獲得了恒久定力和深厚底氣,個性孤獨且自由高傲。
此樹長的位置就很特別,在浮來山佛來峰、浮來峰、飛來峰三峰鼎峙聚捧的山坳底部,三峰環圍成天然屏障。樹下深土數丈,根扎在石灰巖溶蝕階地上,前臨清泉峽和從不干涸的臥龍泉,土壤深厚,水肥充足,背風向陽,冬暖夏涼,獨特的氣候和環境,能避免雷電和洪水等自然災害的侵擾,因而能龍蟠虎踞,穩如泰山。清康熙年間山東南部的莒縣等地曾經發生過一次巨大的地震。莒縣的災情是“官民房屋、寺廟、牌坊、城垣俱倒,周圍百余里無一存屋”。而銀杏樹面對這場生死考驗卻安然無恙。
銀杏俗稱公孫樹,意思是爺爺植樹孫子輩才能結果,生長緩慢,壽命極長,具有長壽基因,抗病蟲和防腐能力強。銀杏出現在幾億年前,是第四紀冰川運動后遺留下來的裸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遺植物,恐龍滅絕后,銀杏卻歷盡滄桑存活下來,是世界上十分珍貴的樹種,系中國特產。其枝干挺拔、冠如華蓋,枝繁葉茂,全身是寶,是樹木家族的老壽星。我妻子指著“三教堂”院里那棵高大挺拔的銀杏興奮地說:“你看,這棵銀杏1300多歲啦!”我說:“是。但它在定林寺只能稱晚輩了,還不知道是‘銀杏王’的多少代孫了!” 目前,我國百歲以上的古銀杏樹近十萬株,樹齡過千歲的也不計其數。銀杏樹是具有濃厚人文色彩的古老樹種。千百年來中國人崇拜銀杏樹,形成了崇拜銀杏的獨特文化現象,銀杏廣泛被種植在宅院、祠堂、文廟、行道、名勝古跡、園林等。浮來山上這棵銀杏,傳說是西周初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東征時所栽。三百年前的順治七年,莒知州陳全國立碑云:“此樹至今三千余年。”中國人把銀杏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樹,當地人一直把這棵古樹奉若神明,游人和居民連一枝半葉也不敢攀折,怕得罪神靈惹災禍。新中國建立以來,人民政府采取多項措施,重點保護,更使其避免了各種人為的傷害。守護綠色生長的活標本,詮釋生態文明的恒久答案。
當然這古銀杏樹的主干較矮,自小就不被伐木者窺見覬覦,樹又遵循自然天道的法則生長,修煉、修復和保護了自己。
莒縣文化底蘊深厚,為銀杏王提供了豐富的生命營養。莒縣是我國第一批千年古縣,文化燦爛,鐫刻著歷史文化的恒久年輪。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已愈百歲的宋平曾題詞:“莒國文化源遠流長”。莒文化與齊文化、魯文化并稱山東三大文化。浮來山屬莒文化的發源地,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評論家劉勰的校經樓就聞名遐邇。郭沫若親題“教經樓”和“文心亭”。劉勰所著《文心雕龍》,與這棵歷經滄桑的古銀杏同輝共榮。銀杏樹端直、剛勁、生命力強,象征著百折不撓、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據傳,當年孔子過莒之南隅,路遇孩童在路中用土筑城墻,孔子主動下車避讓,并說:“孩子筑的土城也是城呀,理應避讓”。坐北朝南、朱門紅墻的“三教堂”香火興旺,殿堂內供著儒、道、佛三教始祖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塑像,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同堂禮拜,任何人的愿望都能在這里寄托。1929年,中共莒縣第一個黨支部在浮來山校經樓上成立,點燃紅色革命的火種。據了解,當地人把“銀杏王”神靈一樣仰慕敬奉,精心呵護與保護,使其免受天旱、蟲災、雷擊、火燒、人為破壞等天災人禍。抗日戰爭時期有西方商人,曾想花巨資購買回國展覽。被僧人和翻譯巧妙勸止。“文革”時期沒有誰敢動大樹一根毫毛。樹下上演的故事與傳奇無計其數……
銀杏王,是傳承民族血脈的圖騰樹,是中華文明的“活化石”,是美麗中國的靚名片。
銀杏的果、葉、材用途廣泛,具有較高經濟、生態、藥用和社會效益,銀杏產業正風生水起。當下,身歷古今、名譽中外的銀杏王更是子孫滿堂,青春蓬發。每年的冬春季節,高速公路和鄉村道路上常有大貨車,把銀杏樹苗送到祖國四面八方、適合生長的地方。為保成活率,樹苗都帶著一個草繩捆扎的樹根土墩,俗稱“老娘土”。全國各地的銀杏林、銀杏園、銀杏大道、銀杏鄉方興未艾、星羅棋布。
銀杏王有傲骨,有定力,有神韻,彰顯君子之風、國樹之威。莒縣正在修復莒國古城,銀杏王被尊崇為核心元素和眼睛。這株老態龍鐘但枝繁葉茂的銀杏樹,站立成中華文明的坐標,坦然訴說輝煌與榮耀、歷史與傳奇,可謂絕仰千古。
“銀杏王”沐浴天光、吸納地氣、凝守元氣,踏上生命新長征……
大汶口明石橋
2018年5月5日,我叫上妻子驅車來到雄偉的泰山腳下,專程謁拜大汶口明石橋。
“泰安這么多好景點,為什么非要看這座石頭橋?”
“一座石頭橋,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大汶河像一條玉帶圍繞在泰山腳下,古人這樣描述:“百川環碧,抱魯伏流。”匯泰山山脈、蒙山支脈之水,自東向西流經萊蕪、新泰、泰山區、岱岳區、肥城、寧陽、汶上、東平等地,又經東平湖流入黃河,奔向大海,全長200余公里。大汶河上游的牟汶河、柴汶河、石汶河、泮汶河、瀛汶河等五條帶“汶”字的河流,在汶口處交匯成大汶河,大汶口也因此而得名。據史料記載,明石橋修建于明朝隆慶年間(公元1567-1573年),故稱“明石橋”。這座明石橋北起岱岳區大汶口鎮南門,南至寧陽縣磁窯鎮茶棚村,全橋65孔,橋面由360多塊大型花崗石組成,整座石橋由數百個巨大的鐵鋦子固定著。這里是古人跨越大汶河這一天然屏障最容易的地方,也是南北古驛道的必經之路。這座“明石橋”,是整個大汶河上唯一的一座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古石橋,也是至今保存完好且能正常使用的一座古石橋。
當天正值立夏節氣,氣溫已明顯回升,樹木和農作物即將邁入旺盛生長期。橋上零星的農民兄弟正下田勞作,不時有拉肥料的拖拉機駛過,遠處幾位匠人正在維修橋墩,為汛期做著準備。此橋橋面由巨大的長石條鋪成,石條用扁鐵的鏈鎖固定。傳說這里最早是簡易木橋,后改為分段的石板橋,直到明隆慶年間,才建起一座橫貫大汶河的整體石板橋。清雍正八年,原石板橋被大水沖毀,兩岸士紳鄉民苦于無資修建,以攻石起家的粥店人姜桂松“捐資倡修”。乾隆六年,石橋修建完成并立碑記載此事,并改名“姜公橋”。之后,雖經兩次較大修整,但均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保持了“姜公橋”的原貌。石橋的選址極佳,頗顯智慧。橋上游是一片平緩的沙灘河底,橋下游是一片巖石,可以起到很好的緩沖、穩定作用。石橋的建成,結束了沿岸人民僅靠船只交往的歷史,溝通促進了商貿往來,也使大汶口成為了經濟重鎮。
史書記載,較早見于《尚書·禹貢》篇:“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浮于汶,達于濟。” 南北朝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四)里記載:“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
記得我上中學時學過《趙州橋》這篇課文。說河北一座石匠設計的石拱橋,“堅固,而且美觀”,歌頌了“勞動人民的杰出智慧和才干”。據陪同的朋友介紹,明石橋分為南橋和北橋,以橋中點為界,分屬于寧陽磁窯鎮和岱岳區大汶口鎮兩地,“一橋連兩縣”。石橋承載著鄉親們繁忙的腳步。有村民挑著重擔氣喘吁吁的身影,有扛著農具、趕著耕牛匆匆下田的步履,有三五成群趕集上店的笑聲,有迎親嫁女、喜爆聲聲的場面,有送子離鄉就讀或謀生、一步三回頭被淚水浸濕的目光。經常有人在河里摸魚,河灘牧羊,或坐在石橋上欣賞美景。那天就有一位年過半百的牧羊人坐在河灘上,任暖暖的春風掀動頭發和心緒,時而用瞇著的眼瞄一下羊群,悠閑陶醉。古老的石橋,見證了無數人的歡聲笑語和人生酸甜苦辣,為大家提供了娛樂休閑的好去處。古老的石橋,鐵環相扣,從橋上走出去,是否也被這鐵環鎖住了綿延的鄉愁?這石橋上有汽車、拖拉機、驢車、自行車、獨輪推車以及各種意圖和各種行色的人流。新與舊、虛與實、快與慢、動與靜、老與少、得與失,都在橋上展現,蔚為壯觀。
《水經注》記載:“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文姜者,春秋時期齊僖公的次女,齊襄公的異母妹,后為魯桓公夫人。文姜城是魯桓公為方便文姜回國省親而建。足見當年汶河古渡的重要。傳說文姜艷麗絕倫,婚姻一波三折,留下許多風流韻事。《詩經》中就有毀有譽。一百多年之后,魯國的孔子周游列國七八年,在齊國待的時間相對比較長。試想“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孔子必定數經汶河古渡,因為這里是穿行齊國、魯國的必經之地,可惜當年沒留下照片或者文字史料。那句膾炙人口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定是孔子站在汶河畔用他那犀利的哲人眼光,望著滔滔汶河水而抒發的感慨吧?他一直在感嘆時間流逝太快,提醒世人:青春易逝、韶華難再。
橋北一公里處,是著名的大汶口文化遺址。這里是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地和命名地。大汶口文化早期屬于母系氏族社會末期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中、晚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大汶口遺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發展的全過程,距今4500~6400年,為新石器時代遺址。1982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汶口遺址,已寫進歷史教科書。在現行中學歷史課本《祖國歷史的開篇——先秦》部分專門介紹了屬于原始社會的大汶口文化,認為與半坡文化相比,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歷史進步是:隨著原始農耕,生產力得到發展,出現了貧富分化和私有財產。它是黃河流域燦爛的古文明,它和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共稱華夏民族的文明起源。
大汶口文化遺址的活標本,就是這石橋和這流淌著的河水了。在鄉下農村,石橋到處都有。當然,架石橋這也是中國老百姓最普通的技術活了。在河道溝汊影響通行的地方,用或長或短極不規則的亂石頭堆壘幾座橋墩,在上面平鋪上幾根長石條作橋面,便是石橋了。長石條的縫隙,或用小石塊填塞,或用水泥抹平,就可以通車過人了。石橋墩就像低頭喝水的馬頭,插在河水里。我們村的村東就有一座石頭橋。橋西側是村里的住戶,狗吠聲、牲畜聲和呼喊聲交織,房前房后是樹木,屋頂飄動著縷縷炊煙;橋東,就是一條土路和東嶺及土地了。田野里一年四季景色美麗,或嫩綠、淺綠、深綠、黃綠,或鵝黃、嫩黃、橙黃、金黃。因為石橋的連結,兩岸的樹木、莊稼鮮活靈動起來,歷史在河水的流淌中淡化或者沉寂。久而久之,人們習以為常,甚至忘記了石橋的存在和默不作聲的功勞。
記得有個《彩虹和石橋》寓言故事,說彩虹曾經譏笑石橋破破爛爛,在石橋面前炫耀自己的五彩繽紛。石橋沒理會彩虹。一會兒后,彩虹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而石橋仍屹立不倒地站在大地上,兩岸的人可以繼續踏著它去耕種勞作。石橋被彩虹的美麗驚住了,它低下頭,心想:彩虹多漂亮啊,如果我像它一樣美,那該多好啊!彩虹看見了石橋,它也在想:這石橋多好啊,壽命那么長。
后來有人又續寫了這則寓言:雨后天晴,彩虹和石橋對話。石橋對彩虹說:“我低矮匐匍在地,你卻高高在上,高貴大方。”彩虹對石橋說:“我有的是絢麗多彩的外表,不如你可以實實在在地為人們做奉獻。”正當他們在互相羨慕的時候,一位畫家在石橋上支起畫架,對著這美麗的風景畫起來。畫家穩穩地坐在石橋上,畫著絢麗的彩虹。這時彩虹和石橋都親眼目睹和體驗了自身價值,一起笑了。彩虹的一生雖然短暫,但給了人美的視覺審美享受。石橋雖然樸實與平凡,但它支撐著不平凡的東西,無形中彰顯出巨大價值。
石橋不必嫉妒彩虹的美麗,彩虹也不必羨慕石橋的堅固。石橋固然不美,但它穩固地橫臥于兩岸之上,默默承載通行,這是它生命的價值;彩虹雖然只是雨過天晴的瞬間,但它那瞬間的美麗卻給人們留下了永久的回憶。這同樣彰顯出生命的價值。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當彩虹,有人做石橋。做石橋的長久默默地奉獻,當彩虹的卻在短暫的生命中閃現出燦爛的火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自揚長避短就是存在的最大價值和意義。無論前者后者,都沒有褒貶、高低、貴賤之分。大汶口明石橋承載著歷史,活著文明的記憶。
5月5日,是偉大的馬克思誕辰紀念日,2018年的5月5日又恰巧是200周年。德國古城特里爾,清澈的摩澤爾河安靜流過。200年前,一個偉大的靈魂在那里誕生,其思想的巨流在歷史長河中迤邐而行、源遠流長,奔騰在時代和人類歷史的峽谷,滌蕩著各種思想灰塵和垃圾,沖擊著人類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世界。在東方國度中國,這一思想巨流實現了最為波瀾壯闊的發展進步,并以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理論形態,激蕩起深刻社會變革的巨大力量。馬克思主義根植中國大地長得茂盛,且開花和結果。中國大地風起云涌至今熱度不減的毛澤東熱,就是生動佐證。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唯有文化能穿越時空,照耀文明的天空。
道路決定命運。道路通,命運通;道路走對了,當然就不怕路途遙遠。我國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直至19世紀末期,我國才出現了鐵路和公路。隨著近代交通工具火車、輪船、汽車的相繼興起,鐵路、公路、航線的不斷開辟,我國古代的驛路交通系統逐漸淡出了視線。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步入新時代,明石橋以其不朽的功業攜手大汶口文化遺址、京福高速公路和京滬高鐵等景觀,共同繪制著古老與現代、過去與未來、靜止與永恒的一幅恢弘歷史畫卷!
憶往昔,樓臺亭榭云煙茫茫,時光穿梭,古渡橋口風采依舊。明石橋凜然站在洶涌奔騰的汶河之上,凝望見證著滄桑和永恒……
黃河口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黃河口,是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匯入大海的地方。
黃河口,地處山東省東營市,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年輕的土地,每年至少新增土地一萬畝。
2018年霜降過后,北方大地五彩繽紛地步入金秋季節,我們全家出動,興致勃勃地游覽黃河口。鹽堿灘涂著稱的東營,已滄桑巨變,成為郁郁蔥蔥的海邊綠洲,竟然還有上萬畝的人工刺槐林。當年,河口區四周是白茫茫的鹽堿灘,風沙蔽日,海邊只有一棵孤零零的老柳樹。“一棵樹”成為記憶痛苦與無奈的地名和地理標志,播種綠色成為多少代人的奢望與夢想。這次到黃河口,我們毅然走黃河北岸,目的是更多欣賞最純美的自然風光。
從河口區孤島鎮出發,驅車約四十分鐘即進入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遼闊、神奇。黃河口的土地因海水千百年浸泡,嚴重沙化、鹽堿化,只有抗鹽堿、耐旱澇、抵貧瘠、能抗風固沙的植物才能活下來,長成鹽堿地的幸存者和主人。遠遠望去,只見海灘、潮溝旁、泛著鹽花和白堿的土疙瘩上,到處是一望無際的蘆荻和蘆葦,綿綿延延的檉柳,鋪展成“紅地毯”景觀的赤堿蓬,當然還有突然振翅、翱翔藍天的鳥群……
在黃河入海口能欣賞到沼澤、灘涂、濕地、蘆葦蕩、森林、水域、草甸等各種景色。深秋季節的東營,最漂亮、最有特色的美景,當然要數黃龍入海、蘆花飛雪、紅毯漫天、群鳥翔舞、長河落日。只見繁盛茂密、蓬蓬勃勃的蘆葦蕩,一方連一方,一片接一片,猶如等待檢閱的千軍萬馬一般。蘆花正盛開著,蓬蓬松松的,在陽光照耀下透明的白,被風一吹,葦穗隨風沿一個方向飄舞,鋪天蓋地。我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趕忙停車拍照留影。那一株株蘆葦堅強柔弱,頭頂雪白的蘆花,若美麗的少女窈窕婀娜,巧借秋風梳洗飄逸的長發,時而自我陶醉,時而竊竊私語。葦穗柔柔地垂落,輕輕滑過臉龐,一絲癢爬在臉上,一縷喜悅鉆進心房,舒適愜意極了。我瞬間感覺身心輕盈,像一朵毛絨絨的蘆花在自在飛翔,體驗大自然清純、神奇的力量。
河道和淺灘上,到處是鳥兒飛翔的倩影。據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的同志介紹,每年十月到第二年開春是鳥類遷徙的時節,黃河口濕地有數百萬只鳥兒在這里捕食、停歇、越冬和繁殖,被譽為“鳥類國際機場”。東營已成為東北亞內陸和環西太平洋鳥類遷徙的重要中轉站和珍稀鳥類繁育的天堂。目前這里有鳥類近400種,其中國家一級保護鳥類就十多種,譬如蒼鷺、鸕鶿、丹頂鶴、白鷺是全國最多的。游客可以隨時隨地看見各種鳥飛翔于黃河口的上空,棲息在灘涂上,或隱藏于蘆葦叢中,尋找、啄食濕地上的小魚、小蝦和小動物。鳥的家族在黃河濕地找到了安全感、幸福感、歸宿感,它們早已把這里看成自己溫馨的家園。
我和妻子執意帶剛會走路的小孫女,到鳥類救助站看野生的天鵝和大雁。小孫女一點不膽怯,竟然新奇地盯著東方白鸛,揮動一束柔美的蘆花,小心翼翼地與之嬉戲。這美麗的瞬間,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高境界吧?在這綿延的蘆葦蕩里,游人、藍天、白云、蘆葦、飛鳥巧奪天工地組合,處處美妙,步步風景。游人們觀鳥、看葦、賞景、趣談……微柔的風聲、悅耳的鳥鳴聲和人們的歡笑聲、吶喊聲交匯在一起,演奏出神圣的天籟之音。
滔滔黃河,自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起步,時而若縷縷琴弦,時而如萬馬奔騰,穿越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大平原,源源流淌幾千年,歷經多少凄風苦雨、坎坎坷坷,直奔祖國懷抱里的渤海灣,成為炎黃子孫尋根溯源的國脈和中華文明的精神臍帶。2016年夏天我去甘肅出差,專程到蘭州市黃河母親雕塑前,仰讀上游黃河的尊容,曾輕問黃河“何時奔騰到東營”?東營在春秋戰國時期屬齊國,管仲在此發展“漁鹽經濟”。明清時期,曾是盛極一時的鹽運、漕運要地和著名商埠。1961年春,在東營村打成第一口勘探井——華八井,發現了渤海灣大油區,后誕生了“勝利油田”。依托新興的石油城,1983年設立了地級東營市。從此拉開油田與地方融合發展,人、油區、植物和鳥類在這片土地上同生共榮的序幕,譜寫下共和國的精彩華章。
“一條黃水似衣帶,穿破世間通銀河。”黃河一路走來,被多少峽谷險灘逼得、擠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急忽緩,百折不撓。黃河無數次發脾氣和改道,其實都是在拼命尋找最適合的入海通道!
“一碗水半碗沙”的黃河水,流入東營已不再湍流澎湃,變得沉穩舒緩起來,海浪和河水縱情擁抱嬉戲,上演 “黃藍交匯”的壯麗奇觀。從黃河距離入海口最后一座浮橋乘船順河而下,船下就是細密的攔門沙,船身吃水很淺,行得也很慢,河面漸漸變寬,約半小時船就到了黃藍交界處。天氣晴朗、海流穩定,真能一飽眼福啦。從高空俯瞰,黃河猶如一條彎曲的巨龍、一把寬箭頭的箭,一頭扎入蔚藍的大海。渾濁的河水與澄澈的海水在碰撞、在交匯、在融合,恰如舞動著的兩匹黃藍兩色的錦緞,纏擰在一起、最后融為一體。流淌著中華民族血脈的黃河,執拗地撲入浩渺無垠的海洋,在融合、融入、融化中獲得新生,真實地復活“滄海桑田”,孕育探索海洋奧秘、創造海洋文明的藍色中國夢……
回望夜幕下的黃河入海口,天高云淡,河海壯美,天水一色,曠野和蘆葦叢中閃爍著點點燈火,回響著悠然的鳥鳴聲,勾畫出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同存共榮的天堂樂園。
黃河口,魅力無窮、心馳神往的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