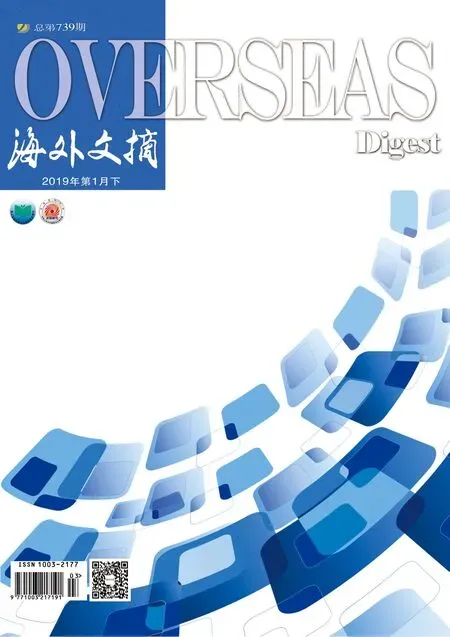民國時期歷史研究的艱難與困境
王晟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清末民初以來,史學取代經學,逐漸走向學術中心。自1920年代之后,民國史學界開始出現了一批近代意義的學術研究機構。與此同時,一批舊學深厚且掌握了西方先進學術研究方法的現代史家涌現出來。因此,有人把民國視為中國學術的一個“黃金年代”,絕不是無的放矢。
但是,民國又是一個動蕩不安、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亂世。波云詭譎的政治局勢加上政府的經濟拮據,又使得民國學人渴望擺脫政治的牽絆,建立一個“學術社會”的理想變成了空中樓閣。因此,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成為每一個民國學人所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1 建立一個純粹學術社會的努力
19世紀20年代,一批擁有西方留學背景的學人陸續歸國并且在學術界展露頭角,傅斯年便是其中之一。如果論學術造詣,傅斯年遠不及陳寅恪、陳垣等人精湛;但是,傅卻是這一群體中非常有雄心且擁有極強組織力的“霸才”。傅早年在歐洲學習心理學,之后又學習語言學,同時又學習了一些自然科學。復雜多樣的學科背景使得傅斯年擁有開闊的學術視野;而且,傅有著把東方學中心從巴黎和柏林轉移到北京的雄心;更重要的是,傅還具有極強的領導天賦,是不世出的學術組織者和領導者。
同時代的史家顧頡剛也有著相同的看法。1927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一生視王國維為學術偶像的顧氏撰文悼念。他對于當時濃烈的政治空氣干擾學術研究的狀況十分不滿。顧認為社會應該形成這樣一種風氣,“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學問只是研究學問,同政治毫沒有關系,同道德也毫沒有關系。”顧頡剛借著王國維自沉一事來表達他對當時社會環境、學術環境的不滿。他認為,國家應該為專心研究學問的人創造良好的學術環境,使學者安心投入學術研究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而且“不擔任學校里的任何責任,更不強迫他們加入某某黨派。”
陳寅恪也是民國學術史上致力于建立學術社會的代表人物。陳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經常掛在嘴邊,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句話絕不僅僅是一句口頭禪。陳認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與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此處的俗諦在當時應是指國民黨的黨義“三民主義”。南京國府成立之后,開始推行黨化教育,加強對于教育界和高等院校的控制。這與陳寅恪等人渴望建立一個純粹學術社會的理想相抵牾,故陳寅恪發此議論。但是,在一個動蕩的“革命年代”,讀書人想過安寧祥和的書齋生活幾乎是一種奢望。陳寅恪的個人命運可以說就是現代學人悲劇的縮影。陳的前半生顛沛流離,抗戰前的學術成果大半葬身長沙大火。后半生又受到歷次政治運動的沖擊。民國學人想擺脫政治,但是政治卻總是如影隨形,將他們的學術夢想擊得粉碎。
2 民族危機——政治形勢對于學術研究的沖擊
1927年,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同年,王國維選擇了自沉昆明湖。關于王國維之死,學界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筆者在此無意于舊調重彈。但是,不論是“殉清”還是“殉文化”,王的死都與政治形勢的變遷糾纏在一起。
到了19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加劇。政治形勢的變化也迅速波及到了學術界。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迅速淪陷。一向主張“不與政治生出干涉”的傅斯年為了回應以矢野仁一為首的日本學者鼓吹的“滿蒙回藏非中國論”,領銜編纂了《東北史綱》,以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傅認為,當時的東北問題絕不僅僅是“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國事者焉。”
3 捍衛歷史客觀性
科林伍德有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史學著作,我們都不難發現這些書中或多或少的鐫刻著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記。我們不能忘記,民國時期的史學家很多是科舉制廢除之后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他們身上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意識還十分濃厚。因而他們與后世那些以單純去探求歷史真相為目的的職業歷史學者的治史動機是不同的。民國史家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承擔著為國民普及歷史知識甚至激發國民愛國主義思想、增強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民國史家想要通過續寫中國歷史以延續民族香火。但是由于時局困頓,這些學者與大時代的風云變幻糾纏在了一起,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他們對當下的體悟融入了歷史的敘述之中。不過作為一名純粹的歷史研究者,筆者還是不免要苛責民國史家們。正是由于他們的一些有失客觀但又對后世影響深遠的論斷對后世史學造成的消極影響到今日都無法徹底扭轉。
今天的時代環境比之百年前已經大大改觀了,故而我輩學人自然要從“讀史求實”的角度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性并捍衛歷史的客觀性,這應是時代賦予當代歷史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