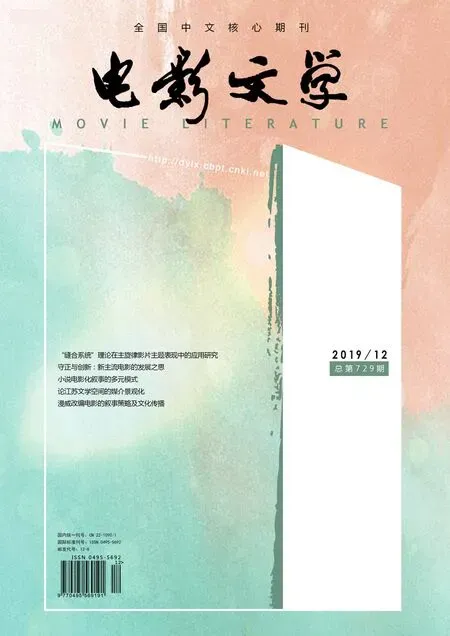電影《黑天鵝》的悲劇審美意識
賈 琳(鄭州大學 音樂學院,河南 鄭州 450052)
一、《天鵝湖》的魔咒及其悲劇內核
《黑天鵝》以紐約劇團重拍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為故事背景,由于劇團芭蕾舞演員的新舊更迭,領舞貝絲即將離開,舞臺需要一位新人上位并分飾兩角:白天鵝和黑天鵝。女主人公妮娜舞藝精湛,在同樣有著專業舞蹈背景的母親調教下高人一籌,是成為領舞的熱門人選,但由于自身性格內向拘謹,她在選拔時多次受總監托馬斯“刁難”,被認為無法體現“黑天鵝”的性感與魅惑,即使加倍努力也未能順利上位成為領舞。故事的沖突由此展開:成為“白天鵝”還是“黑天鵝”,做真正的自己還是托馬斯眼中的“黑天鵝”,這一命題不僅成為少女妮娜心中的一大困惑,也進而引發后續內心的困惑和命運的突變。全片分為兩個敘事層面,作為表層的是妮娜人物性格的異化、內心沖突的加劇扭曲,而內層則是作為原著《天鵝湖》的發展脈絡。
柴可夫斯基的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來源于俄羅斯的一個民間傳說:王子齊格弗里德打獵時偶遇一隊白天鵝,當他追隨白天鵝來到湖邊,意外發現白天鵝變成了一位美少女。原來少女是天鵝公主奧杰塔,她被惡魔羅特巴爾德施加了咒語,解除魔咒的唯一方式是獲得真愛,但如果背叛誓言,魔咒將永不能破。于是王子向公主許下諾言,希望奧杰塔能成為自己的王妃,并在天鵝城堡舉行選妃宴會。而羅特巴爾德得知后,將自己的女兒變成黑天鵝奧吉莉婭。當奧吉莉婭偽裝成奧杰塔的形象來到晚宴時,不僅驚艷了全場也蒙蔽了王子,被騙向她求婚。此時奧杰塔在窗外求救,但也無濟于事。最后她絕望離去,魔咒依然無法收回,白天鵝縱身跳崖自盡。很顯然,電影《黑天鵝》是以《天鵝湖》為主要靈感來源,經過提煉這一經典悲劇故事,構成了作品穩定的內核和敘事主干:施加魔咒——與魔咒抗爭——與魔咒同歸于盡。
為了能扮演黑天鵝并贏得托馬斯賞識,妮娜不惜犧牲自己的本性,不斷誘發自己內心欲望和心理底線,試圖成為強大的“黑天鵝妮娜”。在這一殘酷過程中,影片多次通過令人不適的特寫鏡頭加以描述,例如讓其身體發生變異:撕破手指流血不止、腳趾黏結成蹼、背部持續的傷痕以至最后長出黑色羽毛并強行拔出、發出動物般的呻吟……如果跳脫出影像本身,很難說這是妮娜遭遇的真實境遇,還是內心扭曲的幻想,但當“自我”這一形象不斷出現在化妝間的鏡子、地鐵車窗里時,空洞無神的眼睛和猙獰的笑容,加之懸疑類型的音效和配樂時,鏡頭語言都是低沉怪誕的,映射出她的一種精神病態和人格分裂,而這與《天鵝湖》的魔咒一脈相承。受困于天鵝軀體,妮娜在強行激發自身的原始力量,卻又在違背自我本性,在這樣一種主題架構下,人物細微的心理變化和扭曲行為,已經為她的結局命運埋下伏筆。
二、支離破碎的人物設置
《黑天鵝》全片營造了一種壓抑和不安的狀態,在向觀眾層層剖析了隱匿在個體內心的欲望之下,也塑造出外部環境的支離破碎。首先是女主人公妮娜的角色定位,在片中她是一名刻苦勤奮的芭蕾舞演員,善良純潔卻又軟弱孤獨。作為一個內向者,她成長于一個單親家庭,在母親的嚴厲管教下每日練習,完美、理想、自由和自我構成了她內心渴求的先后順序。圍繞這一潛在秩序,該片設置了母女 / 師生 / 同事 三組關系,而在這些支離破碎的關系中,折射出妮娜內心潛在的巨大逆能量和不斷分裂的過程。
首先是作為母女關系的不斷失衡到破裂。從小父愛的缺失,無疑對妮娜的心理成長造成嚴重影響,包括她對于性、性別關系的理解,而母親過分的保護、事無巨細的管理方式,讓她幾乎與外界失聯:生活的全部就是排練、幾乎沒有朋友、沒去過酒吧,對性和異性抱有敵意。第一次海選時,她并不理解托馬斯所說的“色誘”意義,所以在面對男舞伴和托馬斯時,她的表情是茫然拘謹的。而被提及戀愛經歷時,妮娜流露出尷尬甚至是恐慌。同時,觀眾很難在母親這一形象上發現某些溫暖或者母愛品格,從剛開始的古板嚴厲,進而發展到控制與私欲。“成為一個完美的芭蕾舞演員”是她和她母親的終極目標:作為一名前芭蕾舞演員,母親因為意外懷孕而終止了事業,這是殘酷的。所以她把未完成的夢想寄托在女兒身上,但母女關系始終是一種微妙的敵對關系。妮娜回到家繼續不斷練習,多次出現的背后傷痕卻從未得到過母親的鼓勵與關愛,很顯然,在這一家庭關系中,母愛是異化扭曲的。片中有幾幕戲都發生在妮娜家中,狹小的空間、雜亂的擺設顯露出母親并不關心生活的享受,客廳里掛滿了母親的畫像。母女間悉數的對話、冰冷的鏡頭語言展現出兩人之間的冷漠與封閉。如果說受困于“黑 / 白天鵝”的軀體是一道魔咒,那么妮娜的母親同樣是組成魔咒的一部分。因此,當妮娜從酒吧回來并產生幻覺時,才有母女關系的爆發與推搡打斗,雙方最終在獲得“自我”這一問題上撕破表象。
其次是妮娜與托馬斯微妙的師生關系。在影片中,總監托馬斯是一個二元角色,在妮娜眼中他是藝術家人格的體現,有著敏銳的洞察力,管理嚴苛,是自己的舞蹈導師,卻又有著花花公子的外在口碑(莉莉曾提及,并暗示和他發生過關系)。在試演黑天鵝這幕劇中,托馬斯用一種過激的方式試圖引誘妮娜,激發她的原始欲念,還帶妮娜回自己家中,但客觀來說,我們很難看出托馬斯對于妮娜有非分之想,反倒是一直試圖激發她出演黑天鵝的潛力。但與此同時,他似乎又精于精神虐待,通過鼓勵莉莉與妮娜的競爭,引發妮娜強烈的嫉妒心和內心張力——因此締造出不健康的師生關系:一方面是嚴厲苛刻的管教,另一方面又通過陰暗的手段一次次摧殘妮娜的內心世界。而在妮娜眼中,托馬斯即施加魔咒的惡魔,當妮娜遭遇舞蹈房停電事件時,她出現的幻覺體現了托馬斯在她心中淫蕩而放縱的一面。托馬斯多次出現在妮娜潛意識中的形象,體現了他對自己造成精神傷害,但她內心又渴望受到總監的賞識與認可,出演黑天鵝,這是一種極為復雜和精神扭曲的師生關系,如同《爆裂鼓手》一般呈現出人性的貪婪與私欲。
而片中最為冷漠的在于對劇團舞伴關系的刻畫。當托馬斯在宴會上宣布前領舞演員貝絲退役、妮娜將接替這一位置時,引發的是同事間的嫉妒與猜疑,大家關注的焦點不在于妮娜的舞技,而是她是如何“上位”的。貝絲因為無法接受這一打擊,精神失常而遭遇車禍,這一悲劇給妮娜造成極大的沖擊,以至于她去醫院探訪時產生嚴重幻覺。貝絲和妮娜一樣,曾經是有著完美舞技的“白天鵝”,但在劇團的扭曲氛圍中,表現出被害妄想癥并最終走向自殘和毀滅。在片中,妮娜一直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觀察著貝絲,對于貝絲的命運下場,她是抱以同情又感到恐懼的,因為在這段職業生涯中,她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并產生了某種共情。當然,片中多次著力于莉莉與妮娜這一同事關系的刻畫:這是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在導演眼中,如果妮娜是“白天鵝”,代表純潔、內斂與柔弱,莉莉就是“黑天鵝”的化身,邪惡、心機與外放,她們處于對立競爭關系。公演在即,在莉莉的引誘下,妮娜做出叛逆的舉動,試圖打破內心禁忌,去酒吧、和異性發生關系、嗑藥宿醉,并對莉莉產生幻想。酒吧一晚成為全片的轉折點,妮娜明明很厭惡莉莉也知道她的心機引誘,卻又跟隨墮落,我們不難看出此刻的妮娜,已完全對“黑天鵝”這一形象走火入魔,她試圖尋求外部的各種刺激來激發自己內心的某種欲望,或許她在莉莉身上看到了“黑天鵝”的影子——女性的荷爾蒙和風情,那正是她所欠缺的,所以她決定放棄自己的修女形象,在放縱與激情中解放自己,而這是她迷失自我同時又領悟到“黑天鵝”精髓的開始。對于莉莉,妮娜表達出十足的恨意,尤其在最后公演出場前那一幕,為了自己以“黑天鵝”形象上場,妮娜臆想自己在化妝間殺死了莉莉,在這段錯亂的幻覺中,她展現了嚴重的精神分裂并散發出作惡的快感,這一幕已經預示著妮娜內心的坍塌、走向毀滅。
三、心理沖突的不斷升級與悲劇結局
《黑天鵝》是一部由眾多意象和象征元素組成的影像,這些意象中蘊含著導演對主人公命運和心理狀態的共情思考,敘事語言中散發的強烈悲劇色彩與該片主題不謀而合。例如黑 / 白天鵝截然相反的造型和配飾、演員妝容,妮娜身上屢次出現的手指傷口與后背抓痕、多次出現的夢境、帶有血漬的浴缸、化妝間 / 地鐵上的玻璃鏡等等,每當這些意象出現時,緩慢的長鏡頭和低沉婉轉的配樂,放大了影片黑暗壓抑的氣息,并準確地映射出妮娜的焦慮和脅迫感,她試圖掙脫自己卻又愈發失控,不斷走向崩潰邊緣。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中反復出現的夢境、幻象,以及介于清醒夢與現實之間的游離狀態,模糊了妮娜對本我與潛意識的界限,構建出主人公強烈的心理沖突。繼影片開篇的夢境后,第二次明顯夢境,是妮娜嘗試了莉莉的藥丸后持續致幻的狀態。從她離開酒吧開始,到回家路上的性幻想,家中與母親的打斗、與莉莉的歡愛,最后從公演遲到的現實生活中驚醒結束。雖然事后導演通過莉莉之口交代這一劇情只是妮娜的幻覺,但這一場景已經讓她體驗到內心的暗涌與覺醒:身為乖乖女的她竟然半夜離家、嗑藥、與陌生男子尋歡,回家后與母親大打出手——她在尋找一個“黑天鵝”靈魂的出口,很顯然她是以莉莉形象為參照開始幻想的。再經過夢境的加工,赤裸的欲望與肉體徹底激發了妮娜的情欲,于是才有了自己意淫與莉莉交歡的這段敘事。 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夢境是愿望的滿足,是人們對平時生活中忽略細節的二次加工和轉移,從妮娜的夢境中我們能發現她對于自我意識、潛意識的混亂與沖突。
而莉莉給的這粒藥丸似乎成為一把鑰匙,讓妮娜無需睡眠就能持續產生幻象,臆想成為一種常態:在舞蹈排練房后臺目睹莉莉與托馬斯交歡、后背長出黑色羽毛、化妝間謀殺準備取代她的黑天鵝女孩……黑天鵝成為一種強烈的意象 / 意識形態,控制了她的正常思維,并讓她更加極端。在這一系列夢境后,白天鵝徹底完成了向黑天鵝的蛻變。而當她在化妝間與另一位“黑天鵝”發生打斗,并撿起玻璃碎片刺向對方時,她已經獲得足夠的勇氣,以及邪惡,這正是她想獲得的。如果說現實的壓抑、各種不健康的人際關系讓妮娜無法適應,那么在這三段夢境中她完成了心理沖撞與建設,并挖掘出內心最原始的欲念,實現了黑 / 白天鵝的合二為一,同時也完成了現實自我的徹底分裂。當妮娜化身黑天鵝獨舞時,電影迎來高潮:天鵝之死。她在舞蹈中臆想兩臂長出黑色羽毛,成為一只真正的黑天鵝,忘我旋轉揮舞間,靈欲合一。舞臺上巨大的天鵝影子與舞者相互輝映,最終實現美的升華。在經歷身心與精神的雙重磨難,黑 / 白天鵝在對立矛盾中合體,妮娜創造出了完美。但遍體雪白的她卻帶著黑天鵝的傷口,縱身一躍完成了自己的謝幕,就像她最后臺詞中所說:“完美。我得到了完美。”
妮娜用近乎自殘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謝幕,或許她的不幸折射出一種職業悲劇:優秀的演員都是極其危險的,因為他們為了演繹不同的人物個性,需要不停地游走在人性邊緣。《黑天鵝》正是透過妮娜的危險遭遇,客觀還原了一名普通舞蹈演員的痛苦與悲情,同時也展現出當她在面對善與惡、美與丑、生與死等各種人性抉擇時的掙扎。為了選擇完美藝術,妮娜燃燒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這是一曲女性的生命挽歌。無疑,她的結局充滿了悲劇色彩,這是有關社會意識、自我覺醒和藝術巔峰間的悲壯凄美。但在面對靈魂的吶喊和命運抗爭時,妮娜表現出的頑強抗爭和追尋藝術完美,充分體現了一位當代女性的崇高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