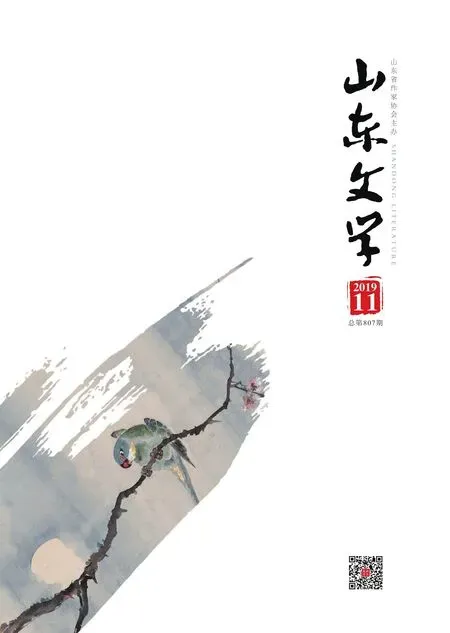老船與晃動的時間
阿 占
喑啞之聲從深處傳來
一條二十年的老木頭船,用兇惡的風浪做了紋身,滿布的殺伐之氣,就像那些久經沙場的武王。現在,它被擱置在早春的岸灘上,正午時分,若靠近船身,能聽見喑啞低悶的聲音從深處傳來。榫卯徹底相離,怕是生命里最后的動靜了。
喀吧一聲!榫卯相扣,這是新船才有的資格。新船和新房子一樣。從前新蓋的大木梁架結構的房子,房架上柁沒完全裝到位,經過一段時間的居住,被煙火氣焐熱了,被人的呼吸落實了,會發出喀吧一聲。新的,邊簧和邊槽之間即便較著勁,仍不會開裂和變形。老船恰恰相反,響起來的,是散了架的聲音。一聲成讖,便已歸天。
再看老船,好像被燒刀子泡過,泛青,泛藍,泛黃,泛灰,泛白,泛一切天翻地覆的狠顏色。燒刀子是什么?因為度數高,味濃烈,似火燒,而得名。漁把式們都知道,燒刀子之烈,遇火則燒。入口如燒紅之刀刃,吞入腹中燃起滾滾火焰。出海打漁,在冰冷的天海之間,正是憑借這一腔剛烈,漁把式們才能找回存在感。
渡海的老船,當年渡的是苦難,渡的是艱險,能夠從這些個中間抽身而過的,怕也只有仁慈了。老船身上的每一塊木頭都有靈性,早就成了雷電的一部分,成了風暴的一部分。老船曾經對主人說過,如果有一天老了干不動了,要將它留在大海上,隨風浪漂泊,逐漸解體。或者在某個瞬間憑借風浪與礁石的夾擊而粉碎,轉眼沉入海底,成為深藍的深處,這些都可以讓老船擁有從生到死一直屬于大海的榮耀感。死于大海,老船相信還會有來世。
至不濟,也要擁有灘涂一隅,對死亡保持覺知,潮汐漲落,時間顯示出不動聲色的力量,生命之光與死亡陰影重新融合,流沙如軟金覆蓋了所有的秘密。
主人肖老大沒有背叛老船。在漁村,老船不能用了,拆卸變賣是一種約定俗成,十個有九個船老大都會這么做——頭顱拆分下來,賣給流動的小販,改造成簡易住房;軀體賣給家具商,打磨上漆,以老船木的噱頭哄抬幾番;心臟和大腦賣給收廢鐵的,與廢棄易拉罐混為一談……大多數船老大都希望那些駕駛艙、發動機和螺旋槳能賣個好價錢,除了肖老大。他知道老船不想這樣死。相會過千軍萬馬,最后落得變賣殘骸,這樣的過程比結果還要疼痛。死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丟失未來,而在于沒有了過去。唯肖老大惺惺相惜。
不過是一條渡海的破船,留著干什么?人們不解地問,包括肖老大的兒子。肖老大陡然大怒,在兒子臉上甩了一個巴掌。
回想起海上的蒼茫日夜,一切背景都簡化了,都退后了,只剩下孤獨的海平線。肖老大和老船始終沒有發現岸,他們固守著心中的石頭,彼此默契。來了好潮水幾天幾夜不能睡覺,要趁著潮水浪峰搶魚。在風口浪尖,他們一起扯著嗓子吼起來。置于風暴的中心,他們把自己拋了出去。
肖老大到死都不會忘記那一年的農歷九月初五,早晨出海還是漫天的胭脂彩霞,到了中午頭兒海就怒了,眨眼功夫,灌滿鐵鉛的云層越來越厚,沉沉地碾壓而來。肖老大從沒見過這么逼仄的天空,他感覺快要憋死了。忽然,冰雹噼里啪啦地砸下來,最小的如雞蛋,大的竟好比半塊磚頭。那浪啊,扯天扯地。一個浪峰過來,船被拋了出去;一個浪峰過來,船又被接住了。漁伙計們不是吐出了苦膽就是嚇破了膽,根本無從下手,只聽任老天安排。
無數的浪峰之后,船竟然沒翻,肖老大還活著,天空放晴,他像一個剛剛經過了墳墓的人,抖掉渾濁,爬了出來。
一起組成舉世的廢墟
肖老大與老船相依為命,彼此的悲喜是連同著生死沉浮一起完成的。
二十年前,肖老大正值壯年,那個吉日,他興興頭頭地置辦了漁網漁具,在新船上貼滿了對聯。大桅上貼“大將軍八面威風”,二桅上貼“二將軍日行千里”,艄桅上貼“三將軍舵后生風”,四桅上貼“四將軍前部先鋒”,五桅上貼“五將軍五路財神”,船艙內貼“船艙滿載”“積玉堆金”,大網上貼“開網大吉”,船頭上貼“船頭無浪多招寶”,船尾上貼“船后生風廣進財”……終于,一切停當了,放炮仗,請財神,做羹飯,下水。
工事一尺,命大一丈,船通常需要三年兩修。過去的二十年里,肖老大都是按照這個頻率把船交給石老二,就像肖老大的爹把船交給石老二的爹,一樣。
從祖上開始,石家就是半島地區有名的修船匠,憑借一把斧頭、一把刨子、一把鋸子、一個鑿子、一些麻絲、一點油灰,石家在不同的漁村里施展著匠心和苦心。修船攸關漁家性命,非同小可。整個木頭船都是手工打造的,修補只能依靠手工推進,一寸是一寸,一厘是一厘,想快也快不起來,即便五六米長的小船,縫縫補補也要七八天功夫。
修船是一種悟性,更是一種緣分。以前這門手藝不傳外姓人,師傅門下頗為擁擠,后來木船被鐵殼大船替代,再加上修船又累又枯燥,很多人轉行不干了,修船匠就跟海里的魚一樣,越來越少,幾代人的手藝快要走到盡頭了。
老船最后一次修整是兩年前的事情。伏天休漁,漁民進城打工,修船匠卻是最忙的。石老二戴著草帽,衣褲嚴實,為了躲過毒日頭,他凌晨四點半就得開工。肖老大提了茶水去看他,順便也去看看老船。他們躲在陰涼地里歇晌,沒有一絲風,滿世界閃著針尖兒一樣耀眼的光。
這船到年歲了,石老二說。我也到年歲了,肖老大說,春秋天三五海里跑跑,撈點小魚蝦,就消停了。后來又說到了各自的兒子。肖老大的搞養殖,石老二的開漁家宴。年輕人誰會守著一條船過日子呢。
茶水濃釅方能解暑,茶銹如鐵,就像歲月的堅硬。肖老大給石老二遞了煙,繼續說下去——那些年,船把肖老大帶到了不為人知的所在,海怪、大魚,他都見了。大魚的脊背是黑色的,拱形,就像退潮時露出的島子。有月亮沒有風的晚上,船把肖老大帶到海中央,大魚就會來報信,告訴他在哪里撒網能滿載而歸。魚嘴一張一合,清脆的聲響能在水面上走很遠。肖老大就仰天長笑,那笑聲甚至能把月亮擊落……
夏天之后,肖老大與石老二再無后會。又過了一個夏天,肖老大與老船一起上岸,漁網漁具都撒在房頂上,老船則風化于天地自然之間,于是便有了開頭的那一幕。也許用不了多久,人們會說,看那老船,像被狼吃剩的牛或馬的骨架,也像被人和貓吃過的魚的骨架。肖老大必定更老了,每逢大潮之日,孑孓而行于岸灘。
海風嘯叫起來,浪的堆疊如雪,他和老船一起組成了舉世的廢墟。
陷在晃動的時間里
早先的碼頭十分簡陋。海灣兜轉,幾進幾出,尋個避風的地方,壘上一行石頭就是堤壩了,堤壩上再碼幾塊方形的條石便有了纜樁。
碼頭既泊船也進行漁貨交易。漁船通常在下午收山,正是碼頭最喧囂的時刻,叫賣聲、裝卸聲、砍價聲混雜在一起,掀起的魚腥氣隨波浪漫涌,從來不會消散。
船老大們穿著橡膠褲,滴著海水,一身咸腥濕漉。這些常年闖海的人,滿臉粗暴美學,額頭上寫滿了曾經的航道,有深有淺,有激流也有暗礁。
漁獲被搬到了碼頭上,船老大開始和魚販子討價還價。販子殺得狠。末了,好歹也得賣,且并不是現錢。馬達突突直響,又一條船靠岸。幾個魚販子不約而同地揚手甩掉半截煙,圍上去,掀起一陣新的熱鬧。在炸雷般討價還價聲中,成筐的魚蝦被裝車運走。沿途散落下幾只透明的小蝦滿地亂蹦,運氣好的蹦回了海里。
天沒黑,吃飯還早,幾個漁伙計開始整理漁網。網目之間牽扯了水草、塑料袋,諸多雜物如果不拿掉,收網拉魚的時候會很費力。就這樣忙活到日頭偏西,船老大方能帶著一身疲憊,朝炊煙的方向回返。
最讓人害怕的是,船在不該回來的時候回來了——那一定是出事了。船,可以打纜停泊,可以隔水泊錨,卻不能突然返航。太陽才爬升了一半,離下午還早,一條或幾條突然回來的船足以讓漁村里的每一個女人掛起愁云。她們放下手中的活計,從山坳的玉米地里,從屋前的花生地里,或者從織網的飛梭上,從曬魚的竹竿上,抬起頭,眼睛里都是恐憂:這么好的天氣,咋回事?
隨后齊齊地撲向碼頭。
碼頭為漁獲豐收提供T臺,為生活秀制造場面,也可以冷血地演繹出期盼與喜悅的對立面。當不可預知的風暴發起殺戮,從碼頭上抬下來的一具具尸體,枯峭形骨,顏色全無。
女人在離別的碼頭目睹男人最后的遺容,嘶嚎大哭,發出動物的哀鳴和植物的尖唳。褶皺相似的船老大、修船匠、漁伙計,臉上堆起不同的悲戚,在碼頭上徘徊著,想說一些寬慰的話,又不知從何說起。最后只好站在碼頭上,站成等待的模樣,擋住冽冽北風,挽起船纜的手上皸裂的口子也在悲傷啊。
在漁村,這些都是必須經歷的一部分。農耕區的二十四節氣歌,意味著生產和生活周期是按年計的。漁家從小爛熟于心的則是潮水時間歌,它非常復雜,每一天都讓人心生不安。
出海,深陷在晃動的時間里。站著是晃動的,躺下是晃動的,捧著碗吃飯也是晃動的。在晃動的每時每刻,卻要對所處的位置做出準確判斷,否則將永遠無法離開大海。
漁村的等待,埋沒于憂傷的時間里。總有一個未歸人。有的是丈夫出了海,有的是兒子出了海,有的是父親出了海,有的是兄長出了海。在那些悲欣交集的日子里,他們不停地離開碼頭,又不斷地回到碼頭,中間的迂回,或許就是一生。
出海的人和等待的人,心硬起來。
巨礁穿起怪獸的大氅
行船闖海,命運多舛,心若不硬,只能破碎,甚至瘋魔,那樣的話,日子也就沒法過了。幾乎每個漁村都有這樣的瘋女人,多年以前,大海咬痛了她。
天黑前,瘋女人會準時來到碼頭,坐在纜樁上,逆著天光,三分之二的肢體埋在暗部,加之衣衫破舊,頭發散亂,越發混沌不清。她直直地看著碼頭上的男人搬運漁獲或者其它什么,偶爾自言自語,反復都是那么一句,且明顯帶著責罵的口氣:怎么還不回來,怎么還不回來?
碼頭上的人漸漸散去。終于,最后一陣摩托引擎聲徹底消失在村口,夜幕砸了下來,就像人間劇場失控的帷幕,一瞬間天就黑了,碼頭沉浸而去,沿岸的巨礁穿起怪獸的大氅,隨潮聲聳動,各種影子在意識里行走,與暗喻為伴。
是啊,月亮升起之前,黑色足以讓所有停泊的漁船塌陷。
瘋女人依然坐在纜樁石上,像一條風干的瘦魚。勞作結束的家人遠遠地喊了起來,回家吃飯啦,通常是兒媳,等船的瘋女人才起身,跟在兒媳的身后走了。
如果去打聽瘋女人的由來,得到的版本往往相似: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啊,已經五十多歲了。年輕時從南邊的漁村嫁過來,是個織網好手。一梭一線,一紡一目,斗網、撒網、攔網,不管網眼是粗是細,都不在話下。她還帶來了祖傳的古法工藝,漁網的最后一道工序不刷桐油,而是涂浸豬血,寓意為“刷腥”,圖個多捕魚的好兆頭。本村的鄰村的都來找她織網,人人都羨慕她家的日子好。
又或者,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啊,已經五十多歲了。年輕時從北邊的漁村嫁過來,是豆腐匠的女兒,帶著一個磨豆子的磨盤,在婆家開起了豆腐坊。她爹那時身子骨還硬,經常會在月光皎白的凌晨趕到,告訴她一些做豆腐的秘方:泡豆子的時候,抓把麥子一起泡,一起磨,出鍋的豆腐有了小麥的筋道,自然不容易散。她很快做出了遠近聞名的豆腐,別家的豆腐切開就散,必須用碗盛,她做的豆腐用手托著就可以拿回家了。
接下來的幾乎就一模一樣了。
大約二十年前,她的丈夫出海再也沒有回來,從此以后,在每天相同的時間里,她還是到這里接船,等丈夫的船靠上碼頭,好幫忙收漁獲。
在漁村,“寡婦”依然是個不吉祥的名詞。丈夫死了以后,她一直沒改嫁,給四里八鄉曬紫菜、織漁網、賣魚蝦、做豆腐,掙些活命錢,等到磕磕絆絆地把孩子養大,她的雙手已經被長年累月的勞作打磨得像銹鐵,像腐木。
漁村地少,種糧食活不了命,只能去海上討生活,父親干不動了,兒子頂上。父子不同船是沿襲至今的習俗,惟有這樣,才能保全一個家族的血脈。她總共有三個兒子,其中的一個兒子長大后執意要做船老大,她堅決不同意,打他,也打自己。可他是船老大的種啊,源頭在岸邊,去路,卻必定在海上。他只一意孤行,到了更遠更野的海上,用身體丈量涌動的大漠荒原。
大約十年前,兒子出海再也沒有回來。她不相信,下次漲潮一定會回來的,她逢人便說。
唉,那個年代的漁村總是傷痕累累。行于風浪是船的宿命,也是漁民的宿命。漁民和大海的關系,有點說不清,是病人與醫生,是選中和被選,是互相供養,是愿賭服輸。
領受的龍王報以微笑
祭海的牲禮供養過了,領受的龍王報以微笑。
漁民眼里的海,充滿了生命意志與神秘能量。拋卻月球和太陽的引力作用不論,他們寧愿相信龍王真的存在——龍王的吐納呼吸制造了海水的漲漲落落。時間一到,推波助瀾,迅猛上漲,達到高潮;時間一過,層層退去,低潮停駐。如此循環往復,永不停息。
到了海上,很多事說不清,漁民只能投以敬畏,默默護持著共同的見知與秘密,想盡各種辦法與大海講和,小心翼翼又勇敢堅韌地從海里討回想要的生活。
“海者,晦暗無知也。”不祭海,漁民們不敢在春天撒下第一網。祭海在漁村是天大的事。五百年以前就形成了節日。中國北方海邊,田橫島祭海節是規模最大的,每年春汛來臨的時候,田橫漁民修好了船,添置完漁具,把漁網抬上船,準備蓄帆向海之前,會選一個黃道吉日——農歷的春分。
四更五更,海邊已經備好了供桌和祭案,船老大們將彩旗獵獵的漁船行到村前海灣,船頭面向大海,一字排列。祭祀前,要用黃裱紙寫好“太平文疏”,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來完成,以示虔誠。祭祀時,數十名壯漢擂出鼓聲,四鄉八疃匯聚一堂,喝酒吃肉,勝似過大年。劇團扎臺唱戲三天三夜,秧歌、腰鼓、高蹺也耍了起來。在自然崇拜的儀式中,漁村鄰里的人情更加深遠和牢固。祭海儀式結束后,船老大們帶著分來的貢品,趕赴大海。
“潮”和“汐”被用來界定白天與晚上的海水上漲,后來,約定俗成,潮和汐也就統稱為“潮”了。潮水漲落,能繁衍生息,也能銷金熔銀。船浮在無底的深淵之上,空茫無望,和在黑暗中行走相似,漁民們習慣了隨浪涌派遣心跳,演繹出沉浸式風暴美學,且從未停止過對于自然的解讀,那些口口相傳的諺語,是潮水日子里的草根教科書。
“二月清明魚是草,三月清明魚是寶”“早上空打空,晚上馱不動”“臺風過海蜇無”,這些說的都是漁汛與潮水的關系。
“早有胭脂晚怕白,天見此象大風來”“日暈三更雨,月暈午時風”“北打閃起狂風,西打閃雨重重”“春風不過宿,一天南來一天北”,這些都與風相關,而風向直接決定著漁汛。
“正月十九觀音暴”“三月清明田雞暴”“四月立夏暴”“九月初九重陽暴”“過了重陽暴,海過打鋪好睡覺”,這些則概括了風暴發生的規律,說的都是大海翻臉不認人的時候。
漁民們彪悍的口音必定來自風浪的塑造,去聲頗多,硬喳喳地,飽含著分量。
傳世的銀器懸于當空
一條白色的魚從海面上躍起,向著東方,完成了兩米左右的飛行,重復了一次,又重復了一次。在天與海之間,它的潔白似有珍珠光芒,亦如傳世的銀器懸于當空。岸灘上有人尖叫起來:快看!好大一條白鱗魚啊。
這是一個轉型后的度假漁村,歡樂著也嘈雜著,潮低水淺間,魚的倏忽一縱是件驚艷的事情。人們舉起手機,像瞄準那些超級明星一樣,同時獻上尖叫。
漁家宴老板站在海草房底下,遠遠地看著,心底涌起一陣不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城里人和內陸人啊。
在遠海,確有飛魚如鳥群,當空展開胸鰭,展開壯麗的飛行。鳥翼魚身,身形如梭,流線優美,風力適當的時候,這些可以支持飛魚躍出水面十幾米,在空中最長停留40多秒以及一口氣飛出400多米。它們在水下加速,一沖破水面就把大鰭張開,尚在水中的尾部快速拍擊,從而獲得額外推力。
飛魚的飛翔,大多是為了逃避金槍魚、劍魚等大型魚類的追逐,也可能因為船只的靠近受驚而飛。如此僭越鳥類特權的舉動往往讓它們搭上性命,撞在了礁石上,落到了海島或甲板上。船老大常常在黎明時分撿起它們的靈魂,并悼念這場遺落的夜間飛行。
漁家宴老板是船老大的兒子,講不完的海故事浸漬了他的童年。尤其在最冷的冬夜,船老大終于不能出海了,他一邊在爐火上烤著干魚一邊講故事,那是漁家傳承了許多代的娛樂方式。
漁村有個好聽的名字,魚鳴嘴。城里人和內陸人被如此詩意的名字陶醉了,一個勁兒地跟漁家宴老板打聽名字的由來。原先,此處水深域擴,不凍不淤,魚汛時常常聽到魚鳴之聲,在深藍深處,在神秘的夜里,黃花魚、黃姑魚,咕咕咕,咕咕咕,像風中的歌唱,又像竊竊的私語。
漁村成海岬,向南伸入海中,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望見對面的孤島。迎著風,大海開始漲潮,迭起層層白浪,推進,推進,撞擊在岸邊的礁石上,嘩然盛開,又轉身即失在無盡的藍里。
很多漁村都在城市改造中消失了,漁村之上生長起現代化高樓,好像發生在一夜之間。消失的漁村也都有著好聽的名字,堯頭村、硯臺村、豐城、女島村、叼龍嘴、南選……無不脫塵拔俗,背后似有故事,又好像不過都是海風里脫口而出的一聲招呼,一個應答,就像“漁路淡如煙,煙中有人住”那樣自然而然。
這些咸咸的名字,這些幾代人不敢丟下的名字,或結合周邊地理寓意,或因了某個傳說,或承載著漁村的演化,如今已經藏進了盲區,永遠不再與潮水相關。
活下來的船老大已經到了古稀之年,嚴肅而不茍言笑,黝黑且精瘦,一副格格不入的舊時模樣。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什么。小潮之時,他還是會抓起漁網去海邊,站在礁石的高處拋灑而出,最后只有巨大的深藍掛在網上,是水滴,而不是魚。
海,每年都在縮小。環境污染、海面升降、地殼運動、河流淤積、人為填海,都是海的硬傷。
越過時間的峰棱,船老大或許想起了漁獵往事,那是船在移動,佇立在甲板上,他的第一個黎明和第十個黎明沒有區別。單調、孤獨和隔離,常常使船老大失去參照系。他強迫自己記憶著日出日落,識別每個星座,這些星星生活在大海之中,就像從前那些數不清的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