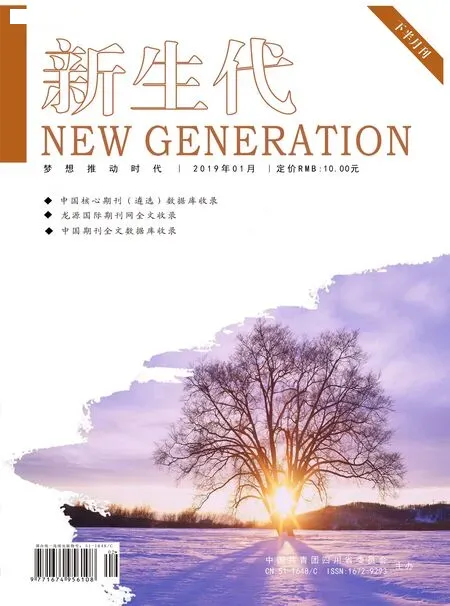校園欺凌的法律規制研究
江思晗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 安徽蚌埠 233030
近年來,頻發的校園欺凌事件越來越多的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校園欺凌這一在很多人心目里只是代表著因為孩子調皮的天性而產生于學生之間的毆打的行為,已經逐漸異化,并成為一種社會問題。近年來首次引起國內外熱烈討論的校園欺凌事件并不發生在中國大陸,而是一起發生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之間的暴力欺凌事件。2015年三月,三名中國留學生將另一位中國女留學生綁架、軟禁、折磨并毆打,3月30日,他們又用相同手段對另一名中國女留學生劉怡然進行施暴,手段殘酷惡劣,該視頻引起了國內外軒然大波,而日后美國加州法院均判處三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個嚴厲的判決結果和事件本身,引發了人們對校園欺凌的重新思考。
欺凌在英語中被稱為bullying,也被稱為霸凌,欺辱。如今,伴隨著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校園欺凌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張,其已經不再僅僅是很多人提到這個問題時會想到的肉體暴力或學生間的斗毆事件,事實上,除了傳統的對身體的直接侵犯外,它也具有了更多的時代性和特殊性,其欺凌手段也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嚴重性。但是,時至今日,世界范圍內的學者對于何為校園欺凌仍沒有達成統一意見或較為準確的語義文本。關于校園欺凌常用的是挪威學者歐文斯的定義,即一個學生長時間暴露在一個學生或多個學生主導的負面行徑之下,和一般的沖突相比較起來,校園欺凌的特點往往是反復性和持續時間較長,雙方力量懸殊且往往呈現出一方具有的壓倒性優勢。同時,歐文斯將其定義為一種“負性行為”。還有一些非主流觀點認為,應當將教職工甚至校外人員也可以視為校園欺凌的主體,但這種對外延的擴大未免有些過度。同時,基于引用較多的美國教育部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制定的統一的校園欺凌的定義:“校園欺凌是學生或一群學生對另一名學生或另一群學生的強制性攻擊行為,它可能對被欺凌者造成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傷害,這種行為涉及學生間可觀察到或可察覺的權力失衡,并可能反復發生 ”,我們可以得出,校園欺凌是以學生為主體,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肉體暴力,群體性孤立,言語侮辱的一系列具有反復性,并達到某種嚴重程度的負性行為。
一.校園欺凌的現狀及我國的應對措施
對于校園欺凌,因為定義的不統一未能有統一的調查數據,但是我們仍可以通過被曝光的社會新聞和司法機關的相關文件對這一社會問題的現狀管中窺豹: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前11個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的校園欺凌暴力犯罪案件2486件3788人,提起公訴3494件5468人,較去年同期同比增長50.3%。教育部政策法規司相關課題組在2016年對104825名中小學生的調查發現,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3.36%,常被欺凌的占其中的47%,偶爾被欺凌的比例為28.66%。【1】也就是說,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遭到過校園欺凌。
伴隨著事態的逐漸嚴重,政府部門也越來越關注相關的法律規制和政策調控。2016年4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印發,要求各地對校園欺凌進行專項治理,這也是首次從國家層面提出了對校園欺凌治理的要求。隨后,教育部,最高檢,公安部等聯合出臺了《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同時,在2018年, 多省都針對校園欺凌出臺了更為嚴格的措施和法律,譬如2018年11月廣東省教育廳等十三部門印發的《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的實施辦法》,對學生欺凌事件的種類和適用做出了明確分類,其中包括給他人起侮辱性綽號和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貶低他人人格的語言。這也是首次在政府專門文件中承認侮辱性綽號和人格貶損也屬于欺凌的一種,無疑對我國立法層面上對校園欺凌的先行研究有很大裨益。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公布,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成為了其中一類立法項目,而反校園欺凌立法將在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時一并考慮,擬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內提請審議,這也是立法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二.我國現行法律的弊端
我國目前并沒有一部專門的反欺凌法對校園欺凌進行一個嚴格的定義,更無從談起后續的規制,以及對特殊主體的教育,對受害者的心理疏導機制和賠償機制,以及更為重要的預防機制。同時,目前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多是教育部門為首出臺的文件,無論是效力位階,強制性和政策落實上,都顯得有些差強人意。同時,也只有東部部分省份出臺了相關政策,而教育部的相關文件里,同樣沒有對校園欺凌進行科學的定義和劃分級別。而由于此前,校園欺凌多被視作單純的人身侵權加以處理,并沒有考慮到主體身份的特殊性,刑法和侵權責任法的規制雖然明確,但并不具體,特別是針對方式多樣化的欺凌,譬如恐嚇,孤立,起外號和侮辱,侵權法都顯得格外捉襟見肘。而主要問題主要集中體現在事件發生的責任承擔不到位和處理方式不恰當。首先,雖然部分欺凌行為可能已經達到了刑事犯罪的標準,但由于當事人身份的特殊(多為學生),多數欺凌行為被掩蓋下去私了了事,甚至沒有被老師家長發現,欺凌隱秘地持續著。其次,管理機構的后續跟進也相當不到位,在欺凌事件被發現后,教師作為受欺凌者求助最便利的管理者,往往對事件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短暫的批評教育后便不再介入,鬧得更嚴重的也不過是調換座位或調離原班級,直至轉校。最后,學校和家庭對欺凌的預防措施均相當不夠,完全沒有相應的標準和機制,而僅僅口頭教導團結友愛,并不能真正對學生欺凌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起到阻遏其發生擴散的作用。
根據另一部未成年人的專法,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規定,尚未達到刑事犯罪程度的校園欺凌行為屬于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對于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法律規定可以進行治安處罰和工讀教育。但是,治安處罰一般并不會對在校學生適用,而工讀教育則是可選擇項,并不有強制性。所以,這部法律同樣難以落到實處,產生教育和懲戒的實效。
以上法律未能充分發揮實效,說明我國現行立法在校園欺凌問題上的的不足與疲軟。因此,有必要通過出臺一部反欺凌的專法,將針對校園欺凌的方案進行統一,并進行科學的分類和定義,同時佐以行政法規,讓教育部門的監管落到實處。
三.國外反校園欺凌法律借鑒——以美國校園欺凌立法為例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針對校園欺凌問題進行專門化,系統化立法的國家,其反歧視法的傳統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編,即“任何美國公民不得因種族,膚色或國籍受到他人歧視”,并在1972年教育法的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別歧視條款。9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出臺多部聯邦校園法案,包括《校園安全法》、《校園禁槍法》。1999年,科倫拜恩槍擊案發生后,各州都開啟了反校園欺凌立法,最早通過法案的是佐治亞州,隨后各州紛紛出臺反校園欺凌法案和反歧視法,對校園欺凌進行了界定和規范。截至2015年3月,蒙大拿州出臺反歧視法案,校園欺凌立法已經覆蓋了美國全部五十個州。
美國各州的立法采取的模式,均是先對校園欺凌進行定義,在五十個州的概念界定中, 幾乎都采用了“騷擾”、“恐嚇”和“欺凌”三個詞語。各州對于校園欺凌的定義主要來源于州立法和教育部門,比如《加利福尼亞州教育法典》。同時,法律均對校園欺凌的構成提出了程度要求和形式構成要件,譬如愛達華州法律要求學生不得對其他學生進行騷擾,挑釁,恐嚇和欺凌。而對于“欺凌”這一核心詞匯的定義,各州的標準各不相同,密歇根州僅僅使用了騷擾一詞來代替欺凌行為,而內達華州則以列舉的方式,對欺凌的種類進行了詳盡列舉。加利福尼亞州則在對欺凌進行范圍界定時,通過《加利福尼亞州教育法》第48900條的第(r)款中確立,欺凌包括書面行為和電子行為方式,并也包括第48900.2、48900.3或48900.4條中界定的由一個學生或學生團體實施的一個或多個行為,而這些行為必須在實際上造成了騷擾的程度,包括擾亂其他學生即受害者的學習生活情況。【2】同時,對于某些法典中未能具象化的欺凌模式,教育部門通過出臺一些規定,消除了法典過于抽象和篇幅限制的缺陷,譬如將欺凌具體規定為身體(踢打,推搡和吐)、言語(譏諷、惡意取笑、罵人和威脅)或心理(散播謠言、操縱社會關系、進行排擠和勒索恐嚇)等方面,部分州則詳細到了以上行為的損害程度劃分,通過設計一套復雜的心理評估系統,來對受害學生的心理狀況進行評估,從而確定精神欺凌的程度。
美國的校園欺凌立法主要分為三大類別,即預防性法律,救濟性法律和懲罰或者說制裁性法律,這一點和中國構想的規制體系大抵相同。其中,預防性法規主要是督促學校,教師和教育部門充分發揮作用,及時發現欺凌的產生或教導學生不要進行欺凌行為。其中,以《新澤西州反欺凌法案》做的最為完善。該法規定,學校雇員或簽約商應在看到或收到欺凌事件發生的相關消息后,當天即向校長口頭匯報,并在兩個工作日內提交口頭報告。【3】校長應當及時通知當事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并會面進行協商。同時每學年應當召開公開聽證會,對該學年度內發生的欺凌事件進行討論和報告,包括欺凌事件的后續處理,欺凌的性質,受害學生的撫慰情況和對涉事學生的處理。
救濟性法律上,新澤西州法律規定,學校應當承擔包括調查人員工資,心理醫生費用和醫藥費等撫慰受害學生的必要支出,并由專門的委員會對欺凌事件進行報告和形成處理決定。對于該處理決定,學生及其家長有權向州法院或民事權利司提出訴訟請求。
而制裁性法律,由于美國各州刑事責任劃分有所區別,因此差異較大。但是,在刑事責任之外,各州法律都規定了嚴格的懲治措施,除了民事賠償外,還包括針對其學生身份而規定的特殊懲罰措施,譬如強制退學,和社區勞動等。以《加州教育法》為例,有意圖對校園內他人實施暴力恐嚇行為,或進行口頭書面威脅,進行習慣性侮辱和猥褻的學生,應當受到休學或退學的處分。但是,除了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疏導外,大多數州立法中還規定了對加害者同樣需要進行心理疏導和教育,而這項工作的承擔著往往是社會義工或學校專門負責學生心理教育的教師。
通過對美國反校園欺凌立法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已經形成了以三類法律為骨干的反欺凌法律體系,同時,美國對于相配套的機制和反歧視的氛圍教育做的都相當完善,這同樣是值得借鑒的
四.對我國反校園欺凌立法的建議
(一)出臺較高位階反欺凌法,對校園欺凌進行科學定義
目前,我國反校園欺凌立法依舊薄弱,而各省教育部門出臺的文件中,也都未能統一什么是“校園欺凌”,它和一般暴力的區別在哪里,如何去判斷它的嚴重程度以及采取相對應的措施。我國法律原則性規定較多,對部分特殊行為的抽象性定義都相當欠缺,也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對其進行定義,這使得案件處理過程中,該行為是否屬于校園欺凌,都會爭論不休,影響效率。因此,法律應當具體明確,避免過于抽象,而即使法律規定的較為抽象,也應當像加州反欺凌法一樣,引用更具體的規定在其他規章中予以輔佐。
而要使得校園欺凌的定義歸于統一,這就對立法的位階提出了要求,而人大常委會近期同樣在討論在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時考慮專立反歧視法的議案,因此,出臺一部反欺凌法,具體明確地規定,何為校園欺凌,是很有必要而且可行的。
(二)加強監管者的責任和權限
校園欺凌發生在校園內學生之間,而最能直接管理學生的無疑是教師和學校,同時,教師的視而不見和不當舉措,也可能成為校園欺凌產生的助推手。對于教師和學校管理不力而發酵的欺凌行為,同樣應當要求教師承擔責任。新聞和相關資料顯示,部分學校和教師都會選擇隱瞞欺凌事件的發生,唯恐帶來聲譽的損害,這種行為本身即違背了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對于教師隱瞞情況,未盡到合理職責的行為,應當按照相關法律予以懲罰,譬如撤職或解聘。【4】
法律應當要求學校建立相應的反欺凌體制,包括報告機制和處理機制,而在此之外,力所能及的學校應當進行氛圍教育,開辦反欺凌講座或相關安全課程。同樣的,在要求監管者承擔更大的責任時,同樣應當給予其更高的權限,譬如對欺凌當事學生的懲戒權,美國中小學校園的校長均有權要求欺凌者休學乃至退學,而在國內,一方面由于義務教育的約束,一方面在于社會環境和輿論對欺凌看的并不重,使得校方在懲戒學生時往往毫無力度,流于形式,喪失監管者的威嚴,使肇事者更加肆無忌憚。
(三)使對在校生的處罰不流于形式化
前文分析中已經指出,雖然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國已經規定了工讀等懲罰措施,但是由于我國的傳統向來是恤幼,因此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落實執行,都顯得過于寬松。而這種“寬容”,往往并不伴隨著有效的改善和預防機制,使得行為人的情況并不會有所好轉,反而成為未成年人和在校生肆無忌憚的保護傘。
國外學者曾經對未成年人刑法進行過研究探討,諸多案例中,施暴者大多都未滿16周歲,因此無需對故意傷害等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對于這部分因年齡而未受到處罰的未成年施暴者,對于其按照法律規定應當受到的管教,應當落到實處地執行。而在刑罰之外,輔佐以行政責任,通過行政法規的規定,對管教不力的學生監護人,可以考慮進行罰款。欺凌者在受監管期間再犯的,對監護人和管理者進行處罰,從而遏制極高的再犯率。
校園欺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事件或行為,數十年來教育學者和社會學家的研究都證明了這種社會現象出現的必然性和難以自行消失的特性,這就要求我們的法律必須對其進行更為詳盡的規制,校園欺凌的主體,無論是欺凌者還是被欺凌者,都是最應當得到呵護和照料的孩子,欺凌行為的頻發也要求法學界對此做出反應,在社會學和教育學對于校園欺凌研究已經如此深入地今天,同樣應當從立法規制的角度,認真思考治理路徑,規范對事件的處理,建立預防機制,構建一套成熟的規制校園欺凌的法律體系,無疑是重中之重。
腳注:
【1】:顏湘穎;姚建龍:《“寬容而不縱容”的校園欺凌治理機制研究——中小學校園欺凌現象的法學思考》,中國教育學刊2017年01期
【2】:尤嬌嬌:《美國反校園欺凌立法對中國的啟示》,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7年09期
【3】:陳榮鵬,方海濤.美國校園欺凌的法律規制及對中國的借鑒:以2010年《新澤西州反欺凌法》為研究視角[J].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15.28
【4】:任海濤:《“校園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責任》,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