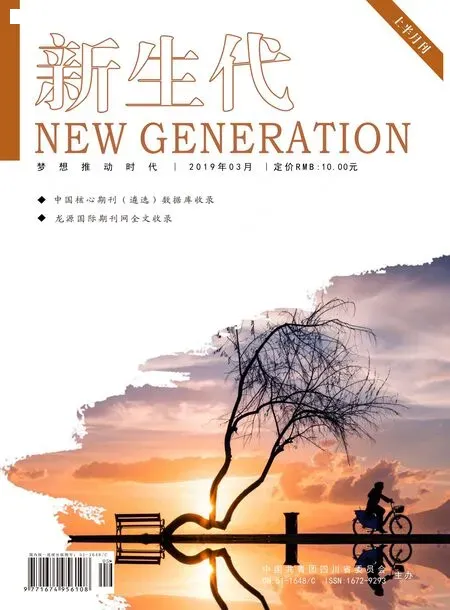共謀共同正犯理論概說
伍梓瑄 西北政法大學 陜西西安 710063
所謂共謀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謀實行某犯罪行為,但只有一部分人基于共同的意思實行了犯罪,沒有直接實行犯罪的共謀人與實行了犯罪的人,一起構成所共謀之犯罪的共同正犯”。
圍繞日本《刑法》第60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者,皆為正犯”,存在兩種不同的解釋。實質性共同正犯論立場著眼于“共同”這一表述,主張僅僅參與共謀而未參與實行者也可構成共同正犯,此即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與其截然對立的,就是形式的共同正犯論(即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說)。該說重視條文中“實行犯罪”的表述,認為只有參與了實行行為即構成要件行為,才屬于共同正犯,故又稱實行共同正犯論。
自大審院通過判例確立共謀共同正犯概念以來,直至草野豹一郎首次賦予其理論正當性,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說一直是日本刑法學界的絕對主流觀點。經過數代刑法學人的不懈演論,承認共謀共同正犯的存在并限制其成立范圍的主張已經成為通說。但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依然無法說服對方,由此展現出共謀共同正犯理論的學術困境。
為了維護自己的學術立場,德日刑法學者提出了各種理論依據,其中具有較大學術影響力的觀點如下。
一、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
(一)協心協力作用說
該說是日本大審院時代通過判例確定的共同正犯關系的理論根基。大審院推演了“共謀”者的罪責,認為“數人既有共謀的事實,其共謀者中不論何人實行之,均為共謀者全體的行為”。該說認為,通過相互之間“協心協力作用”,共謀參與者與行為實行者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共同犯罪,因而參與共謀者必須作為共同正犯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共同意思主體說
共同意思主體說由日本學者型法官草野豹一郎提出,該說第一次在學理上將共謀共同正犯理論正當化,改變了共謀共同正犯判例僅僅影響司法實務領域,而在學界廣為學者反對的狀況[]。該說主張,各犯罪人在共同實行意思下集合,在共謀、協議的基礎上已經成為相倚相援、同心一體的共同犯罪集體。草野氏的表述如下:“一切社會現象,不僅是由個人的單獨行為所產生的,又可以基于數人的共同行為而產生。此種共同現象,……在民商法中則規定為法人或合伙制度。而自刑法上觀察此種現象時,則產生共犯的觀念”。作為共同意思主體的活動,其中任何人的實行都應視為全體成員的實行,至少由一人實行犯罪,全體成員就因此成立共同犯罪。但是由于犯罪集體的存在是暫時性的,因而刑事責任仍由各犯罪人各自承擔。
(三)間接正犯類似說
通過1958年的東京“練馬案”,日本最高裁判所對共同意思主體說進行了修正,提出了間接正犯類似說。該說的主要觀點是,在兩人以上共同謀議實行犯罪的情況下,將所有共謀者的行為視為一個整體行為,參與共謀而未實行者在向參與共謀且實行者提供犯罪方向、強化犯罪意圖、謀劃犯罪方法方面,具備類似于間接正犯的性質。在不以自己之手實行犯罪,而是利用他人實現犯罪的場合,利用他人者,應當視為實行行為之一種形式。在于他人合意共同利用而實現結果之意義上,可將共謀者視為共同實行者。易言之,共謀而未實行者在共同犯罪中,將實行者的實行行為作為自己的犯罪手段,進而實現完整的共同犯罪,因而在其刑事責任的成立與承擔方面,應與共謀且實行者等同處理。
(四)行為支配說
日本學者平場安治主張:“共同正犯之所以就其他共同者之行為亦須負其責任,乃因各共同正犯對于實行行為具有共通包括的行為支配之故……若對于構成要件行為有目的性支配則已足,因此無論自己親自所為部分或其他共同者所為部分,只要具有包括性、一體性之共同目的支配,則最終即使自己并無任何動作,亦可因支配他人之行為以遂行自己之犯罪而成為共同正犯”。行為支配說的基本立場是:“如果共謀者使得實行行為如其本人之意而完成,則其應當被視作基本構成要件共同實現者而以共同正犯論之”。若要成立共同正犯,共謀者只須對實現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整體具有支配性的作用、操縱實行者以實現犯罪目的即可。
(五)實質的正犯說
實質的正犯說的趣旨在于考察共謀者是否在共同犯罪整體中起到了實質性的重要作用,其實質是對“實行行為”的概念加以擴張解釋,將共謀行為與實行行為等量而觀,主張共謀者只要在客觀上對共同犯罪起到重要作用、主觀上具備完整的犯罪故意,便成立共同正犯。
(六)包括的正犯說
大谷實教授是該說的代表人物。該說認為:日本《刑法》第60條中的“共同實行”,是指二人以上的人形成了犯罪合意,只要實際存在共同實行的意思(即共謀),通過相互利用、相互補充他人的行為,則無論是否分擔了實行行為,都可成立共同正犯[]。
(七)價值行為說
該說認為,實行行為的判斷標準,是該行為是否對社會具有價值,亦即該行為是否對社會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同理,要判斷共謀行為是否具備正犯性質,其標準是共謀行為是否具有構成要件行為的價值。如果共謀行為符合上述標準,則當被作為實行行為予以定罪處罰。
(八)優越支配共同正犯說
大塚仁教授主張優越支配共同正犯說。他否定了單純共謀行為可以成立共同正犯的觀念,而從規范視角認為:“沒有擔當實行的共謀者,當其在社會觀念上對實行擔當者而言處于壓倒的優勢地位,對實行擔當者給予了強烈的心理約束使其實行時,從規范的觀點就可以說存在共同實行,可以肯定為共同正犯”。當實行者受制于共謀者的壓倒地位,而相當于共謀者實現其犯罪意圖的工具時,共謀者的共謀行為具備共同正犯的性格,應被視為共同正犯。
二、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說
(一)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
日本《刑法》第60條的立法意圖,是不能把沒有實行犯罪的人作為共同正犯處理。之所以在司法體系中允許解釋刑法條文的權力,是為了保障立法權確立的基本人權。從自由保障的視角來看,共謀共同正犯不具備正當性。
(二)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違反了行為原理
所謂行為原理,是指刑法只應對表現在外部的侵害社會法益的行為進行處罰,其理論意義是禁止處罰思想犯、腹誹犯。如果承認共謀共同正犯,則有可能對僅僅參與共謀而未對犯罪實行產生重要作用的人科處不當的重刑。甚至有可能僅僅因為嫌疑人與實行者有較為密切的社會聯系、處于同一團體、存在朋友關系,就對嫌疑人動用國家公權,不當地開啟刑事追訴。
(三)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違反了責任原理
近代刑法確立了個人責任主義,其理論意義在于確立應當針對個人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原理。共謀共同正犯說實質是對團體或集團的關系者進行處罰,將個人應承擔的刑事責任擴張到團體責任乃至連帶責任,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
(四)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使其易與教唆犯、幫助犯產生混淆
論者指出,司法實踐中,正犯大多數情況下也是指教唆犯和幫助犯的,共謀共同正犯肯定說也承認這種定性。但是這種思路只應在警察搜查的司法運用中獲得承認,而嚴謹的刑法學者應警惕這種模糊化的理論進路和處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