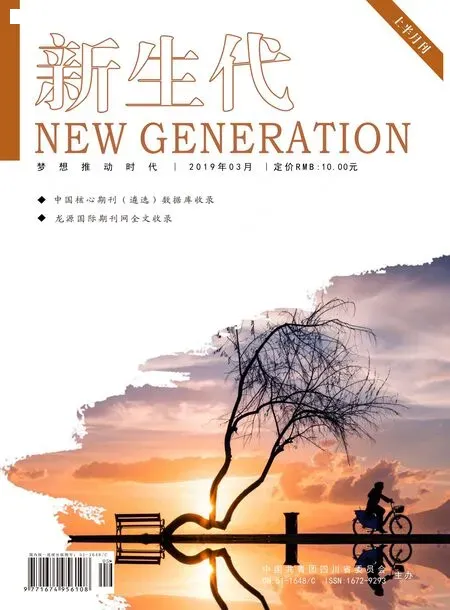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民事司法適用研究
胡澤霖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 云南昆明 650500
近年來,隨著環境公益訴訟實踐的不斷拓展,環境修復責任逐漸成為環境損害救濟的重要責任形式進入司法裁判的范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借助民法恢復原狀來實現環境損害的修復性救濟,為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民事司法適用提供了一定的規則指引,但環境損害修復在法益救濟、標準、責任方式各方面都和民法損害的恢復不同,和民法意義上“恢復原狀”的含義有本質區別,已引發大量理論爭議和實踐困惑[1]。本文旨在總結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實踐經驗和困境的基礎上,厘清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的可選路徑,以便發揮環境修復責任方式對環境損害的救濟功能。
一、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的實踐模式
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大量適用是近年來環境民事司法的一大特點。“環境修復在私益訴訟中基于民事事務的自主品格而具有可選擇性,在公益訴訟中基于社會公益的考量而被塑造為核心責任方式”[2],受到了司法實踐的特別青睞與靈活適用。
(一)直接判令被告履行環境修復義務
直接判令被告履行環境修復義務不僅可以徹底解決環境受到損害的問題,而且可以避開對環境修復費用是否必要、合理的判斷以及加害人可能產生的異議。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判令被告在履行環境修復義務,比如清除污染,恢復土地和水體的原始生態功能,在植被破壞地按照受損植被的種類、數量進行補種復綠,并在確定期間內進行養護等。例如,吉林省某固體廢物污染責任糾紛((2017)吉02民初32號)一案中,法院直接判決被告對傾倒飛灰螯合物影響區域內的淤泥進行清理。直接判決被告承擔環境損害修復義務不僅考慮到環境修復的標準和效果,還需要考慮到被告不履行修復義務時的救濟措施,在司法實踐中面臨的困難較多。
(二)判令責任人采取替代性修復措施
當環境要素遭到污染或破壞,無法直接就地修復環境損害時,法律允許采取 “替代性修復”措施。例如,昆明中院在審理礦產資源案件時,被破壞的礦產資源無法修復,法院建成“環境公益訴訟林”,通過在異地進行補植林木的方式達到生態環境的總量平衡,實現修復生態環境的訴訟目的。又如,在中華環保聯合會訴無錫市蠡湖惠山景區管理委員會生態環境侵權((2012)錫濱環民初字第 0002 號民事判決書)案中,管委會提出了異地補植方案,景區管理委員會在主管單位和中國環境保護聯合會批準的不同地點提出了補種方案,并經法院確認和批準。替代性環境損害修復責任固然有利于具體糾紛的解決,但能否正真實現修復環境損害的效果值得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進一步檢驗。
(三)判決被告承擔環境損害修復費用
環境損害修復是一項技術性強、耗時較長的工程。在責任人無力修復或者不愿修復時,法院可以直接判決責任人承擔環境損害修復費用。承擔環境損害修復費既體現了對受損環境的救濟,又把行為責任轉化為經濟責任,方便執行,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廣泛運用。例如,在徐州市某環境污染責任糾紛((2015)徐環公民初字第6號)案中,法院責令被告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共計人民幣105.82萬元,支付至市環境修復公益金專項賬戶;在荊州市某水污染責任糾紛環境公益訴訟(2016)鄂1002民初1947號)案中,法院責令被告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賠償因其違法行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損失202050元,賠償款付至荊州市沙市區財政局環保專用賬戶用于修復被損害的生態環境。
二、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的現實困境
盡管各級法院將修復環境損害視為恢復原狀的一種形式,在環境民事司法中普遍適用,但恢復原狀是針對傳統財產受損的制度設計,以生態環境這種特殊財產為對象的環境損害修復在司法實踐中還遭遇諸多現實困境。
(一)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法律性質不明
針對侵害財產權益的情形,一是恢復受損財產的權能,如賠償受損書籍之同樣的書籍;二是在不能修復之情形下,進行金錢賠償。對人身權益的恢復原狀主要有精神損害賠償以及消除影響、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但是環境損害不同于傳統的民事侵權,傳統民法意義上的恢復原狀是通過修理恢復受損財產的原有狀態,生態環境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具有整體性與不可逆轉性,這種法律意義的恢復原狀用于受損生態環境的修復,不僅理論上不適用,在科學技術上也無法做到。
(二)履行環境修復義務的適用范圍受限
在環境民事司法中,直接判令被告履行環境修復義務,雖然具有目的正當和易于裁判的優勢,但是還需要一些前提條件。在傳統的財產侵害中,受損財產范圍特定,狀態穩定,與外界隔絕,受損原因單一,恢復原狀相對較為容易。生態環境不同于傳統的有形財產,既沒有特定的范圍和穩定的狀態,也沒有與外界相隔絕的獨立空間,其原狀究竟如何難以界定。就近幾年案件來看,除了要求綠化、補植的資源類案件外,多數案件中的恢復原狀請求事實上是無法實現的,尤其是那些范圍指向寬廣的案件。直接依據《民法通則》或《侵權責任法》判決被告對所污染的土壤、大氣、水體和海洋等自然環境承擔清除污染物、恢復其功能的行為責任,或者對破壞生態的侵權者判令其恢復環境原狀的案件甚少,凸顯直接履行環境修復義務的適用范圍受限。
(三)采取替代性修復措施的適用效果存疑
環境修復必須有整體考慮。環境的各個部分是相互關聯的,例如土壤和地下水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無論污染或修復如何,都不應完全分開。當環境因素受到污染和破壞而無法完全修復時,可以允許進行其他環境修復。環境破壞的替代修復措施能否達到“修復生態環境”的效果,值得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調查。理論上,由于生態的開放性和完整性,任何有效的生態恢復都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更大的規模和更長的時間段,并且局部的,零散的“修理”經常消耗資源并且勞動力無效。在實踐中,他們大多依靠生態環境來修復基地,使被告能夠以另一種種植苗木的方式承擔環境恢復的責任。在沒有考慮林木的長期保護和重新種植后重建生態服務功能的情況下,在幾個月內重新種植綠色植物。在不同地方重新種植確實具有科學合理性,但通常只適用于破壞國有林地的情況。在林權改革的大環境下,林地“有自己的主人”,不同地方的重新種植缺乏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律制度的基礎。如何解決不同地方補種與森林權利所有權之間的法律和有效聯系,仍然有必要嚴格證明[3]。
三、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的可選路徑
侵權責任制度設計忽視了環境損害的救濟和保護,應當從民事責任的角度打破這種情況的變化。生態破壞必須受到與生態破壞有關的財產損害的完全利益的保護。改變把環境修復作為恢復原狀手段的性質定位,明確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并不是要恢復原狀,而是修復受損環境的功能和價值,從而促進生態的恢復。生態恢復的基礎是承認生態環境的價值,并通過修復和改善受損的生態環境,恢復原有的生態結構和基本生態功能,從而提升生態環境恢復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一)生態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適用路徑選擇
環境損害類型復雜,情況各異,但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民事司法適用大致可有以下三條路徑可選: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判決被告直接修復環境損害是環境訴訟的理想目標;如若條件不具備或者被告無意愿,則由法院判處賠償環境損害修復費,由國家統籌利用這筆資金進行生態環境修復;在以上兩中情況均不能實現的情況下,法院可根據“損害擔責”的環境法理判決被告承擔補償性質的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當責任人提出用支付修復費用代替修復行為時,訴訟應當圍繞修復的費用進行審理,然后再由法院委托專業機構修復。如果將生態環境修復的代履行納入到訴訟請求,作為費用請求的衍生請求,其訴的性質應當為一種給付之訴,只有這樣該訴訟判決的既判力才能得到真正落實[4]。如若條件不具備,或者被告無意愿,毋寧由法院判處罰款,由國家統籌安排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這筆資金。
(二)合理界定生態環境損害修復的標準
生態環境損害修復應當根據環境污染侵權的特點,現有技術,人體健康和安全等因素來確定環境標準。筆者認為,如果受損的環境資源有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恢復的環境資源應符合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最低標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標準不斷變化,標準要求不斷提高,因此,在將標準應用于不同時期時,應適用侵權實施標準。如果使用維修時的高標準作為恢復的基礎,那么對侵權人顯然要求太高。但是,由于環境資源具有重要的生態和公共利益屬性,此外,生態環境治理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司法實踐可以要求侵權人以侵權行為的恢復為基礎。通過在恢復時適當平衡標準來提高環境資源的恢復水平。如果沒有相關標準,受損的環境資源應恢復到能夠發揮正常生態功能的狀態。只要達到這種狀態,就可以認為已經恢復了[5]。
(三)制定切實可行的生態修復方法與修復程序
第一,評估損害。這個階段主要是確定是否存在重大的生態環境破壞,是否可以扭轉損害,以及修復損害的成本,無論技術上是否可行和可操作性,其實質是確定生態恢復的條件是否可用。通過評估損害的具體量化來確定是否啟動生態恢復計劃。第二,制定方案。如果確定損壞確實存在且可以逆轉,則應啟動維修計劃和特定維修措施。所制定的方案可以是多樣的,以便進行科學的選擇。第三,選擇方案并予以實施。在制定恢復計劃之后,應評估恢復計劃,以考慮公共健康,安全和經濟成本。監督機構在實施過程中可以進行分階段接受和程序監督。第四,修復結果的報告及驗收。修理完成后,負責維修的人員應以書面形式報告維修結果。對維修過程和結果進行客觀,系統的總結,并由具有驗收資格的當局進行現場調查,從而決定通過還是不通過[6]。
結 語
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民事司法適用對于環境民事法律體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環境損害修復責任民事司法適用的案例分析和檢視,現行民事法律體系不足以承載環境修復的功能。環境損害修復責任作為一種新型的責任方式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生態效益,但在民事適用中面臨著法律依據不足、司法裁量不當等問題,需要進一步通過制度來完善和保障。例如通過法律明確境損害修復責任,加強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聯動等措施。隨著環境損害修復責任的完善,環境損害修復責任司法適用的重要性將會更加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