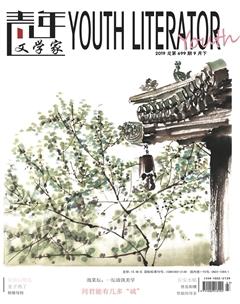土特產
陳泳甫
就整個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來看,自然科學是舶來品,而道德倫理卻是“土特產”。
舶來品自外而來,不穩且易變,其共識的達成也往往迅速。而相較于舶來品,土特產的特點便是根深蒂固,因此道德的分歧也就普遍而難以避免。
“鄉愿,德之賊也。”能被一鄉人稱為謹愿的人,在孔子看來是老好人,是偽君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一般人眼中的常態,在孔孟眼里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令人不齒的社會禍患。類比于今,則各種彈性懲罰備受爭議,被害與受害兩方陣營劍拔弩張,以致局內之人頭暈目眩,局外之人寄以嘲諷。
道德的本質是一種“契約精神”。道德分歧的根本便在于這種契約的彈性。針對此種彈性,儒者要“復禮”,墨者要“兼愛”,道者期以無為至有為,無一不助長了這種彈性,只有申韓,用規則與戒律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這種彈性,使道德退居幕后,使分歧置于判臺。
然而,土特產之所以為土特產,便在于其流通領域的廣泛。
社會行為可以有規則與戒律,而文藝領域,戒律確無從插手。
法朗士曾言:“真正的批評家只敘述他的靈魂在杰作中的冒險”。他不齒法官,不齒道德家,恰如王爾德所認為的“倫理之于藝術家是一種不可寬恕的風格怪癖。”
分歧自此產生,在“偽藝術家”那里,準時會變成時間的盜賊,愚蠢會被拔高頌揚成一種哲學。如梁問道所擔心的那樣,現代審美的敗落,將從宣揚丑開始。于是在藝術的鐵屋子外,戒律不敢入內。宣揚無道德的自由藝術時,只要稍加批評,便被扣上看不見皇帝的新衣的愚蠢之人的帽子。
林崗在“雙典批判”中提到過,文藝作品的修辭越是精妙,如果它與人類基本道德存在分歧,那么它的毒性就越大。如同加了糖丸的毒藥,飲者只賞其甜味,而不知覺中毒素也隨之進入體內。
因此,盡管康德極力推崇的判斷標準中道德的善和情感的美常常錯位,但如果分歧永遠存在,或越拉越大,那么土特產只能一直土下去抑或是腐敗變質。
如是,則我們應有一個基本的準則—人類的價值共識,為土特產包裝,使其“土”而不俗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