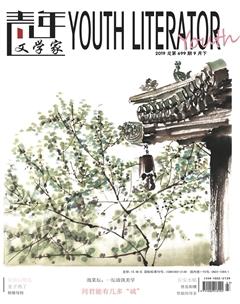堅(jiān)毅的母親
作者簡介:張瑞芬(1983-),女,本科,就職于陜西畫報(bào)社,編輯記者。工作十余年,熱愛生活和文學(xué),多篇文章見諸報(bào)刊。
從小,我是和父親走得近些,他見多識廣、幽默風(fēng)趣且特別疼愛孩子們。母親是我們常常在吃飯、穿衣、睡覺時(shí)才呼喚的。
我的母親平日里話語不多,一心照料著全家人的生活起居。我對她的認(rèn)知是從我11歲開始的。那年夏天的一個(gè)傍晚,我和弟弟在家里玩耍。我小姨一路哭著來到院里喊著母親,極盡悲痛,嚇得我倆呆站在一旁。母親從廚房急匆匆出來,雙手拿著搟面杖,當(dāng)聽到舅舅去世的消息頓時(shí)臉色失常,她一邊安慰小姨,一邊張羅著安排后事。在后來的很多天,我經(jīng)常看到母親的眼睛紅腫,卻未見她放聲大哭過,這讓我很擔(dān)心。老來失子的外婆一人守著高墻大院,整日以淚洗面寡言少語。母親非常擔(dān)心她并一再要求她來和我們同住,外婆堅(jiān)決不肯。從此,母親隔三差五去外婆家探看。那些日子,我和弟弟都變得乖巧起來以此寬慰母親。
每到寒暑假,我便被母親委以“重任”去陪伴外婆。那些年外婆很是傷心哀嘆,但依然給我做美食、講故事,帶我探親訪友。然而她還是迅速地衰老了,消瘦了,背更駝了。當(dāng)時(shí)我不過十來歲,不知如何寬慰她更體會(huì)不到她的悲慟之情。那時(shí)起,我也看到了母親的不易,不再與她頂嘴,并主動(dòng)做起家務(wù)活來。
我上大學(xué)時(shí),外婆患上老年癡呆癥,從此便只識得我母親。母親把她接來和我們同住,細(xì)心照料。那年夏天,傍晚的陽光照在紅墻灰瓦上,我們坐在院中歇息,忽然外婆心疼地說:“閨女,你看瘦成啥樣了?”我忍不住在一旁哈哈大笑,喊道:“老媽,你這么胖外婆還嫌你瘦嘞!”母親也笑得合不攏嘴。后來我和母親常常聊起這個(gè)場景,特別溫馨而感懷。
我們幾個(gè)孩子頭疼腦熱,母親總是立即帶我們?nèi)バl(wèi)生院看病,而她自己生病卻很少去門診拿藥,常搜集一些土藥方,比如感冒很嚴(yán)重時(shí)就會(huì)沖服生谷粒,然后倒頭睡去。我很是懷疑,然而她的確神奇般地很快就康復(fù)了。有一年端午節(jié),母親不知從哪里聽說蜈蚣、蛇皮、蝎子浸泡的藥酒喝了能排解體內(nèi)毒素、強(qiáng)身健體,于是大玻璃缸里便漂浮著這些東西的干尸,看得我直發(fā)怵。母親說“你來兩口”,嚇得我轉(zhuǎn)身飛快逃離了。后來,家里經(jīng)濟(jì)寬裕了,她才停用這些土藥方。
近年來,母親的身子一年不如一年,肥胖的身軀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但她還堅(jiān)持要干農(nóng)活,做家務(wù),不愿閑待一刻。2016年的夏天,她的腿疼得實(shí)在扛不住,才答應(yīng)我到西安找名醫(yī)治病。剛來到時(shí),她拄著拐杖只能忍痛走大約30米遠(yuǎn),我告訴她在家看電視其他的不用管。中午我下班趕回家做飯,到家里時(shí)她已經(jīng)將食材備好正坐在凳子上歇息等我回來。我一邊迅速把飯做好,一邊絮叨著讓她好好靜養(yǎng),叮囑幾句又匆匆上班去。那時(shí)她安安靜靜地看著我忙來忙去,并不作聲,我只當(dāng)她聽了進(jìn)去也沒多想。
兩個(gè)月后,母親的腿慢慢好起來,出去散步能一口氣走100多米遠(yuǎn),她便開始忙碌起來:蒸包子,包餃子,做花卷,換著花樣給我做飯。我一再叮囑她的病是須靜養(yǎng)的,她很認(rèn)真地說道:“你上班這么辛苦,工作上我不懂,家務(wù)活我還是能給你分擔(dān)些吧!”也就是從那時(shí)起,我急躁毛糙的脾性被修煉成了沉穩(wěn)細(xì)心而有耐性。半年后在母親的一再堅(jiān)持下,她又回到了老家安享晚年。一周兩個(gè)電話我是定要打的,閑來無事就是聽聽她的聲音,也會(huì)趕上小長假回去陪她嘮嘮嗑。
又是一年好光景,沙沙作響的樹葉在枝頭婆娑搖曳,布谷鳥“布谷布谷”的叫聲響徹了整個(gè)村莊,燕子飛到屋檐下做成精致小窩和兒女們在那里嘰嘰喳喳過起日子,它們時(shí)不時(shí)在空中展翅飛翔。我和母親在院子里聊著鄉(xiāng)鄰右舍的家常事。母親仍不愿停歇正拿著簸箕撿拾菜種,我站起來拎起掃帚將院落打掃得干干凈凈。陪伴母親的日子里,我的心頭像用清泉洗過般安寧舒暢,祥和而幸福,柔軟而堅(jiān)韌。
時(shí)光緩緩流過,母親年老,我已成年離家,而我們彼此時(shí)刻牽掛在心。我想,這世間的母親大抵是相似的,她們懷揣著一顆極為純真的赤子之心養(yǎng)育著兒女,堅(jiān)毅得陪護(hù)著他們走過無數(shù)個(gè)風(fēng)吹雨打的日日夜夜,一代代繁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