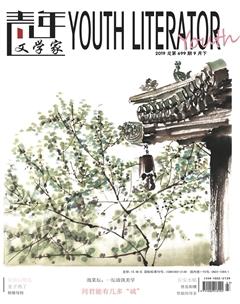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鐘鼓樓》的歷史書寫與文化書寫
摘? 要:《鐘鼓樓》特別展現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背景下老北京的人文風俗畫,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文化思考的角度揭示了普通小市民生活里蘊含的新變與復雜的心態,既有理性的思考,又有感性的闡發。
關鍵詞:歷史;文化;交融
作者簡介:李優雅,南華大學語言文學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7-0-02
劉心武在接受《上海文化》訪談的時候曾提過“我不希望我被放到那種單一的視角里面去觀察”,確實,劉心武對《鐘鼓樓》的書寫是既以歷史的分析的眼光看待處于改革拐點的北京的人和事,又帶著感發式的面對斜陽般的惆悵。
歷史——并不表示塵封的過去,而是過去、現在、未來緊緊關聯。它注重事件的前因后果,注重事件的過程和影響,是連貫的、相互滲透的。在同一個人身上,歷史表現為過去的行為對之后造成的結果;在一定的集體生活區域,歷史表現為不同人行為的相互作用。從影響傳遞的過程看,歷史是直觀的,是動態的,從思維方式看,它是理性概括的。
文化,相比歷史它的存在形態也許有些隱蔽,同時也更加豐富,它在建筑里,在一茶一飯里,在談話里……文化是靜默的,潤物細無聲的,也最是直指人心的。從表現方式看,它是象征的隱含的。
有研究者指出,劉心武屬于“理性型”作家,誠然,劉心武善于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概括性的思維、分析性的話語、歷史的眼光解釋人物的行為,但這并未掩蓋他內心涌動的對于老城老街的復雜情感。
一、歷史書寫:被分割的時間與流動的時間
《鐘鼓樓》以胡同里薛家的婚宴為中心,將胡同里不同身份的住戶的過往與正在經歷的事以倒敘、順敘、預敘的方式濃縮在了卯辰巳午未申共12小時內。時間是具體的、順序的、規整的,表現出歷史的特點。如卯時引出的是薛大娘辦婚宴的背景、婚宴廚師路純喜的人生經歷以及京劇演員澹臺智珠追求藝術創新不被理解的苦惱;隨著婚宴準備工作的推進,辰時娓娓道來了薛大娘與大兒媳孟昭英間的矛盾;巳時才聚焦到了婚禮的主角——新娘潘秀婭,講述了她選擇嫁到薛家的前因后果;午時詳細介紹了宴席的菜式和親屬來客;未時純粹介紹了人們居住的生活場所——四合院的建筑特點、功能分區、它與北京城的關系;申時是見證了北京歷史發展的老人們的自我回顧。
上述事件乍一看似乎跟中心事件——一個普通北京家庭舉行的結婚儀式沒什么聯系,但仔細梳理發現,劉心武的創作意圖并非要將胡同里的居民們與婚禮扯上必然的聯系,只是將婚禮事件作為一個引子讓胡同里的人一一出場,因此他刻畫的不是其他人家與薛大娘家存在的矛盾或利益糾纏。不是建立表面的人與人的行動關系,劉心武更為注重的是深層的聯系,人與人是無關而又相關的。薛大娘生活穩定,操心著孩子的事又喜又愁;于大夫不滿于四合院有些熱鬧吵嚷的環境,期待搬入有自我空間的樓房;慕櫻在愛情里屢屢受挫,并挑戰著社會的愛情觀;荀磊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個人進取意識萌發,致力于翻譯事業。以上看似無序、沒有關聯,實際上表現的是歷史轉折期不同的生活狀態,更能表現社會的復雜性。改革開放后的北京中下層老百姓生活日漸紅火又暗含矛盾,意識形態緊繃的氛圍放松,物質條件轉好,小百姓進取心強,實現自我價值的施展空間大。
正如《鐘鼓樓》里說“任何社會、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種狀態中。在流逝的時間里,社會生活中總是充滿了矛盾沖突,作為個人,他在自己的命運發展中,總是既會有喜樂,也會有哀愁”,從上午5時到下午5時縱橫展示了歷史變遷,交代了各個人物的過去經歷與現在處境以及暗示未來行為趨向,它不是截斷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故事相互聯系、持續地發生,體現了一種流動的歷史感、發散式的歷史觀。
二、文化書寫:象征式的行為與人格化的場景
一定環境下的行為都不是無意味的,人創造了環境,又受到環境的制約,環境是物質文化的一種,人與環境的關系實則為人與文化的關系。張開焱在《文化與敘事》提到:“文化不僅是指外在地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有形世界的東西,還指內在地改變了人類以一種超自然的方式去感知世界并對其做出反應”,因此人的行為某種程度是文化象征的具體化。
薛大娘對婚禮極其重視,對一切環節小心翼翼,精打細算。挑日子為婚禮討個好彩頭,也奠定了以后幸福生活的基礎:“在那張紅色的日歷面前,她把那些偶數讀了幾遍,心中漾出一種安適感”;“薛大娘把小轎車的到來,當作這天婚事中的頭一樁大事”,轎車是接親儀式必不可少的工具,又能體現家庭實力。華夏文化是偏冷靜、克制的日神精神,通常以嚴肅、含蓄的形式進行儀式而非狂放、戲謔,面對重大事件他們總是;宴席上安排四十六道菜不重樣,四輪熱菜外加冷盤,飲食變為不只是滿足口腹之欲,而是一種展示,一種祝愿,一種地位,也是古老禮樂文化的延續。受農耕文化的影響,薛大娘擔憂不確定性,求穩,依賴著外物所給的啟示——也就是吉兇預兆;另一方面,善于經營生活,在有限的條件里攪動出五彩紛呈來,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忍耐與樂觀。
潘秀婭屬于另一種小市民,夾在傳統市民文化和新興大眾消費文化間,有浮躁、虛榮的特性。盡管已經擺脫了傳統男外女內的生活,走向了社會崗位,局限于照相館柜臺,對社會生活的接觸面少,眼界狹窄;不寬裕的經濟與不高的文化水平賦予了潘秀婭式的女性務實的擇偶觀:“她要在夠得著的范圍內,找一個盡可能好一點的對象”、“她要結婚。她要成家。成家過日子”;一方面無意識地被裹挾在社會新興發展的洪流里,講攀比,期盼得到夫家給的“瑞士雷達小金表”的行為象征著潘秀婭這類小市民追求穩定的生存保障,將物質的滿足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要義。
有研究者將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觀念文化,《鐘鼓樓》的四合院與鐘鼓樓屬于物質文化,但由于它們的布局與功能是人心理結構的投射同時也影響著人的生活方式,它們也屬于觀念文化。鐘鼓樓在物質文明不夠發達的年代,承擔著公共報時的作用,不求時間精確,人的生活也并不完全依賴時間,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四處響起了改革的號角,社會抓生產抓效率,對時間的依賴空前增強,“如今鐘鼓樓休息了,它們僅僅作為一種古跡而存在”,“即便公共計時器遍布每一個路口,人們也還是要擁有自己獨享的計時器”。新的時間觀、新的生產方式出現,個人本位逐漸清晰,追求、奮斗、上進這類新的社會目標闖入了安穩的胡同與四合院,青年知識分子或干部在這股影響下表現為積極改造周遭世界的熱情,普通百姓則著眼于工資的提高、吃穿用度的轉好。生活的場景不只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精神世界的一角。鐘鼓樓被人格化了,它仿佛一個遲暮的老人,依依不舍地就要告別夕陽,這也折射出改革階段社會新舊交替的矛盾心態。
三、歷史書寫與文化書寫的交融
《鐘鼓樓》的歷史書寫與文化書寫不是截然分開的,如果說歷史書寫好像是四面八方的、奔騰不息的水流,文化書寫則是水流里的暗涌。《鐘鼓樓》的歷史書寫表明胡同里四合院里人與人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也上升到一個哲學高度:“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單獨地存在著。他必與許許多多的人共存于一個空間之中,這便構成了社會……而這種人類社會的流動變化,從整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歷史;從個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命運”;順著五四時期更多書寫普通人個人的沉浮的文學脈絡,面對工業文明的全面來襲,劉心武更為關注的是大眾、平民,他聚焦的不是某個特定的人,而是許許多多不同文化心態的類型化的人,有偏安封閉的,有浮躁虛華的,有激流勇進的……
劉心武站在歷史的高度冷靜俯瞰,依據跨越古往今來的歷史跨度,卻另辟蹊徑,不寫歷史重大事件與改革英雄人物,寫的是平凡瑣屑。在吃穿住行、細水長流的市民文化里把握歷史,又在歷史的維度里進行文化反思,批判守舊批判浮躁,像老舍一般鋪寫世態民情,與老舍不同的是劉心武表現了變與不變的歷史觀,開頭與結尾都提到了“鼓樓在前,紅墻灰瓦。鐘樓在后,灰墻青瓦。”由于其歷史功用與古舊的建筑特征,簡單幾筆勾畫,讓人生出靜默感、莊重感。社會生活、人的心理活動是不斷流動的,而鐘鼓樓作為古老的報時工具已經被閑置,只作為文化象征存在。它的靜與周圍的動形成對照,它的不變與周圍的變形成對照,傳達出作者的變與不變對立統一的歷史觀及對傳統文化的略帶感傷的懷念。
參考文獻:
[1]劉心武,楊慶祥. 我不希望我被放到單一的視角里面去觀察[J]. 上海文化,2009(02):117-127.
[2]萬海洋. 歷史流變中的人物嬗變——《鐘鼓樓》的歷史感分析[J]. 名作欣賞,2009(15):62-63.
[3]王晨倩. 論《鐘鼓樓》的歷史和人生觀照[J]. 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5(03):43-45.
[4]王鵬. 中國文化敘事學發展歷程與主要視角模式研究[D].湖北師范學院,2011.
[5]夏正娟. 劉心武小說:“理性型文本”的一種[D].吉林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