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黏度骨水泥與普通骨水泥經皮椎體成形術治療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效果觀察
吳潤鋒
河南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骨科 南陽 475000
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性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OVCF)多發于骨質疏松癥的老年人群,主要癥狀為頑固性腰背部疼痛等,可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2]。因老年人體弱多病,生活自理能力差,非手術治療需長期臥床,易引起多種并發癥,因此宜采用手術治療。近年來,隨著脊柱微創技術的發展,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因具有良好的效果,已成為治療OVCF患者的重要手段之一。為探討不同粘度骨水泥用于PVP的效果,我們開展此項小樣本前瞻性研究,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研究已經院倫理委員會審批,納入2019-01—2021-01于我院骨科行PVP治療的OVCF患者。納入標準:(1)經CT三維重建、正側位X線片、MRI檢查,以及骨密度測定確診為胸腰椎OVCF。(2)椎體后壁完整,骨密度<-2.5 g/m2,臨床資料完整。(3)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合并腰椎滑脫、強直性脊柱炎等其他腰椎疾病,以及神經根損的患者。(2)重要器官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礙和對骨水泥過敏者。(3)表達能力障礙或精神疾病患者。依據不同骨水泥粘度分為普通骨水泥組和高黏度骨水泥組。
1.2方法PVP術:患者取俯臥位,常規消毒、鋪巾。C型臂X線機透視確定傷椎椎弓根,以其體表投影為進針點。局部麻醉下以3.2 mm的穿刺針從單側椎弓根通道刺入,正位顯示針尖接近中線,側位顯示針尖在椎體前1/3處,拔出針芯。采用2 mL注射器緩慢注入拉絲期的骨水泥。普通骨水泥組注射普通PMMA骨水泥,高黏度骨水泥組注射高黏度骨水泥。嚴格控制骨水泥注入時間,待骨水泥彌散均勻、即將溢出椎體范圍時停止注入。旋轉穿刺針以防凝固,待骨水泥完全凝固后拔出穿刺針。術后2組均實施抗骨質疏松、抗感染常規治療,并適時指導進行康復鍛煉。
1.3評價指標(1)術前、術后第3天、術后3個月,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3]評估患者手術前后患者的疼痛程度:0分代表無痛,10分代表劇痛。分值越高表示疼痛程度越重。采用功能障礙指數(ODI)[4]評估患者的椎體功能:分值為0~50分。分值與功能障礙程度呈正比。(2)統計2組骨水泥滲漏率:包括骨水泥椎旁滲漏及椎間隙滲漏。

2 結果
2.1基線資料研究周期內共納入符合標準的患者70例,每組35例。2組患者的基線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的基線資料比較
2.2手術前后VAS評分及ODI評分2組患者術前的VAS評分、ODI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術后第3天的上述評分均優于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2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患者術后3個月時的VAS評分、ODI評分均分別優于術前和術后第3天,其中高黏度骨水泥組的上述評分均優于普通骨水泥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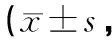
表2 2組患者的VAS評分、ODI評分比較分)
2.3骨水泥滲漏高黏度骨水泥組發生1例骨水泥椎旁滲漏,1例骨水泥椎間隙滲漏,滲漏率為5.71%(2/35);普通骨水泥組發生3例骨水泥椎旁滲漏,6例骨水泥椎間隙滲漏,滲漏率為25.71%(9/3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285,P=0.022)。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OVCF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非手術治療的效果不佳,而且治療周期長,容易引起繼發性椎體畸形和壓瘡、泌尿及呼吸系統感染等諸多并發癥。而傳統開放手術則創傷大,預后效果不理想。PVP治療OVCF既往臨床常用的骨水泥為普通PMMA骨水泥,其生物力學特性良好,彌散性能好,可有效提高患者椎體強度;且通過熱效應、穩定骨折等機制在短期內可緩解患者疼痛。但文獻資料表明,應用普通PMMA骨水泥實施PVP術,術后骨水泥滲漏率較高。若滲漏至椎旁、椎間隙時,臨床癥狀不明顯;但當骨水泥滲漏至椎管內、椎間孔時,神經根、脊髓將受到壓迫和熱損傷而引發劇烈持久疼痛,甚至癱瘓;如滲漏至腔靜脈,還有可能引發肺栓塞而致死[5-6]。基于此,臨床開展了大量的關于高黏度骨水泥的研究[7]。
高黏度骨水泥是在普通骨水泥的基礎上加以改良而制成的新型填充材料,其較普通骨水泥粘度更高,因此流動性降低,對患者造成的熱損傷小,不易發生骨水泥滲漏。本研究結果顯示,高黏度骨水泥組患者術后3個月時的VAS評分、ODI評分均優于普通骨水泥組,骨水泥滲漏率低于普通骨水泥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與有關研究的結果一致[8]。充分表明了高黏度骨水泥用于PVP術治療OVCF的良好效果和安全性。分析其原因在于:注射高黏度骨水泥,可達成瞬間高黏度和低聚合溫度,注射時間長,更有利于患者術后康復。
綜上所述,與普通PMMA骨水泥比較,采用高黏度骨水泥實施PVP,骨水泥滲漏率低,可顯著緩解患者的疼痛癥狀,改善椎體功能。但仍需進行大樣本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予以證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