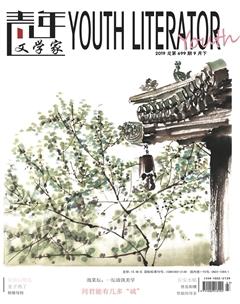書藝家虞世南《筆髓論》與佛教淵源
藺熙民
基金項目:武警工程大學2019年軍民融合專項課題項目(WJM201903)。
摘? 要:著名書法藝術家虞世南《筆髓論》具有較深的佛教淵源,蘊含著豐富的佛教理論色彩,其彰顯心悟說,會通佛藝及其絕妙境界,在中國書法理論接納佛教的歷程中功不可沒。其形成原因及影響是多方面的,也值得加以深究。這對于進一步豐富深化虞世南的研究,不無裨益。
關鍵詞:虞世南;《筆髓論》;佛藝會通
[中圖分類號]:J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7--02
虞世南《筆髓論》是一部中國書法用筆名作,僅一卷,共1034字,包括原古(敘體)、辨應、指意、釋真、釋行、釋草、契妙等七節。主要論述真、行、草各體書法的基本原理、創作規律及研習方法。它是虞世南書法理論的代表作,見解深雋。唐太宗《筆法訣》《指意》篇,采擷較多,《宣和書譜》則謂虞氏“嘗作《筆髓論》,學者所宗”。《筆髓論》是中國傳統書法實踐的理論總結,但細繹其中深層肌理, 蘊含著豐富的佛教理論因子,佛教滋養不菲。可以說,虞世南“君子之書”及君子書風之形成,與佛理關系密切。從此入手可進一步挖掘虞世南的精神世界、心靈情懷及書法意蘊之特點,意義頗豐。
一、《筆髓論》的心悟說與佛教淵源
中國書法源遠流長,但佛教在中土的興起與傳播,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很深。東晉以降,文士儒臣積極抄寫佛典,成為佛教流布、弘揚佛法的重要助力,同時這些佛教經典也成為書法經典名作;更甚者不少書法名家,深受佛教濡染乃至皈依佛門,其書法與人格品性均受佛教浸潤。唐代書學興盛,大家云集,書藝精湛,成就斐然。歐陽詢、褚遂良、薛稷、懷素、柳公權、顏真卿等均從事過佛教書法創作,留下精湛的佛教書法作品。不僅如此,大批士人還爭談禪悅,精神品格受其熏染,特別是佛理禪趣漸融入書法義理中,達到佛藝的深層次契合。虞世南及其《筆髓論》可算其中的佼佼者,其佛學資源十分豐富。主要體現在:
(一)書道在于“自悟”:暗通款曲于禪學自力精髓
《原古》開篇認為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進而認為自從倉頡造字到“立六書”,及經戰國至于秦朝的“八體”,均“不述用筆之妙”,而至于“蔡邕張索之輩,鐘繇王衛之流”,則其成功關鍵在于“造意精微,自悟其旨。”這里強調書藝之本在于書家之“自悟”乃用筆之管鑰,可謂一語道破天機。實際上,中國禪學講究“自悟”,自立自行,只有依靠自修自證自悟才能達到禪修之最高境地,后來的禪宗自始至終以明心見性為鵠的,崇尚自我頓悟,強調自性自度。這里開篇伊始就揭示出書藝之本在于“自悟其旨”,可謂深得禪學之精髓,突出彰顯出書道的主體性、本體性、個體性乃至創新性。書道最高之境的通達源于自悟而不在其他,外力、旁力、他力均非根本,關鍵在于自悟自修自練自踐,特別是心的切中肯綮與游刃成熟,因此書藝之本就像禪修者依靠自力自為自悟臻于佛境一樣。中國思想與文化從先秦開始雖也極強調強大的主體性,但是只有等及佛教的切入,才將自我修證煉養的堅固主體性創立起來,這是佛教對于整個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虞世南強調書藝修煉上的主體性則是這一巨大潮流的積極吮吸者。
(二)書道在于“心”為主宰:彰顯鮮明的佛教“心”學趨向
《辨應》中揭示出“心為君”“手為輔”“力為任使”“管為將帥”“毫為士卒”“字為城池”的詳細序列,形象辨清其相互關系,極為突出“心”的主宰性,彰顯鮮明的佛教“心”之核心性與中心性。“心”“性”是佛教龐博精深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心性修養”本性形成的關鍵。先秦以來形成傳統對外的形-象-言-心-意-情與眼-手兩個線索,以及對內的精-氣-神序列,加上總體的道-氣-性-心關系,均未真正形成、達到以“心”“性”為核心的地步,而正是由于佛教的(“心”)參與和浸潤,發生重大的轉折,過渡到以“心”及“性”為核心與中心的狀態,并且特別是將上述環節從線性發展到垂直的本體關系,從而獲得通達于“道”(即“藝”)的強大“心”力。從中國書藝上講,也是中國書法理論形成的重大關節點,虞世南《筆髓論》則是這一歷程的見證者與必不可少的環節。柳公權亦說:“用筆在心,心正則字正。”
(三)書藝創作之道在于“心悟”:佛教頓悟說的集中體現
《筆髓論》全文貫穿著書藝創作之道在于“心悟”,暗通佛教煉養論之本,是佛教頓悟說的集中體現,是中國藝術頓悟說的促發者。《指意》說:“用筆須手腕輕虛。……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及其悟也,粗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為有馀,短而不為不足。”其中,彰顯出“悟”的巨大效力。特別是《契妙》說:“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妙。……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于至妙,書契于無為,茍涉浮華,終懵于斯理也。”概括出書藝創作要沉靜返潛,絕慮凝思,才能契合其中佳妙之處,進而認為書道之妙在于心悟,要用心參透悟深書學之理,才可臻于佳境。這與蔡邕《筆論》“默坐靜思,隨意所適”、王羲之“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令意在筆前”以及劉勰“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龍·神思》),一脈相承。而這種強調心悟契妙的書藝創作理論與佛禪心性思想密切。佛教戒、定、慧三學中,專志凝神之定尤為重要,與書法創作之道最為相契。而禪悟的根本要義在于通過參禪來“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從而達到本心清凈、空靈清澈的精神境界,它是中國藝術“妙悟”說的直接來源。經過僧肇、竺道生、慧能的發揚,唐代“妙悟”說在文藝上漸露頭角,并運用于書道及其創作。虞世南堪稱其中重要代表,李世民、孫過庭、李嗣真、張彥遠等均受其影響。后源于眾多文藝理論家的參與,至于宋元則以嚴羽為代表真正形成中國藝術妙悟說。
總之,虞世南《筆髓論》蘊含佛家思想因子,源于書法與佛法相通,彰顯心悟說,會通佛藝及其絕妙境界,在書法理論接納佛教的歷程中功不可沒,十分值得加以深究。
二、《筆髓論》佛教淵源的形成原因及影響
虞世南作為政權高層文士,積極為高僧大德、寺院書寫碑文與碑銘,唐初儒道大論爭中奮然為法琳《破邪論》作序,并在《帝王論略》中借用佛教因果報應論對梁武帝信佛卻遭亡國作獨特解釋,指出周武帝滅佛危害甚巨,認為佛道二教均“止惡尚仁,勝殘去殺,并有益於王化,無乖於俗典”,顯示出深刻的佛學見解。《筆髓論》之所以佛教淵源較深,可歸結于:親炙于書圣王羲之七世孫、名僧智永大師,并終身恪守其書道與精神風范;出生于江南名鄉,佛學浸潤久厚;出身于玄佛合流望族鳴鶴虞氏家族,承繼玄佛藝兼容的名士風流;為官階層與交游圈多尚佛,濡染較深。
虞世南深厚的佛教交緣,極大影響了其書法理論名作《筆髓論》,并對其書法風格影響甚大。源于佛藝相通,佛教促發了其蕭朗簡澹之性情,從而使其書法顯示出獨特風格。其書法名作多,筆法與書寫風格受佛教影響深,韻致婉逸、遒逸清勁的《千佛銘》《破邪論序》可謂其中代表。書法是生命藝術,書品與人品緊密關聯。虞世南“虞體”書法,是人品與書品統一的典范。其書法風格溫文儒雅,穩健沉郁,醇厚遒麗,被譽為“君子之書”。張懷瓘《書斷》贊說:“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此種“君子書法”源于多端:沉靜寡欲、崇德修身的人格操守,直言敢諫、深知進退之道的特有品性,命運多歷、熟諳人情冷暖的艱難磨礪,篤志勤學、矢志進德圓業的價值追求。但受業于智永禪師,特別是靠近佛教人士,自身濡染佛教,其思想深處具有佛教空靈脫世思想因子的浸潤,性情恬雅沖淡、溫漠超脫,才使其書作油然流溢出疏淡超塵之氣韻,用筆健朗而圓潤,沉蓄而秀逸。包世臣《藝舟雙楫》贊說“平和簡凈,遒麗天成,曰神品”。如唐碑《幽州昭仁寺碑》三千余字,書法秀麗而俊邁,純靜簡澹秀逸。這不僅受惠于二王恬淡蕭散的魏晉風度,而且滲透著佛教的影響,飽含著超越世俗、參透萬象的佛禪胸襟與禪悅心靈。這對于后世書法理論影響深遠,醇厚勁健中那股俊逸散朗之氣的推崇,以臻于渾然天成的止境,永遠為書道所恪守與沿傳。
總之,虞世南《筆髓論》與佛教有較深的淵源,正由于佛教思想的融入,促成了其關于中國書法之卓見,從中也可看出佛教對于中國書法藝術理論的特有貢獻,值得探究。
參考文獻:
[1]董誥等.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劉勰.增訂文心雕龍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