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合唱團:聾啞兒童唱出天籟之音
王霜霜
“啊——啊——啊——”2 0 1 8年8月4日,北京音樂廳的舞臺上,一群身著白衣的孩子發出長長短短、起起伏伏的聲音。這是由無聲合唱團表演的原創音樂作品《無聲三部曲》。
臺下的觀眾先是茫然,然后感動,有人悄然落淚。15分鐘的演出結束后,臺下掌聲雷動,向臺上豎起大拇指,表達內心的稱贊。
無聲合唱團是藝術家李博和音樂人張詠于2 0 1 3年1 1月創建的,成員是來自廣西凌云縣和福建廈門市的1 4位聾啞人。李博和張詠用5年時間訓練聾啞兒童發聲,并教會了他們合唱。北京音樂廳是他們表演的第三站。
…………
被一聲“啊”擊中了
《無聲三部曲》以古老的“南音”為基礎,并融合了廣西民歌、中國傳統樂器及西方流行音樂元素。演出時,李博站在前排指揮,而張詠則彈奏他倆自創的新型樂器“chén”——古琴與貝斯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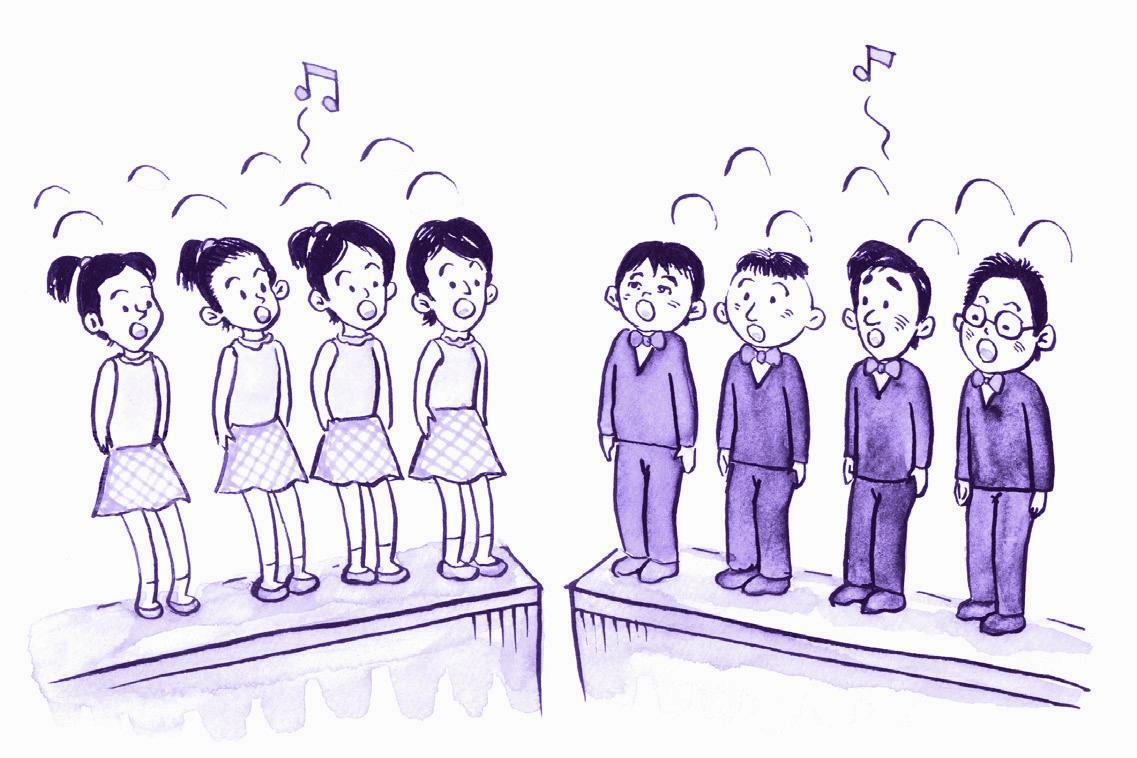
他們倆是多年的好友。張詠曾是搖滾樂隊“子曰樂隊”的成員,李博原本是個畫家。兩人都想“搞點不一樣的”。2 0 1 3年,在做一首實驗性音樂時,他們突發奇想,“把聾啞人的聲音放在歌曲里應該挺有意思的”。
張詠認為聾啞人是本能發聲,“突然‘啊一嗓子,特別像森林中動物的一聲號叫”,原始、真實、震撼。相反,健全人,甚至歌手,聲音都是被文明馴化過的。修飾過了,就喪失了某種“自然”的質感。
他們決定去采集一些聾啞人的聲音樣本。在紅燭基金會的引薦下,他們找到了廣西百色凌云縣的一所特殊教育學校。
…………
他們倆想了很多招來啟發孩子們,希望他們放松下來,別緊張。“你們心里有沒有想唱的歌啊?想發什么聲啊?”但一提出讓孩子們發聲,他們就會連忙用手語說“我不行”。
…………
折騰了兩周,也沒什么進展,兩個人都有點泄氣了。“別再互相折磨了,走吧。”李博到學校向校長辭行。
這時候一個女孩兒跑了過來。一聲很長很穩的“啊”從她嗓子里發出。這個女孩兒叫楊薇薇,當時只有4歲。“她就這樣向你撲過來,啊……”李博伸出兩只胳膊張開嘴,模仿楊薇薇當時的動作。
這聲“啊”擊中了他。“你感覺你就有責任了,她肯發聲說明我們之前所做的事已經在孩子心中產生影響了。”李博說,“你想想,當你相信一個人之后,他就走了,再也沒出現過,那你的心靈肯定會受到更大的打擊和傷害,那我們還不如不來,對吧?”
4年,1分鐘
最難的是如何進行溝通。“因為他們沒發過聲,對發聲沒有概念。舌頭要擺正位置,怎么擺?你要一點點講。擺到位置后,你要告訴他,舌頭要挺住,要挺直,要用力。讓他們理解這些微小的東西特別困難,要想盡辦法,用各種比喻。”張詠說。
…………
光能發聲還不行,合唱團有高、中、低音的劃分。“你是a,你是b,你是c……”幫孩子們發聲后,張詠和李博又根據他們各自的音色,在他們最擅長的聲音附近,分配一個適合合唱的音。
一張嘴,要像鋼琴按下的某一個鍵一樣,就是一個標準音,這對專業音樂院校的學生來說,都十分不易。聾啞人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只能用校音器監測音高。“張嘴,哎,到了”,張詠模仿孩子們邊發聲邊盯校音器,“大家就靠這種方法來訓練、記憶。他們每一點點的進步,都要經過成千上萬次的練習。”
一直到了2 0 1 7年的夏天,無聲合唱團才完成了他們的第一首作品。這首無名的樂曲只有1分鐘。
…………
5年間,無聲合唱團的人員也歷經了幾次變化,有的孩子輟學,有的孩子回家結婚,就離開了。為了讓他們站在臺上“看起來不這么孤單”,2 0 1 7年,張詠在廈門的特殊學校又找到了幾個孩子,組成了現在1 4人的隊伍。
…………
尋找藝術的本質
…………
這幾年,總有人問李博:“你怎么去做公益了?”但他并不把“無聲合唱團”定義為一個公益項目,“嚴格來說,這是一個藝術項目”。
藝術批評家栗憲庭看過演出后,認為這是“把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創造出來了”,他說:“人在生下來以后,就不斷地受到文明和文化的污染。我跟你交流發出來的聲音是跟文化有關系的。語言有表達的功能,同時也有遮蔽的功能。所有的藝術都在找這個世界上什么是最真實的、最本質的東西。”
…………
完成了北京音樂廳的演出后,李博和張詠又帶著孩子們在北京逛了一圈,到天安門看升旗,游歡樂谷、故宮、長城……“有意思的地方,都玩了個遍。”
之前因為殘障,很多孩子都被人瞧不起,但這次來北京,個個都是“家里放鞭炮送出來的”。不過,也有人擔心見過城市的繁華之后,孩子們如何重新面對大山里的寂寞和未來的暗淡。
此前,他們就曾帶無聲合唱團去廈門演出,回去之后孩子們也并未覺得失落。李博覺得,無聲合唱團的價值不是要給孩子們的未來找一個出路,而是希望能帶他們看到更大的世界,以后有更多的選擇。“快樂就行,快樂自信最重要,然后是平等,對吧?別的都是次要的。”李博說,“重要的不是臺上的那幾分鐘,而是他們回去之后,能更好、更有尊嚴地活下去。”
(摘自2 0 1 9年第4期《今日文摘》,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