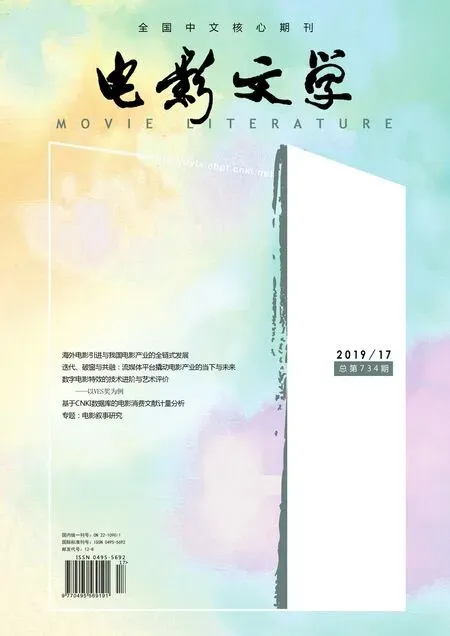作者電影視域下的西部敘事
王黨飛 趙 瑞(.石河子大學 文學藝術學院,新疆 石河子 83000;.兵團電視臺,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在大量西部題材的電影中對于西部的視覺形象建構中,黃土地式的大背景,人煙稀少的邊緣地帶、經濟落后的視覺現象是一種常態,這種視覺性已經成為呈現西部形象的類型化特征之一。當然,如果僅僅把西部形象書寫為空洞的符號,只為滿足市場消費需要,滿足觀眾的視覺消費,那就脫離了西部地區形象的原本審美和詩意化表達。在20世紀80年代,著名學者鐘惦棐在西安電影制片廠提出了拍攝“中國西部片”的口號,提倡打造立足于本土化的、民族化的中國西部片。在以吳天明、陳凱歌、張藝謀等一批第五代導演的踐行下,中國的西部電影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關于西部電影概念,中國電影家協會有著這樣的定義:“中國西部片是以中國的大西北獨特的自然景觀、悠久的歷史積淀和豐富的人文底蘊為底色的中國電影類型片。”(1)《中國西部片》,載于中國電影協會官網,http://www.Cfa.org.cn/info/2007/5138.shtml。在西部本土導演的大量作品中,西部是一個桃花源般的地方,對于西部地區特有的地域自然景觀、厚重的歷史積淀、深沉的文化根源和獨特的人文精神有更加深刻的描敘。
在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電影創作理論——作者電影理論。該理論所提倡的電影“自傳性”在19世紀80年代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第四代、第五代導演的影像。作者電影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兩個。第一是對抗性,主要是對類型和模式電影的對抗,要求電影像文學一樣有充分的對抗性。第二是導演的核心地位。電影要將導演的思想、個性、風格特征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作者電影所代表的“編導制合一”制作方式賦予了影像獨有的個性與思想,而受此理論影響的西部影片也是西部地區內部自我意識的公開呈現,它將成為西部地區強有力的信息傳播者。而西部本土導演的創作會使得西部題材的影片更加“純粹”。
一、西部影像敘事的主體——土地與人
土地元素是西部影視中的一個核心意象,土地是人物的根,一切在土地上展開,又都在這片土地上結束。但是真正有意義的是土地之上的人。
《黃土地》把西部地區黃土地蘊藏的自然美,黃土地背后所代表的勤勞、勇敢、誠懇的底層勞動人民,以及這塊地區落后與貧瘠,表達得淋漓盡致。其出色的攝影,使得黃土地的黃色成為影片的主色調,畫面中大面積的黃土地使得人物在黃土地的大背景下顯得很渺小,影片刻意性的紀實對于黃土地注入了太多的情感,近乎膜拜。同時黃土地也成為西部的代名詞,在觀眾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吳天明的《人生》中黃土地也作為一個有機部分,影片在鏡頭一開始就展現了貧瘠的黃土地和千溝萬壑的高原。但在高加林與土地的關系上,創作者更傾向于表達主角的情感,土地的出現只是主角情感的鋪墊。這使得西部電影更加具有了真實的意味,不再過分放大民俗文化。土地在西部影像中頻繁出現,不僅是作為西部的地域性背景,還更深層次地隱含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文化底蘊的體現載體就是充滿靈性的人。人們確實靠土地謀生,但是土地卻不能成為永久的支配者,二者之間是制衡的關系。
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以下簡稱《白鶴》)中,土地的文化沒有被直接放大,沒有大量鏡頭的刻意表現,也沒有標志性的“黃土地”色調,而是通過爺孫兩代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以及對話緩緩展開,表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土葬的政策打破了爺爺平靜的晚年生活。爺爺是一個堅守傳統生活方式的人,相信人死后留全尸土葬能駕鶴仙去,所以懷著不愿死后變成一縷煙的念想,兩次堵煙囪,兩次為自己畫圈選址。而智娃是一個單純但有點叛逆的孩子,他為了孫悟空被壓五行山下而痛哭,為了滿足爺爺入土為安的愿望,提議偷偷把爺爺活埋了。智娃的建議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壞的方法。曹老頭的墳被挖,湖里的蘆葦被割,鴨子被捉,無人理會老馬的阻攔。讓堅持“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鄉土傳承的馬爺爺,無奈選擇了這種近乎殘酷的方式完成他的堅守,而智娃騎著鐵锨“馬”回家吃飯,地面上的一切看似都很平靜,好像什么也沒發生,但人物失去了自己的根,離故土越來越遠,傳統風俗在現代的政策環境壓力逐漸消解。世代在黃土地上生存的人們,靠土地生活的意識越來越弱,人不再是土地的“子孫”,而是成為土地的支配者。
在一個土生土長的新疆導演陳建斌眼中,擁有著現代文明的城市文化對于傳統的土地文化來說并不是作為異己的存在,在他的電影《一個勺子》中生活在城市中大頭哥和生活在農村中的拉條子分別處于兩種文化背景下,土地之上的人們劃分成了傳統與現代兩個陣營,但城市對于拉條子來說也不再是不可抵達的彼岸風景。拉條子五上五下大頭哥的車,二人之間對話,使得拉條子經歷自我迷失到自我審視的過程,拉條子的性格中有著執著、忠厚、重情的傳統品質,但是愚昧滯后的落后文化因子也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顯現。拉條子遭到多次“下車”的拒絕,這一方面顯示了他的執拗;另一方面也在隱喻傳統農村人的思考方式在被城市所認同的精明的思考中被拋棄。[1]這是新時代下城鄉整合下的一個縮影,西部影像中土地的生命力已經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有了更強的延展力,淡化了“在地者”影子,視角對準了土地之上人。
二、西部影像敘事的對抗——自然與人
人通過勞動創造了人類社會,在自然環境中人化自然的同時也不斷地被自然人化,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不可分割體。生活在土地之上的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是息息相關、相互依存的。
現代化進程在不斷加速,自然環境在逐漸惡化,這使得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越來越受人們重視,而關于人與自然的主題電影也不斷涌現。在中國的西部,這片擁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和濃厚的農耕文化的地區,隨著現代社會的工業化進程,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破壞,這是從農耕社會步入工業化社會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塊土地上人們的思想、心靈以及生活方式上也遭受到極大的沖擊。西部的人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努力生存,但對自然依然懷有敬畏之心。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商業的發展,社會環境的不斷繁榮,也使自然環境被日漸毀壞。人類不再弱小,自然也不再被神話。人們不斷地向自然索求導致的環境惡化,其反噬自身的結果在西部電影中有著直接的闡述。
生于新疆奎屯的導演陸川看到有關藏羚羊、野牦牛被殘酷獵殺的新聞報道后,拍攝了他人生中的第二部影片《可可西里》,電影以一位記者的視角記錄殺戮者和保護者之間的周旋。以記錄的方式展現了藏羚羊慘遭殺戮、尸橫遍野的景象以及保護隊的艱辛。影片中用生命保護可可西里的索南達杰被暗殺,隊長索南達杰中槍后直接倒地的畫面,零表演的死亡時刻,沒有如影視劇中正義的英雄人物那樣,在生命彌留之際還可以對敵人進行最后的反撲或者留下不言敗的遺言,只有身體抽搐后的靜謐,這樣不加修飾的客觀記錄是一種直白的寫實。在這自然環境面前反盜獵者與盜獵者的對抗,其實就是人性善與惡的博弈。珍稀動物慘遭獵殺是人性的惡在作祟,善的一方最終敗下陣來,無言的死亡才是對人性惡最大的控訴。在自然與人的交織里,陸川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如果說《可可西里》是一種紅色預警,那么李睿珺的《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就是一種深沉的自我反思。影片內容如海報所展示的那樣,他們一路上所見盡是逐漸擴大的干旱、干涸的河流和水井、凋萎的草原,還有廢棄的村鎮,并用全景和大全景冷酷地呈現環境的惡化,這些影像是振聾發聵的。荒漠化的范圍似乎沒有邊際,心中家園也越來越遠。當巴特爾和阿迪克爾歷盡艱辛在淘金人群中找到了“去更遠的草原放牧”的父親時,導演用一個搖晃的鏡頭展現兩代人的對望,鏡頭的搖晃是黃金牧場般的家園徹底被摧毀導致心靈震顫的外在體現。弗洛姆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一書中強調,對自然資源過度消費或者消耗而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也是人性異化的一種表現。在影片結尾處,父親邁著堅定的步伐快速走在前面,孩子們無言地跟隨父親走向廠區附近的家。孩子們心中水草豐茂的家園形象徹底崩塌,傳統農業文明在現代都市文明面前是徹底被毀,這是工業和人類的私欲對環境破壞的后果,與電影名《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形成鮮明的對比。正如爺爺賣掉所有的羊后,騎著那匹白馬,望著載羊的卡車遠去時,唱起裕固族的民歌《西至哈至》一樣:“綠色的草原啊正在消失。奔流的河水啊早已干枯。”這首民歌既是自然史也是民族志,裕固族對大自然是崇拜的,自然風景中帶有家族的記憶烙印。歌中展現的風景蛻變是荒漠化的寫照,也意味民族性的消亡。[2]爺爺的去世和草原的惡化的命運是一致的,也是一種“土地”的隱喻變體。《白鶴》中的仙鶴,仙鶴是長壽的代表,是馬爺爺回歸土地的載體;這些動物的意象每一個都別有深意,與影片主題內核遙相呼應。
工業化的發展正在破壞這片土地和自然環境,現代性的破壞力讓傳統的牧民成為淘金工,孩子記憶中的黃金牧場也消失了,心目中美好家園自然也不存在了。在西部本土創作者的影片中不以沙塵暴、無垠的沙漠、荒無人人煙的公路等奇觀訴諸觀眾的視覺滿足,而是通過近乎客觀的真實記錄來昭示著人與自然的依存關系,沒有自然的供給,人們將處于悲慘的境地。過度的索取忽視人與自然的依存性,會付出沉痛的代價。人與自然的對抗不是絕對的征服與順從,而是在對抗中,相互依存尋求共同發展。
三、西部影像敘事的更迭——時代與人
自鐘惦棐首倡后,中國的西部片在電影界引起強烈反響,此后《人生》作為西部片的發軔之作,引發一大批《黃土地》《野山》《老井》等以西北人現實生活、生存狀態和奮斗經歷為題材的影片涌現。這一時期影片中的人物有著極其強烈的意圖,如《秋菊打官司》中堅持要說法的秋菊,《老井》中堅持不懈打井的村民,他們成為“一根筋”式的西部群體代表,這樣的人物塑造體現了在改革開放時期,西部地區落后、愚昧的現狀,也是造成人們對于西部刻板印象的一個原因。而那些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人,比如《黃土地》中控訴男權的翠巧,《老井》中義無反顧地追求幸福的新時代女性巧英和打破老井村民堅守傳統風俗的高加林。他們是改革開放時代下的新銳代表,以小見大地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這種人物是為響應時代需要而塑造的帶有虛構浮夸成分的真實人物代表。相比西部武俠片《臥虎藏龍》中的神秘莫測羅小虎,《新龍門客棧》中掃地僧般存在的廚子,《東邪西毒》中的隱士東邪西毒等這些完全虛構出來的俠客。20世紀80年代西部電影中鄉土人物的塑造雖然有弊端,但也是接地氣的一種表現,是回歸西部現實生活的一個注解。
新時期的西部電影也是鄉土的題材,但更多的是批判現實主義。李睿珺、吳天明、陳建斌的影像都把觸角伸向了自己生命起源的故土,他們自己是從鄉村到城市,電影中卻是以一個回憶者的姿態去建構一個現代環境下鄉土空間。作為演員陳建斌轉任導演的處女作,這部影片訴說了陳建斌眼中的世界,表達了一個電影人的思考。影片中的世界不是虛構的,不是在城市,而在農村,“城市是這片土地上很小的一部分,而絕大部分我們統稱為鄉村的地方,才代表了更為真實的世界。我們不應被自己生活的這個狹隘空間蒙蔽。”[3]李睿珺的《白鶴》和《水草》更多帶有鄉愁的回憶,2012年拍攝的《白鶴》中智娃愛看的《西游記》,智娃和小伙伴們赤裸躺在馬路邊玩游戲,還有2015年《水草》中騎著駱駝尋找家鄉的裕固族少年,均是導演詩意化的精神故鄉建構。2016年吳天明的《百鳥朝鳳》也不是對于舊傳統的顛覆,而是對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呼喚,游天鳴經歷了幼時嗩吶匠職業的尊崇,青年時期嗩吶在西洋樂面前敗下陣來的時期,目睹了游家班成員前往大城市謀生的決然和嗩吶藝人老年街頭賣藝的凄涼,但他依然堅持回家鄉繼續嗩吶事業,這是導演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傳承傳統文化的體現,是理想化的結局,旨在呼喚青年一代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這亦是導演詩意化的故鄉生活,是在高速發展的時代中,尋求精神皈依的體現。《一個勺子》中富人李大頭、警察、村長、騙子、拉條子,一個角色代表一個階層,一個階層映照一種世道人心,直到最后合理顛覆了“好人有好報”“傻人有傻福”的傳統民間諺語。這幾類人物的塑造,建構了一個小型社會,是社會各類人士的濃縮,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立場和價值觀。《一個勺子》電影名中的“勺子”就是新疆方言,是對“傻”的地方性解釋。“勺子”一開始是指金世佳所扮演的傻子,最后拉條子戴上傻子的紅色遮陽帽,有意成為他人眼中的“勺子”,拉條子的逃避與放棄也帶動觀眾去深思,“勺子”到底是誰?謎底如斯芬克斯之謎一樣充滿了悲劇。影片結尾并沒有給出明顯的答案。正如金馬獎對《一個勺子》的評價:“在悲喜之間洞穿人世的復雜,猶如一面照妖鏡,讓社會中的人無從遁形。”人是最復雜的社會性動物,影片只是把現實生活美好的外衣給撕開,露出內在的丑陋。真正的答案在于自我的反思。開放式的結局留給觀眾無限的遐想以及深深的思考。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也間接造成了主角拉條子的自我迷失。拉條子秉承的傳統禮數和經驗在面對城鎮的現代化與物質化的沖擊后,原有的道德評判和價值標準就被質疑了,失去自我成為一個勺子亦是人性惡的勝利。
如果說《黃土地》《人生》中導演塑造的人物是對生活的前瞻,《白鶴》《水草》《百鳥朝鳳》是導演對與鄉土倫理一同消失的傳統文化的擔憂。那么《一個勺子》是導演站在我們的時代直視我們真正的此時此刻生活,把西部日常生活中關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沖突娓娓道來。
四、結 語
中國的西部電影與美國西部電影截然不同,中國西部電影的最大特點就是寫實主義,有點詩意現實主義的風味。但是并沒有美國西部電影中所具備的三要素:公式化的情節(英雄救美),定型化的人物(善惡分明的英雄人物),圖解式的視覺形象。在鐘惦棐的理論影響下,以吳天明為代表的第四代和以陳凱歌、張藝謀等為代表的第五代中國影人開始了風格化的藝術追求和個性化的藝術表達,而這也正是受作者電影理論影響的踐行表現。中國西部的電影《黃土地》《黑炮事件》《老井》《野山》等都具有明顯的“作者”色彩。中國西部影像中人與土地、與自然生態、與時代的關系,其實是因為傳統文化在快速變化的現代文明中斷層的外在體現,脫離了傳統文化的人們猶如無根的浮萍,人性的惡因脫離了枷鎖而暴露無遺。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僅是文化自信的基礎,也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西部地區農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少數民族的文化個性正在日益消弭。
在地理概念上,西部獨特的地域所形成的空間,使得西部農耕文化十分濃厚,黃土地也因此成為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和中國西部電影的重要表現對象。前有吳天明的《人生》、陳凱歌的《黃土地》,后有顏學恕的《野山》表現對于農耕文化迷戀或反思。在游牧文化上,這是一個與農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是由西部地區的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一種文化,游牧文化的特點就是對大自然的適應與征服。馮小寧的《嘎達梅林》體現了蒙古族的信仰以及蒙古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但在李睿珺的《水草》中則體現的是游牧文化在現代文明進程中出現的斷裂。在宗教文化上,《可可西里》中的“天葬”場景就充滿了藏傳佛教的文化氣息,還有《水草》中爺爺去世時喇嘛做儀式也是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在軍事文化上,西部電影中的《黃河絕戀》和《紅河谷》有所呈現。因為在歷史上西部邊塞就意味著戰場,西部的軍旅生活也激發了許多著名的邊塞詩;軍事文化與農耕文化相結合形成的“軍墾”文化,也是西部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中國西部地區的自然之“險”與地形之“雜”直接決定著西部多元的文化形態。[4]無論是西部的人,還是西部的空間,在西部本土導演的影像中其都是受文化熏陶的表現。因此多元的文化才是西部敘事的內核,西部多元的文化形態是西部影視持續發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源泉。尋求西部多元文化的最小公約數也是西部電影走向市場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