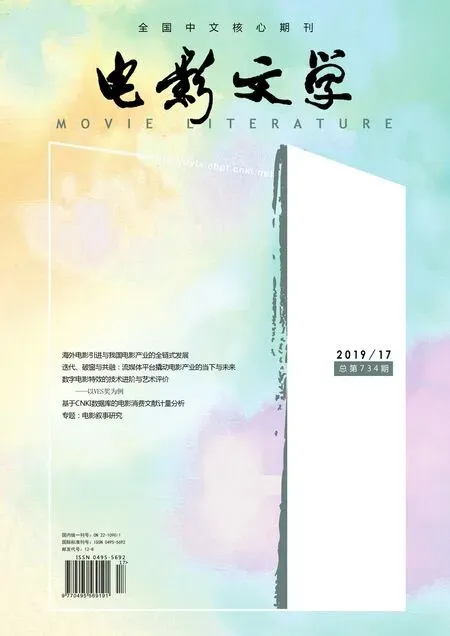影像與文化:河南電影的創作與傳播研究
朱曉娜(平頂山學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河南電影在產業規模上有所擴大,為推進河南區域文化在現實基礎上的形象提升進而涌現出一些優秀的影片在創作中深挖中原傳統文化,注重植入區域文化形象,對“河南形象”進行很好的包裝和推廣。“河南形象”作為河南省整體實力的重要體現之一,也是河南軟環境、軟實力、無形資源的重要內容。她代表著河南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綜合的外在反映,也代表著區域自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地區文化形象作為地方‘軟實力’的無形資產,媒介建構的‘地區文化形象’不僅影響受眾與他者對該地區的社會認同和價值判斷”[1],也能對現實社會中的區域交流產生重大影響。在此背景下,進行基于電影影像分析“河南形象”的形塑建構研究,對于影視媒介的河南區域文化形象的探索以及構建依據,影視媒介傳播機制自身研究空間的拓展都無疑具有相應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河南電影的銀幕呈現
研究“河南形象”基于對“河南電影”的定義,尚無定論,廣義上指含有河南地域元素的電影。例如由非河南電影公司制作或非河南籍導演主創,只選擇在河南取景、取材,其中并沒有河南本土機構的制作參與,不以河南籍人員為主的創作團隊所有出品的電影。而狹義上的“河南電影”是從河南籍、決定電影影像的人或力量與地域中管理者來界定,認為主創團隊(導演、編劇、監制等)到制片集團、影視公司、電視臺、曲藝團體都應是河南籍人員或長年在河南工作生活為主,比如2010年6月由河南導演盧衛國根據許昌農民自籌拍電影的原型故事創作了喜劇片《不是鬧著玩的》,本課題研究基于第二種“河南電影”定義界定。
以2008—2018年為節點,從十年之間選取二十多部河南電影作為項目研究對象,根據電影主題出發大致分為六種類型,包括中原喜劇電影:《不是鬧著玩兒的》(2010)、《就是鬧著玩兒的》(2011)、《給你1000萬》(2011)、《誰hold住誰》(2013)、《還是鬧著玩兒的》(2017);豫劇戲曲電影:《程嬰救孤》(2008)、《清風亭》(2010)、《新大祭樁》(2012);本土民情電影:《黑蛋,快跑》(2009)、《新年真好》(2010)、《幸福的白天鵝》(2011)、《念書的孩子》(2012)、《潘多拉的寶劍》(2012)、《自古英雄史出少年之岳飛》(2012)、《好好地活著》(2014)、《念書的孩子2》(2015)、《三個孬家伙》(2016);河南美食電影:《豫菜皇后》(2007)、《胡辣湯》(2010)、《洛陽水席》(2012);地域文化電影:《鈞瓷蛤蟆硯》(2010)、《新年真好》(2010)、《道口燒雞鋪》(2011)、《甲天下》(2011);時代人物電影:《永遠的焦裕祿》(2014)、《李學生》(2018)等。
這一時期電影多以河南電影電視制作集團、河南電影制片廠為制作出品主力軍,又以河南籍導演韓萬峰、朱趙偉、路振隆、盧衛國等人指導創作,作品內容豐富,貼近現實,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和濃郁的中原地域色彩,不僅征服了眾多觀眾,并在國內外獲得了多種影視創作的獎項。作為區域文化形象的構建者,河南電影人著眼于如何真實地認識河南,用不同時刻,各地理區域,以及電影敘事的文化身份等實踐者影像創作。河南電影的生產者也從電影精神到影像塑造正在不斷通過影像的形式輸出著動態的、多元化的河南形象,對河南區域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河南形象的傳播與文化輸出
這一本時期內,河南電影敘事主題與審美內涵的發展與演變,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的變化構成了密切的對應關系,從河南電影創作作品中透視“河南”區域形象樹立軌跡,梳理河南電影敘事主題的多樣性,可以深入了解河南意識形態的演變、民眾關注熱點的變化以及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和美學觀的發展,更可以透視電影與時代和社會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關系,深化河南電影與河南形象、中原文化研究領域研究。
(一)影像藝術里的中原文化遺產
河南電影作為中原文化的一種載體,具有其他媒介無法比擬的優勢,能夠把本土時空地域中的文化形態和人文景觀傳遞他處,展現新時期的風土人情,歷史風貌,反映出河南精神和中原文化的內在價值與現實意義。河南電影和電影人正在傳播并傳承著豐富多彩的河南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成果,尋求文化共鳴。《鈞瓷蛤蟆硯》正是以河南禹州鈞瓷為背景,鈞瓷文化彰顯了中原物質文化遺產的視覺化特征,具體可感知,有形有色,濃縮了整個宋代的精華,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文明程度,更能體現出中原古人的聰明才智和精神文化。“影視藝術具有故事性,擅長情感化和藝術化的表現手法,同時具有文學敘事樣式所沒有的視聽優勢,因此影視藝術能夠在潛移默化中讓觀眾去體驗影像的魅力,領略藝術的美感”。[2]電影講述了發現一宋代鈞瓷珍品蛤蟆硯后產生的一系列矛盾與糾紛,刻畫了各種人物在珍寶面前所呈現的品格和靈魂,展現了新一代河南青年樂觀積極向上的生活模樣。作為器物文化,禹州鈞瓷具有獨特的審美創造精神,非凡的藝術感染力也成為豐富現代人精神生活的厚重素材,河南電影從而進一步弘揚了鈞瓷文化。河南電影美食系列三部曲《豫菜皇后》《洛陽水席》《胡辣湯》,將中原地帶的飲食風俗與當地山水、人文、情懷相結合,從飲食文化折射出地方歷史變遷和社會心理流變,“不僅具有中原歷史文化的厚重感,更洋溢著積極進取的時代變革精神;不僅關聯著完整的家園夢想與鄉土情懷,更表征著完整的社會倫理規范,成為對一個古樸醇厚的文化傳統的深情守望”。[3]早已聞名于世的洛陽水席文化屬于筵宴文化,源起唐代已有千年歷史,二十道菜,章法有序。在漫長的發展中早已是中原地區民俗與民風的一種生動表達,融入了民間自發形成且廣泛認同的社會政治觀念、道德觀念、文化藝術觀念,河南電影從美食塑造上推廣了中原飲食文化,提升了河南形象的影響力。
(二)視聽盛宴里的中原戲曲文化
在河南,電影與戲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戲曲電影將中國傳統戲曲藝術通過運用電影蒙太奇手段而形成一種具有濃重中國文化特色的電影形式。豫劇代表著河南獨特的文化形態,豫劇電影以影像的方式記錄了戲曲獨有的藝術表現,又通過銀幕對民族歷史以及中原文化認同起到了積極的傳承作用。20世紀80年代,豫劇電影綻放出多姿多彩的花朵,將豫劇的藝術精華融合于歷史故事、民俗傳說中,創作了大量弘揚中原文化的優秀豫劇電影作品。電影藝術的構思和題材的開掘,離不開豫劇扎根于民眾的民間性,凝聚世世代代中原人民的智慧。新時期豫劇電影進入了探索與嘗試階段,大部分的豫劇電影在保留戲曲特色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電影視聽傳播手段的創新,包括鏡頭、景別、構圖、舞臺美術和服裝設計等,其中《程嬰救孤》《清風亭》《新大祭樁》等塑造了性格鮮活的“忠孝義節”的傳統故事,世代相傳,“崇德尚仁尚義”成為民族精神背后的深層力量,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價值觀念、道德風尚和性格特點。優秀的豫劇作品更是展現了中國戲曲文化的風采,名揚海外,實現戲曲文化的跨文化傳播,進一步擴大了豫劇的影響力。《程嬰救孤》被譽為這一時期河南戲曲電影的成功之篇,把元雜劇流傳的“趙氏孤兒”用豫劇的創作方式、加工、潤色等形式獲得了新的傳播,“導演運用電影手法將戲曲表演程式進行整合、截取,在不破壞與客觀環境統一的原則下展示戲曲程式,增強了戲曲電影‘戲’的屬性”[4],通過豐富的人文內涵與美妙的視覺效果,在影像化的感知體驗中潛移默化注入了中原地域文化價值,讓作品充滿極強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三)空間敘事環境下的河南人形象
電影故事的發生必須依托一定的發生空間,使電影能最大限度自然而生動地呈現場景,賦予地域一定的個性與生命,受眾在故事的講述中和審美體驗的愉悅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影像中的地域形象。區域文化形象就是特定區域文化普遍反映出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行為方式、制度形態等文化因素和狀態,在社會公眾心目中所形成的綜合表象或印象。[5]河南電影的拍攝地多選擇省內:洛陽、開封、堯山、輝縣、新政、嵩縣、登封、商丘等歷史文化名城,群山環抱,綠樹掩映,古樸寧靜。地域文化生活中的獨特空間,培育著鄉土真實的歷史生活和普通的河南農民形象。農業文明對中華民族精神個性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中華民族的中和、仁愛、重功、勤儉、自強等優秀品質,幾乎無一不與中原農業文明的影響有關。河南電影人有些出身于河南農村,有著濃郁的鄉土意識,《黑蛋,快跑》《幸福的白天鵝》《念書的孩子》《好好地活著》等作品意在通過電影敘事來展示河南農民生存的境遇,洞悉生存困擾的深層成因,以生存理念重新確立和尋找河南人未來的文化身份。他們運用電影各種敘事技巧,構造了豐富多樣的人物、故事和情感,令人深刻的地域形象或鮮活的人物形象代表著當地真實生活的風土人情,直接引發觀眾的生命情感共鳴。通過移情作用,激發了受眾對故事發生城市的文化、風俗、歷史、傳統以及河南形象的內涵產生興趣和欲望。
《不是鬧著玩兒的》《就是鬧著玩兒的》《還是鬧著玩兒的》均以喜聞樂見的形式,用河南地域的方言也成為影視創作的重要素材,將方言參與并豐富著電影敘事的節奏,從視聽上充滿了濃厚的鄉土地域氣息,用電影語言蘊含著豐富的生活內涵,表達了一種純粹的藝術風格,這在某種層面上增加了觀眾的欣賞欲望和故事的戲劇效果。中原文化的人格理想大都體現出一種對人的內在品格和外在行為一致性的認識。電影中的影像形塑與文學中形象敘事有著共通之處,都在立求通過人物語言讓創建的“人物”活著,不僅是在敘事話語上,敘事空間、敘事節奏等方面導向敘事形象的生動性與完整性,形象本身進行深刻的思想情感交流。電影《李學生》由以“河南好人”“商丘好人”李學生的真人真事為原型創作,演繹與體現著中原地區良善的民風,質樸純真,運用藝術逼真地呈現了“中原文化的獻身精神”,用中原地區深厚的文化積淀塑造了河南人精神品格。
三、結 語
“河南形象”具有多指向、多維度、多領域、多關聯的研究特點,與不同的學科之間有著交叉和結合點,中原區域文化既是地域性的,也是多元性的,河南電影人作為影像傳播的第一行為主體,把客觀世界的中原區域文化信息轉化為電影文本,利用主題意蘊——受眾接受的影像溝通過程,融合本土的文化傾向和價值認知體系,開拓題材,內涵詮釋,解讀加工,通過光影手段再把電影文本轉化為運動的藝術形象,在這其中,一方面地域與文化決定著藝術創作的走向,而另一方面電影也成為文化的記憶,傳承著文化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