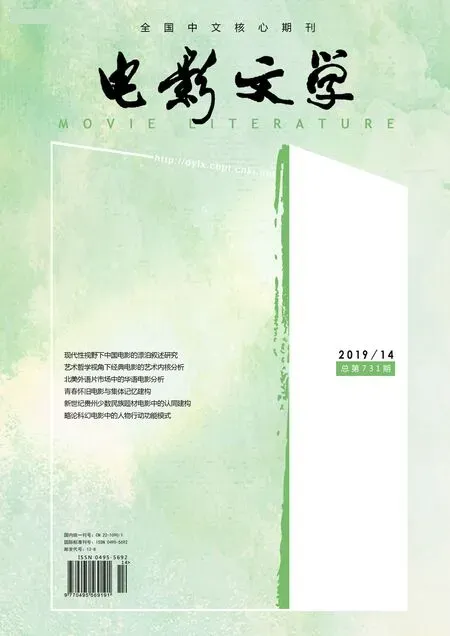藝術哲學視角下經典電影的藝術內核分析
屈云東 袁靜晗
(1.中南大學 建筑藝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0;2.云南大學 昌新國際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一、電影本質的藝術哲學探析
電影不僅是20世紀以來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更是一種結合了時空、動靜、造型、節奏的綜合型藝術。影像所具有的直觀性和便捷性,賦予了電影承載真實瞬間、故事、情感的能力,為電影插上想象的翅膀,跨越時空與國界,自由地翱翔。
在此,我們將把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方式來進行分析研究,基于丹納的藝術哲學理論視角,借助丹納的《藝術哲學》中的科學精神,以經典作品作為切入點,對備受關注的電影藝術進行探討。詮釋在哲學視角下電影藝術的本質,探究電影藝術中的“典型”,旨在對電影藝術本身形成一個明確的認識,推進電影藝術的健康發展。
電影,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的影像畫面。[1]產生于丹納的故鄉法國,1911年在電影先驅者喬托·卡努杜的倡導下,電影成為繼繪畫、音樂、雕塑、舞蹈、建筑、詩歌之后的第七種藝術。[2]
這種結合了所有的藝術種類的藝術,并未把欣賞藝術的門檻抬高,反而讓藝術更加“親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有的人很少甚至從未去畫廊參觀畫展,去禮堂聽音樂會、朗誦莎士比亞的詩歌,然而幾乎所有人,不論何種身份地位,都觀看過電影,無論是通過影院的大銀幕,抑或電視機的小熒屏,所有人都在主動或者被動地成為電影的受眾,讓電影成為最具群眾性的藝術,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播,形成一股電影的熱潮。
既然我們把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類型來研究,就需要探討電影作為一門藝術,它的本質是什么?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藝術的本質首先是一種模仿,一出戲,一部小說,都企圖很正確地表現一些真實的人物。[3]那么電影藝術的本質是否也適用于這個觀點?這就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首先,從電影的內容表現上看,拍攝制作一部電影首先需要有劇本作為支撐,電影劇本有原創的劇本和基于文學作品改編的劇本。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比如《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活著》《霸王別姬》等觀眾熟悉的電影,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文學的抽象內涵與電影的具象體現令電影這門藝術具備了強力吸引大眾的能力, 但并不是所有文學作品都適合改編成電影,實際上還存在著近乎硬性的條件限制; 換言之,并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能夠輕而易舉地被改編為電影。例如嚴肅文學類的作品其實是極難改編成電影的,因為,嚴肅文學類作品中的所有意象與審美均需要借助深刻的理性思辨才能得以在讀者的腦海中完成。那么什么類型的文學作品才適合改編成電影呢?我們需要認識到電影是受到時間限制的,一般電影時長都在100~150分鐘之內,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呈現一部文學作品,這個文學作品必須要講述一個故事,擁有鮮明的故事情節和明確的人物關系,能在有限的電影時長內向觀眾清晰講述。原創的電影劇本也是如此,在規定的時長下,用符合視聽語言的方式,講述一個故事或交代一種狀態。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電影同文學作品一樣需要情節作為支撐,基于電影視聽語言的特點,由一系列展示人物性格、表現人物之間以及人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具體事件構成的情節是驅動一部電影敘述的核心。而情節的來源正是現實生活發生的事件,取材于現實中發生過甚至正在進行的事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早已證實過,故事情節的來源正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模仿,取材于現實中的人物,企圖表現現實中的事件與沖突。
電影藝術中也存在著科幻片、動畫片等放棄了特定的現實背景,塑造具有創世紀意義奇幻神話的電影類型,比如E.T、《阿凡達》、宮崎駿的動漫電影等類型電影的存在,這些電影情節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無跡可循,那么這些電影的創作是否是來源于模仿呢?首先可以肯定的這些類型的電影同樣是靠情節驅動,雖然科幻動漫的電影情節與現實生活存在很大差異,但在此類電影內容的處理中,通常將主角的困境從冒險異世界的設定轉為城市、國家或與許多國家密切相關的公共領域,把主角定位為平凡人,與身邊的小人物發生著交集。通過這種方式,與社會生活相聯系。可以看出這些情節建立在現實生活或已有知識的基礎上,沒有一定的知識經驗作為積累,也無法對未來,對異世界進行合理想象,故而這類電影的情節同樣源于模仿,是一種對現實異化、夸張、變形的模仿。
其次,從電影的表現方式上看,電影最終通過大銀幕呈現,讓受眾觀看。為了讓受眾在觀看電影時集中注意力,電影形成了自己的視聽語言體系,不同于話劇與朗誦,電影情節的表現需要不斷變化的場景作為支撐,情節的帶入依靠著場景的轉換。電影早期的場景來源于現實場景的直接取材與呈現,形成一種代入感,觀眾不能進入一幅畫中,不能在歌劇表演時登上舞臺,但電影的取景地就在現實生活中,觀眾隨時能走到這個場景。例如電影《羅馬假日》拍攝地就在羅馬的大街小巷,觀眾可以隨時走進電影的拍攝取景地,給人一種故事真實發生的代入感。隨著后期制作的成熟,電影場景的拍攝不再需要實地取景,利用后期技術模擬出現實的場景,保持這種身臨其境的代入感。電影塑造的這種代入感的表現方式就來自電影對現實場景的模仿。不管是最初的黑白電影,還是如今的3D電影,電影追求的都是一種讓人仿佛身臨其境的視覺效果。這種時空再現性緊扣著受眾的心弦,引起熱烈的反響。
通過對電影藝術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進行分析之后,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電影藝術也是一種源自“模仿”的藝術,是一種運用文學、造型、設計、音樂等多種藝術形態,實現對現實生活進行一種動態的模仿。
在確定了電影的本質之后,還需要探討電影藝術的目的,電影的目的是否是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的絕對正確的模仿?丹納在藝術的本質中提出:藝術品的目的是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各個部分的關系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3]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電影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對現實生活進行1∶1的呈現和精確的還原,因為電影的時空不是線性的。空間方面,上文提到了電影情節的表現需要不斷變化的場景作為支撐,情節的帶入依靠著場景的轉換;時間方面,電影并不是為了在兩個小時的時長之內講述兩個小時發生的事情,電影時間跨度可以長達幾個世紀。在《阿甘正傳》中,可以看到,阿甘從少年時的奔跑,一直到了大學;珍妮離開阿甘后,阿甘的奔跑,可以看到,電影并沒有忠實地還原阿甘如何從少年到大學,也沒有記錄阿甘在路上如何奔跑,電影想強調的只是阿甘身上奔跑的這一特性。
電影藝術是怎樣表現主要特征或重要觀念的呢?這里就要提到電影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蒙太奇。蒙太奇也稱為電影后期剪輯,是電影的基本特征之一,通過后期的剪切編輯實現畫面的切換,場景的變化,時間的變幻,人物的成長。通過蒙太奇來掌控敘事的節奏,組織情節,形成整體。不難發現,電影之所以有蒙太奇,就是為了對組成電影的情節進行有計劃的改變,比現實生活中真實的情節,更加清楚地突出某個重要觀念,突出電影最想表現的關鍵部分。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電影藝術的本質也來源于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模仿”,其目的不是對現實的精確還原,而是描繪最主要的或最突出的特性。電影利用蒙太奇的方法有計劃地改變和組織部分,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概念,比現實中的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完全。
二、 電影《活著》與《阿甘正傳》概述
丹納認為藝術作品存在著“等級”,群眾和鑒賞家決定著等級,估定藝術品的價值,受眾手中有著評價藝術品的“尺度”,如莎士比亞的詩歌、莫扎特的音樂、萊奧納多·達·芬奇的畫等在藝術中占據著至高的位置,成為藝術評價的標準與創作的山峰。這些藝術家及其作品成為藝術中的“典型”,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些作品體現著藝術的“特征”,研究這些作品,對藝術的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基于丹納對藝術的“特征”分析,我們從電影中的經典出發,對經典中國電影《活著》與美國電影《阿甘正傳》的分析出發,分析電影這門藝術里的典型,對電影中的“特征”進行探析。
選擇電影《活著》與《阿甘正傳》作為分析的樣本,原因在于:首先兩部電影都上映于1994年,都改編自本國家的文學作品,都是表現時代變遷的史詩電影,敘事的時空有著相似性,縱向發展有著可對比性;其次兩部電影雖然內容與風格迥異,但是卻一致地獲得了世界范圍的認可,來自中國的《活著》和來自美國的《阿甘正傳》兩部電影都被BBC評為21世紀最偉大百部電影,擁有著超越時代超越空間的影響力,橫向發展也有著可對比性。《阿甘正傳》獲得了第67屆奧斯卡金像獎、第4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第19屆日本電影學院獎、第39屆意大利大衛獎等,同時也在中國各大擁有電影評分的平臺,一直保持至少9分(10分制)以上的高分。《活著》在中國各大擁有電影評分的平臺,一直保持至少9分(10分制)以上的高分,在世界范圍內也獲得了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第48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第52屆美國電影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綜上,不難發現,兩部電影是電影藝術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將它們作為樣本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活著》是張藝謀導演作品,改編自中國作家余華同名小說。在電影中主人公福貴是嗜賭如命的紈绔子弟,在經歷了被抓到國民黨的軍隊充軍,之后又陰差陽錯地成了軍隊的戰俘。經歷了諸多波折后,福貴踏上了歸家的路程,回到家中卻發現福貴的母親已經西去,他的女兒鳳霞因為一場大病變成了啞巴。一家人繼續過著清貧而又幸福的日子。在一場意外中,福貴失去了自己的兒子——友慶,然而這卻不是福貴一家不幸的終點,命運似乎從不肯眷顧福貴一家。鳳霞懷孕生子時,因為難產而死。福貴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女兒。福貴給孫子取名為饅頭。雖然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是福貴依舊認為日子總會越過越好。電影以中國近代開始經歷的數次變遷為背景,訴說著男主角福貴的一生。
《阿甘正傳》是羅伯特·澤米吉斯導演作品,改編自美國作家溫斯頓·格盧姆同名小說,主人公阿甘是個智商只有75的低能兒,阿甘的智力雖然有所缺憾,但是在體能方面卻展現出了過人的天賦。阿甘與奔跑注定相互成就,中學時期,他在躲避同校學生的霸凌的過程中,闖入了一所大學的橄欖球比賽現場,被教練一眼相中,自此阿甘成為大學生,也是學校的橄欖球巨星。大學畢業后,阿甘自愿參軍去了越南戰場。戰爭結束后,阿甘成為戰爭英雄并受到了總統的接見。影片的最后,阿甘成為名人、成為企業家、成為父親。阿甘的一生經歷了世界風云變幻的各個歷史節點,但無論周遭的人與事物如何變化,他依然如故,勇敢而善良,“傻人有傻福”,不停地創造奇跡。
三、“特征”理論視角下經典電影的藝術內核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了藝術的“特征”理論:特征存在著不同的等級,一個特征本身越不容易變化越重要,特征之所以穩定,是因為更接近本質,在更大的范圍內出現,只能由更劇烈的變革加以鏟除,最穩定的特征占據最高最重要的地位。特征越重要越有益,占的地位就越高,而表現這種特征的藝術品地位也越高。[4]現在我們將這一理論運用到對電影的分析中來,探討“特征”是如何在電影藝術中體現。需要注意的是,電影作為綜合的影像藝術,它同時運用音樂、畫面、造型等多種藝術手段,表現豐富的場景和內容,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動態藝術,當我們基于丹納藝術哲學的視角對電影進行分析時,需要考慮到它可能體現了一種特征,也可能反映著多種特征,所以當我們運用丹納的“特征”理論分析經典電影時,應該分層次,對每個特征進行分析。
(一)時代流行影響下的經典電影
丹納認為藝術中特征的表層是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這些特征是時代的流行風氣,不同時期的電影呈現出不同的審美特征,完全以流行為依托的電影注定了其易改變和不穩固的命運。中美與《阿甘正傳》和《活著》在1994年同期上映的電影據不完全統計約有將近千部,許多電影在當時也獲得了很高的關注,爾后在時代的洪流里逐漸失去了奪目的光彩,這類電影如中國香港的《鑄劍》、美國的《傾城佳話》。《鑄劍》制作拍攝于20世紀90年代,改編自魯迅同名小說,電影通過眉間尺的復仇路上從被通緝到在宴之敖的幫助下殘忍復仇的故事,在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世界發展的主流的背景下,體現了90年代處在轉型與束縛中美好與黑暗的思考。美國的《傾城佳話》講述的善良的警察與美麗的服務員伊芳的感人故事,是對90年代末,東歐劇變后,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樂觀與自由精神的一種體現。兩部電影應時代而生,不僅電影中人物的性格特征符合同時代的主流,電影的題材也契合著當時社會的心境。然而時代在變,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也會隨之改變,受眾喜愛的角色形象也在改變,為某一時期的審美量身定制的電影只能留在原地,成為一種時代的記憶。
《活著》與《阿甘正傳》中其實也有對當代的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的塑造,例如《活著》中的人物“春生”,懷揣著夢想,充滿能量,敢于嘗試新事物,在環境轉變中不斷掙扎。《阿甘正傳》中的鄧·泰勒中校,忠誠勇敢有信仰,遇到挫折也能有第二次“站起來”的機會。與同時代電影不同的是,《活著》與《阿甘正傳》把這些特征作為電影的配角,而不是主要表現部分,沒有為了滿足當時的審美而對原著中的時代交替與歷史變遷進行淡化。
(二) 經典電影的時代氣候依托
電影把符合時代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當作配角來表現,與他們和電影的主角以及其他人物一同放到大時代里,在滾滾向前的馬車中,經歷著考驗、經歷著變遷。正如不斷變化的表層特征一樣,電影中的每一個人物自身也不斷在成長,構成了大時代下一幅富于變幻的眾生相。
這一特點也讓這兩部電影到達了特征的第三層:特征的第三層是非常廣闊非常深厚的一層,這一層可以存在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這個特征附帶著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學、愛情、家庭,都留著主要特征的痕跡。 一部電影若想符合藝術的這一層特征,需要有思想情感和歷史背景作為支撐,不僅僅局限單個的角色或事件,而是以歷史變遷的眼光透視一個時代或一整個時期。《活著》和《阿甘正傳》都是以社會變遷為背景的電影,《活著》從20世紀40年代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沒落開始,電影的時間軌跡一直延伸至社會主義新中國;《阿甘正傳》以20世紀中期作為起點,將解除種族隔離、越戰、水門事件、中美“乒乓外交”等美國史上重要事件融入電影。以人物為線索,將小人物融入大時代,表示了時代氣候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狀態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對政治歷史環境的揭露是兩部電影共同意圖的體現。在兩部電影中,時代的政治事件不只是作為單純的背景來加以敘述,而是被置于主要地位,成為電影的重要敘事載體。人物與政治被捆綁到一起,密不可分,電影所想表現的不只是人物的成長,更是一種政治的歷史的時代風貌。
《活著》以20世紀40年代初封建氣息濃重的中國鄉鎮生活為開篇,到后來的革命戰爭、新中國成立、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社會主義改造、“文革”等,影片跨越4個時期的變化,以福貴的個人經歷透視中國近一個世紀的變遷歷程。《阿甘正傳》從智力低于常人的主角阿甘的視角展現了美國社會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歷程,阿甘的成長歷史就是一部美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史。[4]當然,對于到達了這一層特征的藝術,僅有歷史是不夠的,因為這個特征將要在人類的記憶中永遠保存,是人類發展的主要形態之一,所以藝術還需要關照歷史中的人物與人物的思想情感狀態。兩部電影并不是僅為了對歷史進行一個線性的敘述,而是站在歷史的角度對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人的狀態進行觀察與思考,對社會的發展以及人的進步進行有益的探索。在電影《活著》中,我們體會著政治對人性的壓抑以及人在歷史大潮中惶惶然的生存之境,比如福貴一直熱愛的皮影戲,在家境沒落時期,福貴用皮影謀生;之后參加革命,福貴在軍營中表演皮影戲振奮軍心;“大躍進”時期,福貴的舞臺變成了全民煉鋼鐵的工廠,福貴用皮影戲為集體勞動的工人們打氣,皮影戲便隨著福貴成長,一度成為福貴的立身之本,甚至在戰爭時期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政治能讓你成為英雄,也能讓你成為罪惡,福貴的皮影戲工具在“文革”中被定義為“四舊”,被一把火化為灰燼。諷刺的是燒了福貴的皮影戲工具的鎮長積極響應破四舊,最后卻被打入“走資派”。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壞,福貴不知道,鎮長也不知道,因為在那個時代好壞的標準一直在變化,只有上層建筑有權制定這種標準,人民的聲音是微弱的,是不被傾聽的。《阿甘正傳》中立志戰死沙場成為英雄的丹中校,卻在戰爭中活到了最后。失去了雙腿的丹中校離開戰場后,無法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只能領著政府的救濟金度日。稀里糊涂參軍的阿甘,沒有任何遠大的目標,只知道服從指令,最后不僅活下來并且成為戰爭英雄,被總統親自授予勛章。丹中校與阿甘境遇的落差,不僅是對戲劇沖突的強化,也是影片對戰爭的一種反思。與精明能干的丹中校相比,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阿甘似乎不是戰爭英雄的有力候選人,正如與強大的美國相比越南似乎以卵擊石,然而卻把美國拖入了十年的越戰泥潭,損失慘重,電影利用對荒誕現實的表現,給夢想成為世界霸主的美國敲響著警鐘。兩部電影以歷史為基調,風格卻是荒誕的,這正是對歷史發展與時代精神的一種體現與反思。
兩部電影除了從宏觀上反映時代之外,也有著從微觀角度對社會進行的觀察。例如《阿甘正傳》中很多情節都反應的種族歧視的現象,在當下的美國仍是社會關注的問題,《活著》中表現的女性在社會中的“失語”,也是當今中國存在的社會現象。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兩部電影在藝術表現上切合了丹納對于藝術特征中第三層特征的特點,具有了跨時代的深度與廣度。這種根植于歷史與時代的藝術特征是相對穩固的。
(三) 經典電影對“原始地層”的觸碰
丹納在特征理論中強調,第三層并不是藝術特征的最后一層,因為這些典型無論如何頑強與穩固,仍然是要被消滅的,一個民族在長久的生命中要經歷好幾回這一類的更新,在更新中主義與思想情感抑或是文明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隕落,最后留下來的,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只有一個民族的本來面目。它不會因為世代連綿而改變,并且會作為構成民族的特性始終存在,這才是原始地層。一個民族他們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能,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響。[3]那么《活著》與《阿甘正傳》是否具有這種原始底層般的特征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意識到兩部電影距今僅有23年,整個電影藝術從誕生距今也不過百年的時間,所以兩部電影是否觸及最主要的特征,還需要經歷更長的時間來作為檢驗,這里僅進行一種階段性的探討。《活著》和《阿甘正傳》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電影敘事風格迥異,但卻同時取得了世界范圍的認可,除了歷史與文明的原因,能打動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受眾,藝術需要關注的是人本身。《活著》和《阿甘正傳》最重要的藝術特征是反映了人為了生存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在不斷更迭的境遇下人性的堅韌,這也是一個種族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的必備特征之一。電影《活著》的主角福貴年少紈绔,嗜賭且非常任性,給家里帶來了很多麻煩,最后甚至輸掉了祖傳的宅子。福貴家不再是富有的大戶,福貴也不再是衣食無憂的少爺,福貴必須想辦法謀生,隨著境遇的改變,福貴也隨之成長,開始承擔起一個父親、丈夫、兒子的責任。在角色的轉變中,總是會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福貴經歷了被抓捕,經歷了戰爭,經歷了長時間與家人的分離,見證了陪伴他多年的皮影被付之一炬,甚至見證了自己兒子的死亡。挫折與困難仿佛滾雪球般沖擊著福貴的一生,考驗著福貴一家的韌性。當所有人都認為福貴會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擊倒時,福貴卻一直保持站立的姿態,在與生活交手的這些年,福貴勢單力薄搖搖晃晃卻從未倒下。一開始被動絕望自發的承受,到后來的自覺想辦法,在活著的路上跌跌撞撞,依舊保持對活著的熱誠與希望。
觀眾不自覺地被電影塑造的福貴這個角色深深打動,不僅是因為福貴的機智與堅強,更是因為從福貴身上看到人的韌性和對生命的敬畏。正如原著作者余華所說“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這也是中華民族千年間經歷無數變遷依舊存在的本質特征之一。
電影《阿甘正傳》的主角阿甘雖然是智力低于常人的智障者,但是僅比正常人的智力平均值低了5分。阿甘是幸運的,作為低能兒的他靠著過人的運動天賦進入了大學;大學畢業后陰差陽錯地參了軍,卻比任何人都適應軍營生活,并成為戰爭英雄;退役后繼承了戰友的遺愿開始捕蝦,成為富翁;功成名就后回到家,與摯愛珍妮結了婚,和自己的兒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從一無所有的低能兒到名利雙收的英雄,阿甘的一生是被幸運女神親吻過的一生。然而幸運的背后也有著常人想象不到的艱辛,阿甘也是不幸的,作為低能兒從小被欺凌,直到大學畢業參軍后才擁有了除了珍妮以外的第二個朋友——巴布,然而在戰爭中,救了連隊的所有人的阿甘卻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巴布;不斷地追逐著自己心愛的人珍妮,卻不斷被珍妮推開,珍妮最后雖然還是回到了阿甘身邊,而那時珍妮卻已身患絕癥;可以看出阿甘的一生是不斷得到也不斷失去的一生,他得到了成功,得到了名聲,得到了財富,卻失去了巴布,失去了母親,失去了珍妮,阿甘許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在奔跑。阿甘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仍是由生活的碎片組成,發生在阿甘身上的事,普通人身上同樣會遇到:被心愛的人拒絕,被人看輕,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目標在何方,但是在努力的路上,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方向。有幸運的時候,也有隨波逐流的時候,在得到與失去的拉扯之間,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得到了不斷的成長。鍥而不舍的獨立精神是美利堅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
電影的觀眾來自全世界,來自不用的國家,有著不同文化背景,觀眾不一定能理解電影所想傳達的文明與時代的特征以及背后的寓意,但是每個觀眾在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感情世界中都能找到這個兩部電影所體現的人性的韌性這一典型特征中找到自己成長的影子,生活的影子。就像《阿甘正傳》的結尾,阿甘所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每個人都有注定的命運,或者我們的生命充滿著偶然與不確定,我想兩者都有吧。”每個民族的背景、文化、精神和生命歷程都存在著差異,但是面對生活時,人類為生存所做出的努力,在生活面前展現出的堅韌,這一特征是同樣的,是最經久深刻,不隨時間褪色的。1994年至今已有24個年頭,日本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曾說過:人生和電影都是以余味定輸贏的。時代在不斷發展,電影制作的技術越來越先進,制作周期越來越短,24年間產出了上萬部電影,而《活著》和《阿甘正傳》通過了時間的考驗,至今仍有著鮮活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影響力,不斷被人提起,仍能引起共鳴,散發著歷久彌新的醇香。兩部電影之所以能成為電影中的“典型”,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兩部電影能成為電影藝術中的經典,是因為兩部電影通過綜合的動態的電影藝術反映著不同層次的特征,兩部電影并不滿足于當下的流行,而是層層深入,在反映了文明與時代特征的基礎上觸及了“原始底層”的民族的特征,經久深刻,從而成為經典。
四、結 語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電影藝術的本質也來源于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模仿”,其目的不是對現實的精確還原,而是表現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電影利用蒙太奇的方法有計劃地改變和組織部分,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點,也就是某個重要的概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完全。
電影藝術中也存在著典型的特征,特征越穩定,電影作品越容易取得高的地位,但是電影藝術與其他藝術不同的是,電影藝術是綜合的、動態的藝術,因此在經典電影中往往不只滿足于反映某一個特征,而是通過人物的塑造以及情節的設置,由淺到深地反映著不同層次的特征。首先一部經典電影是立足于當代的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的,這一特征不僅決定著電影在當時的接受程度,也影響著后世對不同時代的流行特征風氣的了解;然而要成為經典電影,絕不能被當時的生活習慣與性格特征所局限,在這一特征的基礎上,要進入藝術特征的下一層次——歷史、時代、文明,著眼于時代大環境,反映著社會的現象與問題,引發著觀眾的思索,這一特征更具有穩定性,決定了電影的深度和廣度;最后,經典電影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在前面特征的基礎上,嘗試去觸碰最原始的底層,探討反映的是民族與人性的本質這一特征最為穩定持久,也最打動人心。由此,就誕生了電影藝術中的經典,被載入史冊的同時,也讓電影藝術發光發熱。
當前我們對電影的研究,更多的是進行一種敘事與視聽語言的批判,而缺少對電影本身的一種哲學思考。電影作為最具群眾基礎的藝術,其發生發展需要哲學作為指引。以充滿嚴謹科學精神的丹納《藝術哲學》研究為基礎,能給電影的發展提供一種哲學的視角,對電影藝術如何為現實帶來有益的影響,從本質出發,提供一種思考。然而,我們要認識到丹納的藝術哲學忽視了經濟因素的局限性,因為電影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且不同于以往的藝術形式,電影是群體性藝術,在電影提出概念到實現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財力與人力的投入。但是,丹納的藝術哲學可以指引我們邁出第一步,在此基礎上綜合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多種因素,對電影藝術進行分析探討,讓電影走向更遠的藝術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