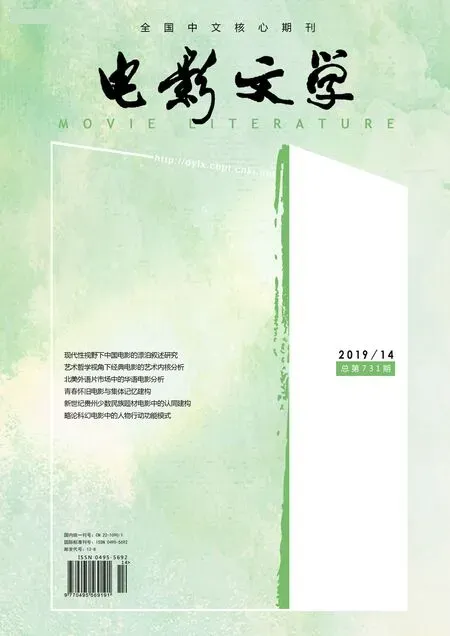女性視角、文化碰撞與真實故事:《沂蒙六姐妹》的敘事美學解讀
邵珠春(棗莊學院,山東 棗莊 277160;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9)
作為山東電影制片廠為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獻禮片,“沂蒙六姐妹”所受到的關注已經遠遠超過電影本身。由沂蒙地區抗戰期間發生的真實人物改編而成的《沂蒙六姐妹》,本身集合了沂蒙六姐妹與一系列沂蒙紅嫂的真實故事,因此,無論是主流意識的宣傳還是影視角色塑造的需要,《沂蒙六姐妹》都被寄予極高的期望。在此背景下,如何對《沂蒙六姐妹》進行電影敘事藝術的創新,就成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從敘事層面來看,電影《沂蒙六姐妹》的最大創新在于敘事視角的獨特,影片以月芬為主線,以第一人稱視角為敘述視角,通過月芬的成長經歷,向觀眾展示了真實的戰爭故事畫面;從故事內容來說,愛情成為貫穿整部電影的情感主線,編劇在戰爭題材電影中貫穿愛情的全新視角為戰爭題材電影開辟了全新的視角與智慧;從敘事空間來看,在創造的當時,沂蒙六姐妹的原型人物仍有四個健在,在電影《沂蒙六姐妹》創作過程中如何處理人物真實與理想的關系,直接關系到影片創作的成敗;從色調運用來看,影片以月芬衣服的紅色調與灰冷的背景色調形成強烈對比,創造出一種浪漫與悲壯、理想與現實交錯縱橫的空間結構。影片以女性視角凸顯出戰爭對人類命運的摧殘,在人物性格的不同塑造中刻畫出戰爭年代女性的偉大,創造出一個個感情真實、個性豐滿的沂蒙紅嫂形象,完成了沂蒙紅嫂的價值提升與形象塑造,實現了《沂蒙六姐妹》電影藝術的敘事創新,開辟了戰爭題材電影表現的獨特視角。
一、女性視角下的生命張力
(一)戰爭題材的敘事創新
《沂蒙六姐妹》一改主旋律戰爭電影表現中對男性英雄群體的表現,以沂蒙六姐妹為代表的普通女性群體為視角,標志著電影《沂蒙六姐妹》在敘事視角上的獨特與新鮮,不同于《紅色娘子軍》《戰火中的青春》等電影對女性戰士形象的塑造,此片中的女性是真正普通的女性形象,是女性視角下的愛情與戰爭,影片圍繞戰爭中的女性塑造出立體而感人的人物形象。影片以新娘月芬為主線,將整個沂蒙山區的普通女性串聯起來,使敘事線索更為真實和連貫。通過歷史的剖析解讀個體的命運,才能更好地理解個體在歷史情境中成長的隱痛,才能追問命運的分離聚合又有怎樣的成因。[1]女性視角下的生命張力,直接體現為以月芬為代表的普通女性的愛情悲劇人生。外表柔弱的女性群體在戰爭的背景下,迸發出超乎尋常的生命力與韌性。在宏大的戰爭敘事結構中,女性敘事常常處于失語的、被遺忘的狀態。月芬作為貫穿電影《沂蒙六姐妹》始終的敘事焦點,突出地反映出戰爭題材中女性視角敘事結構的復雜性與情感表現的豐富性。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結婚的月芬,美麗、溫柔、善良,與丈夫南成從未謀面。影片一開始展示女性視角是月芬與嫂子抱著的公雞舉行的拜堂儀式,男性的缺席顯示出這場婚姻的特殊性,也暗示了月芬婚姻的悲劇性。剛剛嫁入郝家的月芬,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知道南成的樣子,幾次向嫂子打聽從未謀面的丈夫的相貌與情況,當她從嫂子嘴里得知丈夫和小侄子長得像便急忙跑去端詳熟睡的侄兒;當部隊從村莊經過時,她急切地在行進的隊伍里尋找丈夫的身影。影片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展示出戰爭年代女性情感的真實性與生活性,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現實主義敘事產生了強烈的情感沖擊,在寫實與詩意的影像敘事中給觀眾造成身臨其境的當下體驗。
月芬因借糧回娘家而錯失了與丈夫唯一見面的機會,影片以嫂子上氣不接下氣地奔跑、月芬急切地奔跑、南成奔跑的蒙太奇處理手法,使畫面形成時空交錯的影像重疊,而最終的無法相聚將敘事進一步推向高潮,也更加渲染了整部影片的悲劇性。月芬由單純地在家守候變成主動去前線支前尋找丈夫的行蹤成為電影《沂蒙六姐妹》的一條敘事線索,揭示出女性對希望與夢想的勇敢追求。但是影片的敘事又不全是圍繞著月芬這一中心展開的,影片同樣講述了其他女性。因此,在敘事結構上,影片是以月芬為主線,同時兼顧其他女性的線索為敘事方式,在增強故事豐富性的同時又豐富了敘事的層次性。女性視角下的生命張力,還體現在月芬與春英的抗戰意識覺醒與獻血時情感爆發的瞬間。在支前擔架隊與急架火線橋的敘事過程中將這種女性力量的內在生命張力進一步擴張,勝利歸來時的白色喪禮則將女性視角下的生命張力表現到極致。
(二)戰爭后方的女性命運
《沂蒙六姐妹》通過對普通女性的細致刻畫,以全景式的視角和細膩的手法向我們展示出女性情感世界的豐富性與堅韌性。“以往的戰爭影片過于關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而忽視了同樣處在戰爭陰影下的普通女性。事實上戰爭從來沒有性別上的優待,戰爭從來沒有讓女人走開。”[2]影片以喜慶的結婚展開鋪墊,春英誘捕公雞的畫面和背景中隱約露出的“喜”字暗示出一場將要進行的婚禮。而春英懷抱公雞與月芬拜堂的畫面,顯示出這場婚禮的特殊性,公雞在此成為缺席男性的代表,也暗示出月芬命運的悲劇性。雷蒙·威廉斯在《現代悲劇》中認為:悲劇往往表現為理想主義者對抗命運的斗爭。它一方面是社會悲劇,“另一方面是個人悲劇:男人女人在他們最親密的關系中經受苦難并且被毀滅”。[3]影片以歡喜的紅色、結婚的場景為起點,以滿門忠烈的白色喪禮、白雪覆蓋的沂蒙山為終點,以郝家兩代人的犧牲凸顯出戰爭帶給女性群體的悲劇性。
女性是家庭的象征,戰爭在本質上體現為男性力量的角逐,隱喻的是對家庭與女性的守護。在革命戰爭年代,家的外延得到了延伸,小家的生存必然依附于國家的存在。在此,以沂蒙六姐妹為代表的年輕女性將對小家的需要放在一邊,承擔起維系大家庭的責任與擔當。對于這些普通女性來講,部隊就是她們的家人,所以當部隊從村中經過的時候,老百姓將煮好的雞蛋、新縫的軍鞋無私送給了路過的軍人。春英與月芬為了幫助像丈夫一樣的士兵而毅然選擇了擔架隊。一直到肩扛火線橋,最終將這種對大家庭的情感認同推向了高潮,她們扛起的不是普通的戰士,而是自己的家人;她們不僅扛起了戰爭的勝利,更扛起了民族的希望與未來。所以,孟良崮戰役最后取勝了,取勝的關鍵是人民。正是由于每一名解放軍戰士背后都有一群無私支持他的“家人”,才形成了他們為親人、為家、為國勇猛頑強的戰斗力。影片從女性群體的視角出發,呈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家庭觀。獨特的視角與相同的文化感受使觀眾獲得了一種與傳統主旋律電影不同的觀影體驗,增加了觀眾的身份認同與情感體驗,同時也拓展了主旋律電影的視角與深度。
影片沒有直接講述沂蒙山的男人,但月芬在獻血時震撼人心的那句“你瞎了嗎?俺們沂蒙山的男人都在前線哪!”帶給觀眾強烈的情感沖擊,使觀眾直觀感受到戰爭年代女性與男性群體的犧牲與奉獻。當沂蒙山的男人為國家、為革命奔赴前線、義無反顧時,后方的女性群體也自愿承擔起支前任務:攤煎餅、縫軍鞋、備馬草……所以,片中曲既唱出了沂蒙山普通女性群體的心聲,也唱出了后方女性對革命的奉獻和犧牲。“春風吹,柳葉青,我送哥哥去當兵,哥哥你參軍去遠方,我在后方生產忙,冬有棉衣夏有糧,請你把心放。送哥哥到軍營,參加隊伍真光榮。”
二、文化碰撞中的新舊文化
(一)地域文化的民間色調
《沂蒙六姐妹》大量還原了沂蒙地區的民俗文化,積極吸取了中國民間藝術的文化形式,在還原時代的同時也復活了傳統民間文化的內在生命力,從外在形式追求到內在民族氣質表現上都體現出獨特的民族審美文化,形成了獨具中國文化內涵的審美風格。首先,對傳統民俗的還原,這一幕表現在一開始的迎親隊伍中,吹吹打打的迎親場面與獨輪車上象征幸福美滿的大白饃饃,正是那個年代結婚時的重要嫁妝。其次,對民間藝術形式的還原。在送入洞房的一幕中,春英與月芬共同走出的門梁上貼滿的“門箋”,正是沂蒙剪紙藝術的一種,其形狀如小幡,紋飾如人勝,象征著喜慶與平安;在月芬的婚房中,貼在墻上的年畫也是沂蒙地區特有的民間藝術形式,是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最后,月芬繡的荷包高度還原了獨具時代特色的民族文化。據導演王坪講,為了追求盡可能還原那個年代的生活特點,荷包是由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繡出的,所象征的正是沂蒙紅嫂對前線丈夫的深切思念與美好祝福。正是導演用心去還原沂蒙農村70年前的時代風貌,才最終使影片具有了濃厚的中國美學特色。這種美學特色不僅體現在對傳統民族藝術的深刻還原上,同時也體現在導演為整部影片所賦予的詩意色彩上。以月芬為主線的紅色服裝,使整個藍灰色調的畫面影像變得生動而活潑。在電影中,這抹紅色所象征的不僅是革命,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賦予紅色的美好意象與祈盼。也正是這抹紅色,讓觀眾始終懷著一種希望,總盼望月芬與南成終能團圓,家人都能平安。
(二)新舊文化的碰撞融合
在月芬的拜堂儀式上,由蘭花帶領的一群年輕女性熱情洋溢的唱詞,正反映出革命文化對舊文化的吸收與改造。“根據地里新氣象”的唱詞一出,伴隨的是傳統文化的“一拜天地”。在此處,革命文化與民俗文化產生了時空交錯的影像重疊,伴隨“打破封建理應當呀”歌詞同步出現的則是月芬與春英懷抱公雞對拜的畫面,在視覺上形成了新舊文化強烈的矛盾與沖突,這種看似矛盾的文化沖突所反映的正是兩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秀兒、小鶴與月芬一起看隊伍時,秀兒對月芬說“連面兒都沒見就嫁了,這可不像在識字班啊”,體現出新文化對舊文化的否定與批判。在舊文化與新文化碰撞交融的過程中,兩種文化形式總是并行存在、此消彼長的。在這一過程中,沂蒙精神從文化層面反映出一種文化結構與權力結構,實質上反映的是黨領導下的文化發展模式,是先進文化對舊文化的改造、吸收與重新建構,使之適應時代的發展。沂蒙精神的形成正是兩種文化相互融合與適應的結果,也反映出黨的文化路線的科學性,通過新文化的融入使舊文化重新煥發出生機與活力,從而為沂蒙地區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和思想保證。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雖然看似矛盾的文化沖突,其所反映的正是革命文化的適應性和人民性。
沂蒙精神的形成反映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革命的成功一方面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在世人眼中,沂蒙老區往往象征著貧窮與落后,特別是在看到影片中的石頭板房時。實際上在當時那個年代,沂蒙地區恰如延安等革命根據地一樣,是新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因此,片中的沂蒙六姐妹無論是裝扮還是發型都是非常潮流的,沂蒙地區的年輕人對新文化的接受是熱烈與積極的,一如沂蒙六姐妹對革命的支持與憧憬。因此,片中除去幾處具有中國傳統民俗色彩的文化形式之外,所展現的幾乎都是經過革命文化洗禮的新文化樣式。《沂蒙六姐妹》所反映的沂蒙精神作為新時代文化建構,正反映出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品性。
三、真實故事的時空再現
(一)革命符號的藝術呈現
《沂蒙六姐妹》是沂蒙地區廣泛流傳的革命戰爭年代的真實歷史故事,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是中國革命文化的象征符號。因此,編劇與導演對沂蒙精神的藝術創作過程,既依賴于對沂蒙文化的特殊情感,又依賴于對沂蒙文化的價值判斷和生活關照。沂蒙精神被藝術創造活動賦予外形的過程,不僅體現在外在物質媒介,更體現在激發美感的形式結構中,這些形式的內部結構使沂蒙精神具有了視覺感染力,這些形式不是外在的技巧或手段,而是沂蒙精神生命本身的基本組成部分。沂蒙精神的符號性就體現在這些具體可感的形式結構之中,沂蒙六姐妹也因此成為一種文化象征符號,她們所具有的熱情、堅韌、勇敢使其成為激勵一代又一代國人的精神標桿。沂蒙六姐妹的革命事跡是沂蒙精神形成過程中的標志性歷史事件,這種可給人以感知的具體形式和深入人類精神領域的深層思考作為一種符號,正體現出沂蒙精神美學所具有的“感性—理性”的雙重結構,也使我們從文化符號的角度對沂蒙精神形成的復雜性、豐富性、悲壯性、生命性特征有了一個更加全面和客觀的把握。沂蒙精神從一個側面、一個視角向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傳統文化發展的新方向,使我們得見傳統文化發展的實在內部結構,展示出傳統文化所具有的豐富性和生命性,這也是沂蒙精神在當代人類文化中的現實意義。影片在傳承與弘揚中國革命主旋律的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傳承與發展。
(二)感人情節的真實再現
《沂蒙六姐妹》是一部描寫和謳歌戰爭年代軍民魚水情深、骨肉相連的贊歌,表現出沂蒙山人民無私奉獻、愛黨愛軍的高尚情懷和美好心靈,編劇與導演正是本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思路,才創作出這樣一部無愧于時代的藝術精品。沒有千千萬萬沂蒙女性可歌可泣的奉獻,也就沒有電影《沂蒙六姐妹》的誕生。“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人民生活中本來就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4]在這部電影創作過程中,編劇蘇小衛為了寫好劇本,和導演親自到沂蒙山區體驗生活,在與“沂蒙六姐妹”的原型人物交流過程中,蘇小衛情感受到極大觸動,她說:“這個片子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你編都編不出來。”不僅是導演與編劇,片中的演員在拍戲過程中也是提前到沂蒙山區去親身進行生活體驗,包括攤煎餅、推碾子的細節,都需要用心體驗,只有將細節做到真實,才能獲取觀眾的認可,只有熟悉沂蒙六姐妹生活的真實環境,才能將人物形象完美地塑造出來。這種真實性不僅包含場景細節的真實,同時也包含對人性表現的真實,《沂蒙六姐妹》這部電影之所以感動人心,正是因為影片中對人性真實深刻的表現,影片沒有將人物塑造成全無自我的革命機器,更彰顯出編導對生活與人性的準確拿捏。
四、結 語
《沂蒙六姐妹》向觀眾展示出一幅感情細膩、情感逼真的革命歷史畫卷,讓我們深切體會到革命戰爭年代人們生活的不幸,同時又體驗到革命戰爭年代人們關系的淳樸與自然,影片彰顯的人性、愛情、友情與革命熱情深深感動著祖國的年輕一代。《沂蒙六姐妹》在新舊文化的沖突中表現出沂蒙普通女性的革命情懷,特殊的戰爭敘事方式呈現出獨特的沂蒙精神美學,塑造出血肉飽滿的革命女性形象。影片選擇的女性視角為沂蒙精神的表現與傳承打開了嶄新的視角,為其他藝術形式的沂蒙精神表現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藍本,更加深了對革命文化的深刻體驗。以月芬為代表的沂蒙紅嫂由此也成為千千萬萬個為革命、為國家無私奉獻青春的美麗化身,正是由于沂蒙山區有千千萬萬個這樣的紅嫂存在,才支撐起中國革命的勝利。影片以獨特的美學表現向觀眾講述了中國精神、中國文化、中國故事,是沂蒙精神穿越時代的光影重現,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