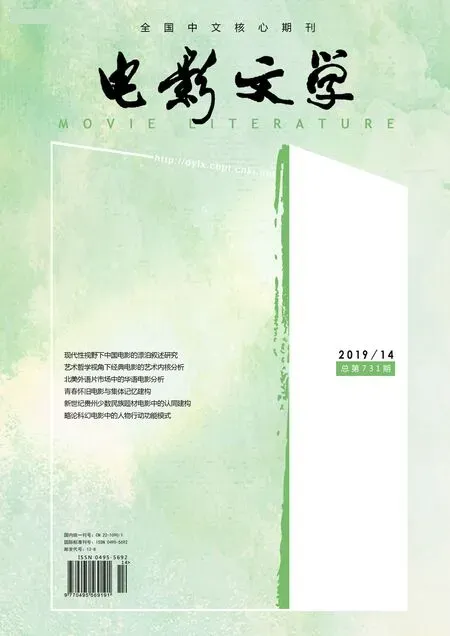電影《重返無人區》的主體精神建構分析
王 銳(吉林廣播電視大學 社會工作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2)
新時期以來,隨著國產電影藝術逐步向更高水平邁進,紀錄片電影也迅速發展,并在近年形成了一個發展高峰。作為一種紀實藝術類型,紀錄片電影以其現實主義的突出特色吸引了眾多觀眾。西藏,因其雄偉壯觀、神奇瑰麗的自然風光、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神秘的宗教文化,成為國產電影中一個熱門敘事背景、一種敘事常態。從宗教傳奇、雪域冰川,到純粹生命、身份秘境,越來越多的西藏自然和文化元素被發掘。第六代導演張揚的作品《皮繩上的魂》和《岡仁波齊》,便是以西藏為敘事背景,將鏡頭對準那些朝圣路上的虔誠教徒和向死而生的藏族人民。而《七十七天》和《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以下簡稱《重返無人區》)等則將鏡頭對準雪域高原一個神秘的區域:藏北羌塘無人區,透過這片廣袤無垠的荒原,表達了對自我的追尋與認同。其中紀實探險類電影《重返無人區》由95后導演饒子君執導,上映于2018年8月31日,獲得了第八屆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新人獎”。影片以生命禁區——羌塘無人區氣勢恢宏、美麗壯闊的自然風光為敘述背景,講述了一群懷揣夢想、充滿激情與勇氣的年輕人,在藏北無人區探索普若崗日冰原的故事,在艱苦卓絕的找尋之路上,建構了主體對文明的反思、對信仰的堅定以及夢想的追尋等精神內涵。
一、尋找生命樣態與反思現代文明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國產電影整體格局中,對鄉土中國的電影敘事與想象一直占據顯著的位置,而對鄉土中國生命樣態的持續興趣與強烈關注則構成了近40年來中國電影最主要、最深刻的敘事主題。對生命樣態的持續探掘,使得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的洪流中,更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價值。探險紀錄片電影《重返無人區》以被稱為人類生命禁區的藏北秘嶺——羌塘無人區為主要背景,這片平均海拔高于5000米的高寒土地自然條件惡劣,方圓百里荒無人煙。由于其遠離人類現代文明,較為完整保留了大自然的原生態面貌,顯示出壯麗的原始洪荒之感,成為海內外探險旅行家們魂牽夢縈的天堂。在敘事視角上,影片從“人類”與“動物”兩個維度呈現了這片荒原上自然生命的兩種不同樣態,展示羌塘無人區里生命原始的洪荒、綺麗、新穎而富有生命活力的自然生存方式。
相對于人類的現代文明,羌塘是一個古老、原始、純粹的天堂,是藏牦牛、藏羚羊、高原狼的故鄉。這里發現了5萬年前石器時代的痕跡,是人類原始文明的起源,而今已退化成了一個氣候多變、風雪肆虐、人跡罕至的荒原。現代紀錄片電影的文化懷鄉,集中呈現為對現代文明的異己感和對故鄉的情感回歸。守望人類的起源,把情感系于故土的童年時代,沉浸于對鄉土的追憶與懷戀,是現代人鄉土情感的主要表達方式。影片在建構主體“懷鄉”情感時,通過透視羌塘這片“生命”世界的生命樣態,表達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影片中羌塘這片“化外之地”的壯闊秀美、古樸奇幻,構成了一幅幅風景畫,不能不使觀眾為之驚異。導演和制片人以對生命極度關心的眼光,以人類的童心和現代人的眼光悠然神往地洞視著人類的童年之所——羌塘無人區的普若崗日冰原。影片的鏡頭多對準羌塘遠離現代都市文明的生命樣態:一頭落單的野牦牛在與攝制組車隊相遇時,既表現出巨大的蠻力和原始的野性,又以“擦肩而過”的驚險舉動向人類發起攻擊;圍繞攝制組逡巡的野狼,表現出掠食者的兇猛和土著的姿態,也以就地翻滾的姿態向人類表示出友好的態度;藏羚羊成群結隊,泰然自若地從保護區邊緣的公路兩旁走過;普若崗日冰原這一獨特的地域環境,因帶有濃郁的遠古時代遺風,更襯托著藏北自然環境的壯闊與美麗:粗糲的大自然,萬類蕭條的冰原,天空里暗壓的烏云,隨時呼嘯而至的寒風。凡此種種,影片以最大的藝術創造力,在無人區里各種生命樣態與人類所代表的現代文明的交鋒中,不斷發掘和表現人性的弱點以及克服與戰勝的過程。如制片人老蔡在面對司機關師傅由于急性肺水腫該如何下撤、何時下撤等問題時,選擇從團隊整體出發,冒險堅持到第二天天亮下撤,以避免夜間下撤在過東溫河過程中可能給團隊整體帶來的風險。此外,團隊中巴桑等人以生命為賭注,驅車為團隊探冰的忘我奉獻精神,更彰顯出人性中的勇敢、善良和愛。在緊張的冒險情節后,影片輔之以熱血澎湃的旁白:“我們都曾在年少時扮演騎士,但如今卻嘲笑英雄,在神話湮滅的時代里,唯有一顆伸展不熄的心,才能給平凡以偉大的勇氣。”以此為影片增加了更加濃郁飽滿、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提升了電影的“生命”價值內涵。
二、探尋生命意義與堅定信仰
馬爾庫塞說:“人的歷史就是被人壓抑的歷史。文化不僅壓抑了人的社會生存,還壓抑了人的本能結構。但這樣的壓抑恰恰是進步的前提。”[1]西藏的靈性和精神的磨礪,安頓了現代人的靈魂。在當代國產影視劇中的西藏,個體的生命在信仰中受到規訓,在神靈的庇護下可以篤定生活。在《重返無人區》中,藏北密嶺——羌塘無人區便是這樣一個遙遠寧靜、自然原始,有著至誠至純情感,承載著神秘虔誠信仰,富有生命精神的所在。影片中一群懷揣夢想的電影人,試圖回到人類的原初,以期為現代人的精神探尋一個安頓之處、棲息之所。普若崗日冰川,便是建構這樣的西藏想象的理想圣地。對普若崗日冰川的想象和探尋,就是影片為現代人面對現代化的精神焦慮而探索的一條化解路徑。
《重返無人區》的生命意義探尋和精神信仰,采用神秘化敘事和冒險情景營構兩條線索并進,創造了原始冰原與現代生活兩個世界,藝術地建構了羌塘無人區的真實世界,以此來解構現代社會的精神焦慮,推崇人性的正向力量和原始純粹的西藏精神。從對現代文明的否定,投入到對西藏的想象和精神信仰。影片中,老蔡所帶領的攝制團隊苦苦追尋普若崗日冰原主峰的過程,近似于虔誠的宗教信徒的朝圣之旅:至純至誠、信念堅定、不棄不餒、勇敢執著。歷經種種艱難險阻后,當第14天團隊一行終于抵達世界上最大的中低緯度冰原——普若崗日冰原主峰群后,制片人老蔡虔誠地匍匐在冰川最高的峰群底下,以一種“他者”視角,對著人類歷史滄海桑田所凝聚而成的一塊塊冰層進行膜拜和審視。情感的至誠至純、生命的堅貞執著、信仰的神性虔誠在羌塘無人區的秘境、絕境與心靈之旅相互疊加中,完成了影片關于西藏的“想象”。
三、追尋冒險和征服的夢想
沈從文認為:“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2]藝術的本質在于延長生命,生命青春、向上理想、追求完美生活的努力都值得頌歌、鼓舞。追求冒險和征服,是人類對健康生命個體或群體生存方式的探索,是反映生命發展、變化、矛盾和毀滅的形態。冒險紀錄片將人類的這種夢想和愿望以藝術化的方式表達出來,產生了砥礪人心的磅礴情感力量。
電影《重返無人區》中,子君以探秘藏北秘嶺的特殊方式來紀念父親饒劍峰,以此接近和理解作為登山者的父親:“我從來沒有機會了解過真真正正在高海拔上攀登的他是怎樣的。”父親的登山夢始于西藏,子君冒著生命危險重返西藏,勇闖藏北無人區,既是為“抵達父親曾路過的高度,接近并理解父親”,也是為回到夢開始的地方,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