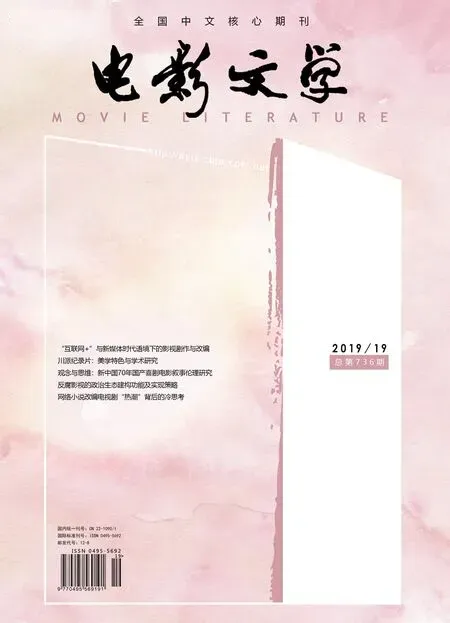小說與電影的關系及對改編的啟示
侯夏雯
(長安大學,陜西 西安 710064)
電影是一門年輕的藝術,相較于其他的藝術形式而言,百年的發展歷程不過是彈指一揮間。它不僅是技術或是藝術形式,更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和文學特別是小說的關系十分密切,電影在中國扎根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向文學獲取資源,還借鑒了眾多文學創作中寫作手法和敘事技巧。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更愿意輕松地隨時隨地觀影而不是守著青燈爬梳文章,文字閱讀的日益邊緣化使得傳統小說越發無人問津。人們更愿意通過銀幕甚至屏幕來“閱讀”一本小說。然而,如今的電影改編更加注重視覺感官,商業色彩極其濃厚,充斥我們眼球的各種大片更是毫無“藝術”氣息,純粹為了感官刺激和娛樂。新世紀以來粗制濫造的改編作品及其對電影造成的不良影響,讓我們不禁擔憂電影的未來。
一、改編:小說與電影的互動
電影對小說的改編是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借鑒最明顯的例證,二者的多重關系通過這種互動也能夠簡明清晰地展露出來。改編可以視為對小說文字世界的影像化調度。怎樣才是好的改編?這就需要我們探討小說和電影藝術的本體屬性,即作為語言媒介的文字與影像。小說與電影都在敘事中建構時空,在文學作品中,空間始終存在于概念中,而讀者對于時間的延續感則非常強烈,因為小說的構架、情節的發展和人物的變化都取決于時間而不是空間,并且,隨著小說敘述的延續,也在建構著時間。時間在電影中也有同樣的決定作用,但是時間的延續要借助空間現實的延續才能實現。小說中的時間是用語言文字建構的,而電影的時間是用事實建構的。小說喚出一個世界,而電影直接展現出它按照一定規則安排組織好的世界。電影中構成的時空連續體與現實的時空連續體類似,都是一個整體。電影讓我們感知到一個隨著時間變化的世界,過去消逝不見,未來尚未存在。在電影中,一切就如同現實生活,只屬于現在時,在不斷地變化,我們實際感知到的只有空間,不斷移動變化的空間。小說營造的世界始終屬于過去,對于讀者來說,它是已經成形的實體。這種客觀化會造成一種時間的差距,讓讀者感到一段實際延續的時間;而在電影中,觀眾始終與主人公一起行動,其心理時間永遠是當下。
其次,我們需要明確二者各自的特征屬性以及二者的巨大差異。電影首先是一種表現手段,然后才是一門藝術。或可能是一門藝術,我們可以界定電影是一種像文學一樣的審美形式,它用畫面作為表現手段,而畫面的序列就是語言。活動畫面可以比作語匯,電影藝術可以比作文學,電影現象可以比作印刷術。那么,電影同時也是一種復制和傳播的手段。“電影與印刷術一樣是大量復制和傳播精神產品的工具。它對人類的影響不亞于印刷術。”[1]電影早已成為與文學、繪畫、雕刻等并駕齊驅的第七種藝術,然而電影沒有失去它的通俗性,一部電影的最終完成需要導演、編劇、攝影、演員、美工、音樂、剪輯等工作人員參與,是一項集體藝術;并且,所有的電影工作者,都具有能動性,都會對電影形成一種潛在的“影響”。電影類似人類的夢境,它將深潛于人們意識中的欲望和意念以視覺的形式外化,從而將人們腦中無形的思想固化為一種特殊的感知方式——視覺影像。
真正的電影藝術家往往能夠突破常規,自由地控制時間與空間,對電影時空實現超越性的闡釋和拓展。康德將時間和空間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形式,時間觀念的轉變必然會帶來一種全新的“看世界”的方法。時間和空間是整理感性經驗的先驗的“感性直觀形式”。小說與電影在描繪這個世界的時候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享有極大的自由(小說比電影更自由),具有傳統舞臺所不具備的靈活的流動性。它們都有極大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題材。小說和電影都能夠在接受者心中創造出一種幻覺,這種幻覺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形,但它們卻沒有消解時間和空間。電影既是一種最機械化的藝術,又是一種在時間空間上最自由的藝術。機械與想象彼此滲透,互為條件。
二、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批評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而言,電影對小說的改編可以被視為一種文學的批評活動,將抽象文字組成的小說改編成為視覺畫面組成的電影,就是對文學文本的一種闡釋,對原小說文字的解碼過程就是闡釋文本的過程。然而圖像解讀與文本閱讀是大不相同的,圖像對文字的改編將抽象的意義和畫面具象地用電影影像展現出來。改編是一個通過媒介重新分配的過程,在改編時閱讀就在悄悄地進行,不論改編的社會歷史背景如何,電影的風格會在某種程度上與原作保持一致。從電影中視聽畫面的編排到內部的表意機制,都建立在閱讀作品的內在本質上,改編后的作品會讓原小說與影片有一種內在的契合。這種契合決定了許多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電影其實是一種對歷史背景的回歸,在由文字媒介向圖像媒介轉換的過程中回歸到了原作所處的歷史背景、社會背景以及意識形態中。
其次,在將文字符碼轉換為視聽符碼的過程中又會不可避免地代入創作者的主觀性和創造性。創作者在改寫劇本、拍攝影片甚至后期剪輯制作的過程中對原著進行的選擇、增刪、替換甚至“變異”,都是一種完整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從文學作品到電影的改編不局限于對原文故事的忠誠度,也不是對原文內容的簡單重復,改編本身就是一次再創作活動。在此意義上,影片的創作者在改編的過程中,也是在對原小說文本進行批評。電影的創作者既是小說的闡釋者也是批評者。即使改編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是對原作的一種重復,也是在表達一種認同和解釋,即認同作者的觀念,并將之用不同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進一步闡釋原著的內容。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在這種批評(改編)中往往會超越原作者所表達的意義內涵。
在這種“改編式閱讀”的過程中,往往只有部分內容會吸引改編者的注意和興趣,經過讀解的小說會帶上個人色彩,改編的影片會加入導演的個人理解,強化某些特殊的興趣點。最后,往往這些“偏好”和“興趣點”會成為影片獨具的魅力。在改編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內在的符號轉換。導演會從自己的生活經驗、感受出發,結合電影藝術自身的特性,對小說原著的題材進行再選擇、再提煉,融入自己熟悉并且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素材,以此來展現對于生活獨特而深刻的見解,加入豐富的社會歷史內涵,從而在一定意義上深化影片的主題。如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蘇童的中篇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編劇倪震在改編原作時將故事的發生背景定在南方,而導演在創作時直接將敘事的背景放到了北方農村。北方雖然沒有南方的細膩和滋潤,卻自有一番別樣的渾厚和凝重。
創作者還會依照自我的生命體驗、人格理想以及對社會的思考,改變人物的人生經歷和性格特點,使得影片的表達更符合主題。或是強化原著主人公性格的某一方面,或是為其性格注入新的元素,讓電影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圓潤,更富有動作性和感染力,更加貼切地表達影片的主題。例如在《紅高粱》中,主角余占鰲的身份和人生經歷由一個土匪司令變為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如此一來,在影片結尾的高潮段落中,這些生長于高粱地的漢子為了保護故土,拿著原始的農具殺日本人,打汽車,便有了一種敢愛敢恨、舍生忘死的熱烈奔放的情感蘊藏在其中,突出了影片對純潔、坦蕩的生命的禮贊的主題,也體現了導演的人格理想和美學追求。
好的電影改編會讓原著“脫胎換骨”,并賦予其新的形式和意義,這是一種創新而非照搬。電影的敘事結構是不能用同樣的小說結構表現出來的。創作者應當依據電影藝術的敘事規律,并且與受眾的審美選擇以及心理需求相結合,創造出合適的敘事順序,并利用獨特的敘事技巧讓影片的敘事節奏更加自然流暢、舒緩有致。讓敘述的故事清楚明了、生動形象,受眾也會更容易認同和接受。在電影語言中,畫面通過其象征性、邏輯性和潛在的符號屬性而兼具話語和詞匯的作用。借助這門語言,就不再需要通過約定程度不同的抽象符號,而是利用“具體現實的復現”[2],去獲取小說中各種現象的對等物。電影的攝影藝術,是一種將文字語言轉換為影像語言的藝術。創作一部影片,就是要重新建立起一套與原劇本提供的文學故事相對應的視覺語言代碼。當然,這種對應不是全然地照搬,它需要一次恰到好處的從語言文字的表意到影像的表意的“轉化”。影片的邏輯推演和主要含義是以影像的展現為基礎,而不是以語言的連貫為基礎。
電影中的視覺形象有其造型規律,導演從電影語言的特殊表現方式及自我的美學追求出發,選擇、改動甚至強化某一具象的元素,為影片營造出獨特的表意氛圍。建立起隱喻等象征機制,寓以其豐富的內涵意蘊,使影片的風格鮮明獨特。如《菊豆》對小說《伏羲伏羲》的改編,以染坊代替了原故事的空間環境。在這正正方方的囚牢一般的天井四合院中,五彩的染布透露出鮮活的生命活力,而大紅色的染布、血紅的染池則更加將這種生命的激情和熾烈的情欲發揮到極致,整個染坊象征著多彩的社會,在這里的生死輪回無疑影射著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巨大寓言。在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導演創造了隱喻家族僵化繩規的大紅燈籠的視覺形象,并且強化了這一視覺象征的含義,女人們的生死以及悲歡離合都寄寓在這個紅燈籠的亮與滅上。而在張藝謀的另一部影片《秋菊打官司》中,導演又著重強化了烘托紀實氛圍的紅彤彤的辣椒的形象。導演張藝謀運用這些具象化的視覺元素,不僅加強了中國民族的獨特韻味,而且這種獨到的運用方式也符合中國的傳統美學和民族的審美習慣,能夠完美地展現民族生活樣貌、民族心理以及民族風俗習慣。從《菊豆》中以紅色為主調的染坊,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紅燈籠,再到《秋菊打官司》中紅彤彤的辣椒,均賦有這個以紅色為主色調的民族的獨特個性和風味。
電影作為一門藝術不應僅簡單地記錄含義,而應創造自己特有的含義。電影語言本質上屬于審美創造。這不是一種推論式的語言,而是一種經過加工的語言。它的抒情性多于理念性。電影在改編的過程中可以創造出超越文字文本的視覺影像,建構新的視覺符號,深化表意機制。電影改編是針對小說文本的一種敏銳的、批判性的回應。
三、傳播:電影媒介溝通世界
在中國,電影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和再現,對小說的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以謝晉為代表的“第三代”導演及“第四代”導演將文學作品搬上銀幕,使得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不僅能夠體驗到視覺的愉悅,也能夠受到一定的文學熏染,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他們對于文學的了解。當一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之后,文字語言就被轉譯為了影像的語言,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改編相當于促進了文學原著在國內的第二次傳播,也促進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搭上了電影媒介這趟快車,小說的接受群體會變得龐大起來,甚至一些經典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在電影的改編下重新走入人們的視野,煥發出新的生機。如錢鐘書先生的小說《圍城》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出版,但是熟知這本小說的讀者卻寥寥無幾,小說的影響力僅限于學術范圍之內。直到20世紀80年代,《圍城》被“第四代”電影導演黃蜀芹改編為電視劇,才讓大家知道了這部經典的小說,電視劇的熱映在當時引起了一時轟動,原著小說的讀者也急劇增加。影視媒介的傳播效果成就了這部膾炙人口的經典名著。
20世紀80年代以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海上花》《色,戒》等小說被搬上銀幕,掀起了“張愛玲熱”,電影的魅力讓小說原著再次煥發青春,吸引了更多的讀者返回去重新閱讀小說原著。1988年是名副其實的“王朔電影年”,其四部小說(《橡皮人》《浮出海面》《頑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同時被改編為電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出現了“王朔熱”,其小說銷量大增。作家池莉也憑借自己的幾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而使得自己的作品大賣,江蘇文藝出版社更是出版了洋洋灑灑的六大冊《池莉文集》,長銷不衰。“池莉熱”已經成為新時期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風景線。
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影片在國際上頻頻獲獎,也從側面說明了改編電影在逐漸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國際認同和接受。“第五代”導演的發軔之作《一個和八個》(1983,張軍釗)根據郭小川的同名敘事詩改編而成。張藝謀在這一階段的全部作品也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尤其是當代文學的中篇小說。其作品也是“第五代”導演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其獨立指導的處女作《紅高粱》(1987,根據莫言同名中篇小說改編)一舉奪得第三十八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不得不說,這對于莫言日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功不可沒。
四、接受:電影改編影響審美選擇
反過來,小說也受到電影改編的影響。一部小說與一部電影一樣,唯有被“看”,其意義才是完整的。如果僅僅是印刷鉛字的組合或是感光膠片上的固態圖像,那它們就毫無價值。電影從創作的初期開始到最后的完成會被“看”兩次:第一次是編劇、導演、攝影師、演員及其他工作人員,第二次是每一位觀眾。電影對小說的改編是建立在閱讀原小說的基礎之上的。
觀眾不僅是被動的接受者,同時還是隱性的“創作者”。導演在創作一部影片的時候,就已經在面對廣大的潛在受眾,電影的創作不僅是一種個人化的表達,它多多少少都會受到社會、觀眾甚至影評界、學術界反饋的影響。一部拍攝完成的影片,只是作為第一文本的樣片,觀眾的觀影過程及之后引起的反響和討論才會形成影片的第二文本。第二文本是對電影作品的一種補充和完善。從這個角度而言,電影的創作是受到電影接受的制約的。正如著名法國電影導演路·達更所說,在影片中,“一個畫面的含義,或更確切地說,對它的解釋是取決于看到它的人的感情,取決于這種感情是否豐富,取決于他的教育和文化素養的”[3]。
人們在接受電影文本的過程中,最先理解的都是先在的經驗結構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和理解內容。這些內容也是最易于產生普遍接受效應的,具有大量重復信息以及按照常規編碼的作品往往最容易被人們接受。所以受眾的各種先在的歷史環境、文化閱歷、人生經驗會直接影響到他們對電影文本的接受效果。同時,人們所期待的電影文本,也是與他們的意識及潛意識是分不開的,不同的人生經歷、文化視野會讓人們期待在文本中得到不同的滿足和體驗。在此意義上,觀眾的期待視野是基于每個人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經驗結構的選擇結果之上的。在幾乎所有的主流商業電影中,敘事文本的含義與觀眾的期待視野是同形同構的。顯然,以大眾趣味作為藝術評判的審美標準是不恰當的,大眾趣味只能作為一種對藝術作品的特定反映,作為一個重要的依據,幫助我們確定藝術作品的心理價值。
隨著我國社會文化分裂為大眾文化、精英文化與主流意識文化多元并存的態勢,精英文化受到了大眾文化與主流意識文化的雙重漠視,現代性的精英文化呈現出邊緣化的趨向,精英文學的地位一落千丈。迫于生存的壓力,作家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而留在文壇,向電影改編靠攏,不失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生存策略。于是,那些曾經叱咤文壇的一線知名作家,如今紛紛“轉行”做起了電影編劇。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王朔的作品紛紛被改編為電影,并且引發了“王朔熱”,王朔以對影視文化徹底迎合者的形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其四部小說(《橡皮人》《浮出海面》《頑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98年同時被改編為電影,這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988年也由此被稱為“王朔電影年”。隨著阿城、蘇童、李碧華、馮驥才、余華、張賢亮、池莉、王安憶等作家的作品紛紛被搬上銀幕,小說的接受由個體化的閱讀走向了電影化的集體觀賞。小說坐上電影改編這趟快車增加了廣泛的受眾,電影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力量讓許多作家一夜成名,走紅后的作家可以不再整日苦守青燈,與紙為伴,而是到處簽售自己的小說作品,名利雙收。這種經濟利益的驅動,讓許多作家在初嘗甜頭之后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更加迫切地想要與電影聯姻,加入電影創作的隊伍。
誠然,如前文所議,許多文學作品借助電影媒介的強大力量獲得了廣泛的讀者,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春,某些作家也因為電影的傳播影響力而一躍登上國際的舞臺。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將小說改編為電影僅僅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去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因為一部成熟的小說被改編為電影之后也會為作家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可以獲得幾倍甚至幾十倍的稿酬。但是小說的創作卻出現了“去歷史”“去深度”“去現實”的價值傾向,在寫作技巧上,也舍棄了語言文字的理性邏輯,放棄了文學的深度和思考價值,只注重故事場景和對話。這無疑對文學有消極的影響。
進而言之,小說電影改編的熱潮并不能作為評價電影本身好壞的標準。電影藝術的評價標準,必須來自作品內部,作品內在的審美特征。外在的接受群體,如編劇、導演、觀眾等,都必須先通過對電影文本的具體分析之后才能有所定論,依據大眾趣味的選擇標準永遠不能直接成為衡量評判電影價值的審美標準。如果一個導演不分青紅皂白地取悅觀眾,迎合他們的口味,那就表明導演受到了利益的驅動。這種利益驅動可以來自對功名的渴望,也可以來自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或者意味著導演根本就不尊重觀眾和閱讀者,因為他沒有向受眾提供富有啟發性的藝術作品來訓練他們。如果無法提高觀眾的鑒賞能力,以給創作者鞭策和批評,那么電影藝術與文學將永遠停留在最原始的消費階段。
五、結 語
在改編小說的過程中,需要創作者重新思考它的題材,或是直接賦予原作另一種發展脈絡和完全不同的意義,創作者從他人的作品出發,獲得靈感,再創造出一部屬于自己的個性化作品。電影附加在原文之上,營造環境和氛圍,說明原文,延伸原文,用視覺形象去表意。電影如果能夠形神兼備地再現原著的精髓,就能夠深化自身的理性表達方式,將小說與戲劇中的原始素材更好地與自身的美學結構相結合。
除了創新現有的視聽語言技術,還應當在小說與電影文本中同時建構起理性主義的規約以及人文精神的維度。視聽語言手段的創新體現在深刻的表意機制和新穎的敘事技巧等方面,電影可以充分地學習并借鑒小說中的敘事手段和技巧。而人文精神的建構則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建立小說與電影中的人文價值體系,小說與電影所體現出的人文思想需要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尊重個人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其次,拓展創作者的人文視野。作家和導演的人文觀點及立場會影響到整部影片的基調,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文視野會從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角度來評價社會與人類活動,表述其人文經驗與感受。再次,創作者的人文經驗、人生閱歷以及個人涵養都需要得到高度的重視,借鑒人類歷史上豐富的藝術經驗和知識儲備,從而挖掘出創作者自身的經驗及閱歷。最后,在電影創作的過程中,創作者需要明確最終的人文目標,或是闡述人文的主題,或是深挖人性的奧秘,或是作為一種豐富人類自我認知的資源累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