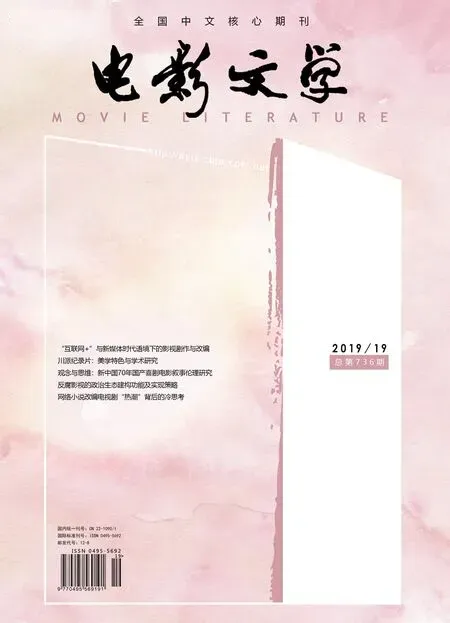《人盡皆知》電影在敘事中“當代性”的缺失
化 冰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電影學院,澳門 999078)
在后現代審美碎片化閱讀的時空下,觀眾更加注重視覺審美的體驗,對于傳統的敘事情節和文本價值多已漠不關心。其敘事的先鋒性走進當代中并沒有獲得當代社會審美敘事的認可,成為現代電影中存在的一部分,而對于觀眾的視知覺體驗并沒有過多關注。在后現代電影中我們對傳統藝術文本進行解構,傳統的敘事情節在特定的社會審美中轉瞬即逝,傳統意義下所產生的審美不能適應當下社會,用當下碎片化閱讀方式的審美去觀看電影,會產生陌生感,與當下的審美產生偏離,這正是當下電影在審美接受中的一個常態。電影《人盡皆知》是著名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作品,這部作品是一部家庭倫理劇,在美學敘事上并沒有宏大敘事,而是從微觀的角度對“人性”探索,在家庭瑣碎的事情中尋找另一種存在意義。但又由于《人盡皆知》的當代文本注入了很多當代元素,加上在異域西班牙的鏡頭拍攝,讓導演的個人敘事化身份去身份化,成為一個異場的介入,讓電影敘事在一個更加客觀的環境下拍攝,這一點讓其更加貼近了現代生活;同時它的缺陷在情節上也很明顯,跳躍式的敘事方式雖然增加了觀眾在視覺方式上的震撼,但是讓融入中的敘事線索在影片中埋下了很多隱患,人們不會從中獲取反思,而是留下了更多的疑問和不解。在這種含混的敘事情節中,討論它的“當代性”意義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情節敘事的碎片化
電影《人盡皆知》的敘事情節主要圍繞著三個主人公展開:勞拉、帕科與亞歷桑德羅。勞拉是西班牙人,她出生在一個莊園地主家庭里,從小快樂地生活著一直到成年,在此期間,她與其青梅竹馬的戀人帕科深深相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沒有真正地走在一起。勞拉輾轉幾年,最終與遠在阿根廷的亞歷桑德羅相守,成為他的妻子。此時亞歷桑德羅經營著一家很大的公司,勞拉的生活非常好,并且生下了一兒一女。從地域上看這三位主人公相距甚遠,沒有任何交集,但敘事的第一個矛盾點就是勞拉的妹妹要舉辦婚禮,帕科也應邀來此。多年的戀人再次相遇心情復雜,他們并沒有來得及詢問對方的生活與經歷,馬上產生了第二個轉折點,勞拉的女兒被綁架的消息傳來,這為故事的敘事埋藏了第一個情節。本來勞拉帶著一雙兒女回到故鄉,生活依然很平靜,自己妹妹的婚禮舉辦得非常成功,整個宴會的賓客載歌載舞,將整個婚禮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在這一片祥和的氛圍中突然劇情大反轉,雖然可以在視覺審美中帶來沖擊,引起一種快感,相比紀錄片的平白直敘增加了劇情的復雜性,但是這種劇情的安排并沒有逃脫肥皂劇的陰影。我們仔細回顧情節,另一位主人公帕科現在已經是一個莊園主,他留有絡腮胡子,體形壯碩,看上去是一位很開朗的紳士,耳朵上戴有一只海盜耳環,從衣著上可以看出他不在意一些生活的細節,是一個大度的人,但是為什么在破舊的小教堂角落刻有他們二人字母縮寫,并且能夠一直保存到現在呢?這顯然與周圍的環境是不相符的,周圍的環境很破敗,而字母縮寫LP卻仍然能夠保留在教堂的建筑上,是為了表示勞拉與帕科之間的愛情特別純真嗎?是什么原因讓他不能夠跨越二人之間的界限呢?
在教堂里出現顯然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事實,這種濃厚的婚禮氣氛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審判,而這種審判是公開化的,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事情。這對勞拉無疑是最痛苦的打擊,她并沒有從內心里真正放下對帕科的感情,但她已經是兩位孩子的媽媽,她急于逃離這種場景,卻不想上樓之后沒有看到自己的女兒,正在她忐忑不安時收到了女兒被綁架的消息,讓她從重見舊愛的焦慮中直接進入到家庭的悲傷痛苦之中,這實質上是一個情感的轉折點。但讓她更加絕望的是周圍的村民并沒有幫助他們尋找女兒,而是在不斷討論身邊的人誰能夠交付得起贖金問題,勞拉在這個時候大哭,勞拉的形象詮釋得確實淋漓盡致,這是本劇比較成功的一點,導演并沒有安排綁匪說不交贖金就撕票的環節,沒有將其上升到懸疑的劇本當中,而是將其停留在家庭倫理層面上。根據后面的劇情可以看出,在勞拉身邊能夠有能力支付這筆贖金的只有她的初戀男友帕科,而她對丈夫的公司破產卻一無所知,帕科表示可以出賣自己的莊園來贖回勞拉的女兒,周圍的村民猜測這筆費用誰是最需要的當然勞拉并沒有直接猜忌自己的丈夫,當女兒被贖回的時候沒有追究到底是誰綁架了女兒,反而是基本恢復到了之前的生活狀態,但似乎勞拉與自己的丈夫之間的感情變了,從信任變成猜忌,這在生活中似乎就是常態。在《人盡皆知》影片中,故事的情節這樣跳躍式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調動觀眾的激情,在視覺化上形成震撼。與此同時,導演并沒有對這其中的伏筆做出過多解釋,而是將整個情節的重點集中在倫理關系和人性的探討當中。勞拉女兒的親身父親是帕科,這是一件人盡皆知的事情,包括勞拉的丈夫也知道此事,但并沒有對此事進行追究,而是選擇了默認。帕科在營救的同時也可能是有私心的,這種救贖是出于自己的女兒,如果換作是別人,帕科并不一定進行營救,與周圍的村民是沒有什么區別的。同樣,女兒被救出來之后勞拉并沒有對帕科進行感謝,而是選擇與丈夫一起離開,這種默認的離開也是對這種荒誕人生經歷的宣戰。原本的和諧家庭不復存在,家庭里塵封已久的秘密逐漸浮出水面,大家都被瑣碎的事情將自我劣面展現出來,這種審美情節的安排實質上是對當代家庭生活的反思。帕科雖然外表熱情洋溢,富有愛心,但是他救勞拉的女兒是因為他是孩子的父親;勞拉丈夫亞歷桑德羅雖然曾經事業不錯,但是破產后他設計綁架勞拉的女兒,而不是兒子。雖然這一點在影片當中并沒有明確指出,但是根據情節的安排,亞歷桑德羅的嫌疑無疑是最大的,并且導演在其他情節有暗示,如當地居民對綁匪的討論,綁匪沒有提出撕票等都是暗示。這種敘事具有極強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情節界定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在情節的敘事中這種模糊的真實性是后現代美學的典型特點。在文本的敘事中是對所追求的傳統美學的確定,在當代性語境中,傳統文本話語權的失語逐漸被消解和打破,在情節的敘事中就體現出碎片化。同時這種碎片化的審美是當今觀眾對影像關注的主要方式,在《人盡皆知》電影中這種敘事性的碎片化更為明顯。
二、敘事的當代性缺失
從傳統的倫理泡沫劇到《人盡皆知》這部影片的轉向,就情節的主題而言,都闡述的是家庭倫理的瑣碎事宜,在愛恨情仇之中逐漸尋找自己的人生軌跡,這在現代社會來看不是個例,而是我們在社會中的一種關系體現。在情節的表達上與傳統的泡沫劇有較大差異,傳統泡沫劇在敘事手法上往往注重故事情節之間的邏輯性,整部影片從敘事的開啟到結束都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雖然有時會加入一點伏筆在里面,但隨著敘事的解鎖,伏筆都會成為敘事的鋪墊。而《人盡皆知》在敘事手法上與之前有很大不同,在后現代美學審美介入下,導演大量使用伏筆和暗示的手法,讓整個故事的情節成為一種插敘插議的形態,在敘事的過程中形成空間的共存,讓《人盡皆知》在影片中具有極強的跳躍性。而這種抽象的敘事邏輯必然會導致空間思維的邏輯性淡化,讓它按照自我內心情感的需要去發揮。這在有些劇情當中表現為話外語,主要介入的手段如做夢、自言自語等,成為一種自我精神的發泄,這是人在內心情感上對外界的失語。而后現代文本的敘事方式又是反理性的,強調人的內心主觀情感的表達,在整個故事當中并不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也沒有一個核心的主人公,是去中心化的,敘事中不會形成虛擬化的英雄主義,當然宏大敘事的方式在影片中也很少見。
勞拉這一人物形象的設置在情感基調上注定是被犧牲的。其小時候的幸福生活到成年后失去的戀人以及后來與丈夫、孩子發生的倫理事情,不去評判她在道德上的問題,就專從敘事情節安置上看,就是去當代性的。在文本的安排中兩個完全再沒有交集的主人公通過一場婚禮產生了交集,就顯得很有巧妙性。首先就觀眾看來,勞拉妹妹的婚禮雖然表面上熱情洋溢,但實質上是暗藏冷漠與禍端的。帕科與勞拉本就是青梅竹馬的戀人,這一點鄉村破舊的教堂就可以證明,多年之后這種情感依然存在,這也是眾人皆知的事情,這需要一個引子來點燃他們之間的故事,妹妹的婚禮就是一個引子。其次就婚禮本身來說,也是勞拉與帕科之間愛情的見證,他們青梅竹馬,也有自己的女兒(女兒不是勞拉與她丈夫生的),他們就差一個婚禮的見證,地點恰好就在教堂,因此有理由認定為婚禮實質上是為他們準備的,是女兒被綁架的伏筆和整個情節的矛盾點。之后勞拉在女兒救贖之后與丈夫一起黯然離開,我們似乎認為很不符合敘事邏輯,這就是后現代性美學下的敘事方式。帕科拿出巨資救贖了勞拉的女兒,本應該是一種高尚品質的塑造,是一種英雄人物的譜寫,但是導演通過之前教堂的見證和村民的議論鋪墊出勞拉女兒的父親就是帕科,塑造出親生父親救贖女兒的故事。這種故事在倫理學中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就是去英雄主義。
當女兒被救贖出來之后,勞拉并沒有感謝自己女兒親生父親,同時勞拉的丈夫也并沒有對此追問,而是選擇沉默黯然離開。從觀眾的角度上看這種跳躍式的情節設置很荒謬,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試想一下,勞拉雖然與帕科是青梅竹馬的戀人,但二人之間并沒有得到神父的洗禮,也沒有任何公認,因為各種原因二人沒有在一起,也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勞拉已經懷孕。《人盡皆知》文本也提到勞拉輾轉去了阿根廷,最后與事業正在輝煌時期的亞歷桑德羅結婚,也沒有表明這時的勞拉就已經懷上女兒。而妹妹的一場婚禮卻讓這對曾經的戀人相遇,指認勞拉女兒的父親是帕科,這顯然是不恰當的。跳躍性的敘事硬是以此為線索,這種敘事情節的安排就是后現代審美的虛無性,他們的人物形象塑造彌漫著強烈的虛無性,家庭的信任與關愛變成了猜忌和冷漠。這種消極的現代文本缺少了傳統人物的特點,在急于探索人生發展的路上的彷徨、自卑,喜歡表現人性的自卑與劣勢,反對英雄主義和崇高,而這種反叛的缺失是對當下社會中的陰暗面進行的批判,虛無性的敘事并不能一直成為主體。
三、敘事中“當代性”的重構
在后現代審美文化下,我們應該怎樣從傳統的文本敘事中跳躍出來,讓整個敘事符合“當代性”的審美邏輯。《人盡皆知》影片在敘事性上塑造了很多的宏大敘事,又不動聲色地將那些主人公之間的邏輯變得虛無,在每一段敘事中都能體現出審美的邏輯性,它是一個含混不清的部分。當他們之間的秘密和緋聞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時候,這些已經不再是秘密,而是走向公開場所下的審判。當勞拉與青梅竹馬的男友深戀時,綁匪綁架女兒之后并沒有撕票進行威脅,而勞拉也沒有選擇報警,但是破案顯得毫無頭緒。在這些情景中,我們似乎可以追尋到傳統劇本中的邏輯敘事,有可能清理出一種敘事的邏輯,但是有一種創作手法的介入打破了這種虛擬局面,就是畫外音的介入,它直接讓整個鏡頭轉向情感化的敘事表達,而蘊藏在其中的敘事邏輯就顯得更加虛無縹緲,成為一種模糊不清的審美,需要觀眾從虛無中得到審美的靈感,這樣做的一個優勢是加強其中的哲理性表達。二是需要觀眾根據自己的觀看感受,接受其中的敘事邏輯,特別是在影片的結尾,其敘事的情節引起疑問,它們通過無聲的鏡頭和心理活動將整部影片中真正的兇手暴露無遺。這種安排給人一種強加上的感覺,雖然解釋了文本沒有結局的敘事邏輯,但很難讓人接受。
正是這種反理性的敘事邏輯中,在現實中并不符合觀眾的審美邏輯,我們很難能夠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式進行敘事性的思考,很顯然,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表現方式對傳統文本進行解構。在現代性的語境下,既要對傳統的理性邏輯敘事進行遵循,讓其具有完整的邏輯敘事結構,給觀眾呈現完整的文本故事,同時也要兼顧大數據互聯網影響下的觀眾審美。傳統的文本在敘事情節和拍攝方式上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審美潮流,人們樂于碎片化的審美閱讀,除了典型的鏡頭拍攝技巧之外,應該按照文本的主線與副線進行有計劃的刪減和增補,這樣既可以保證完整的敘事邏輯,又可以符合影片制作的規律,引起觀眾在觀看中的視知覺體驗,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敘事性中“當代性”的重構關鍵點要適合公眾的審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