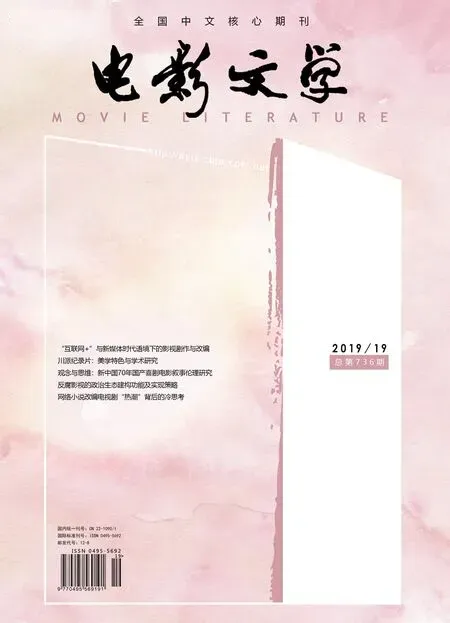《絕殺慕尼黑》的“加蘭津”形象重解
李曉寒
(山西傳媒學院,山西 太原 030013)
《絕殺慕尼黑》是一部傳記類電影,同時也是一部紀錄片,電影由安東·梅格爾季切夫導演。講述的是在1972年慕尼黑世界奧運會籃球比賽中,蘇聯通過自己的努力打敗了蟬聯36年冠軍的美國隊。雖然這一球是險勝,但在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思議的。整個決賽,美國隊一直領先于蘇聯隊,在最后的三秒鐘,蘇聯仍然沒有超越美國,他們似乎看到了最后的勝利,已經開始在慶祝,但是就在最后的三秒鐘,蘇聯隊采用新的戰術,打破了美國隊的封鎖,又進一球,打破了美國不敗的神話。這一切的功勞除了隊員們密切的配合之外,還要仰仗于他們的籃球教練“加蘭津”。“加蘭津”在蘇聯并不知名,自身并沒有受過嚴格的球隊教練訓練,很少為百姓所知,并且當時蘇聯正處于冷戰時期,國家經費匱乏,生活貧困,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加蘭津”能夠帶領這樣的一個球隊,打破了美國長達近四十年的不敗神話,讓比賽的結果發生逆轉,改寫了整個籃球的發展史。近日電影《絕殺慕尼黑》在中國內地上映,在此之前就已經刷新了俄羅斯影票最高紀錄,并且在英美媒體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梅格爾季切夫呈現給觀眾的影片敘事,正是當年最具有爭議的后三秒鐘,在這最后的三秒鐘到底發生了什么,能夠成為雙方一直具有爭議的懸案,《絕殺慕尼黑》影片就是講述1972年比賽的前因后果。“加蘭津”教練剛接任這支年輕的球隊時就宣布要打敗美國隊,這給他們的內心帶來了許多惶恐,國家的榮譽與家庭的父愛的矛盾該如何選擇,原型佛拉基米爾康德拉辛的形象是什么?由此蘇聯核心教練“加蘭津”的人物形象設置具有多重意義。
一、爭議的“三秒鐘”
在整個比賽的最后六分鐘時間,蘇聯隊由于體力直線下降,導致許多球失誤,如葉杰什科在運球中的掉球、扎穆哈梅多夫的發球失利。這給美國隊的反攻帶來了先決條件,事實上美國隊也是這樣做的,在喬伊斯三分線上跳投命中之后,整個比賽的分數已經追到了42∶44,整個比賽已經只剩下最后的三分半,而此時蘇聯隊的體力嚴重下降,盡管蘇聯隊一直還保持在領先的地位,但是在經歷了福布斯的二分中投之后整個比分相差一分。在最后的三十多秒鐘,按照正常的比賽只要拖住這三十多秒就完成了勝利。據考證,蘇聯在之前已經獲得49枚金牌,急需一枚金牌來為50周年慶。此時將球傳到了亞歷山大·別洛夫,讓他進行控球,別洛夫企圖利用自己高大的身體直接進行中投,沒想到被美國隊的麥克米倫封蓋之后,他并沒有選擇就近傳遞,而是選擇了空傳遠方的薩坎杰利澤,又被美國隊員柯林斯截下,可以說在這最后的三秒鐘整個球場是非常激烈的。蘇聯的幾次進攻都被美國隊給攔截下之后,前鋒隊員薩坎杰利澤選擇對正在飛身上籃的科林斯進行犯規,由此雙方的矛盾又平緩下來,比分依然僵持在最后的48∶49,蘇聯隊領先一分,這似乎就可以判斷出勝負了。蘇聯隊員的犯規讓科林斯久久不能從地上站起來,但科林斯經過短暫的治療之后,仍然站在罰球線上進行罰球,幸運的是兩球都命中,美國隊捍衛了自己不敗的神話,是否他們已經真的勝利了,而三秒鐘的爭議就由此而來。
球場的比賽并沒有落下帷幕,蘇聯的助理教練巴什金則提出,之前蘇聯曾經叫了一個暫停并沒有生效,需要主裁判將這個時間算進比賽當中。要知道,在比賽快結束時吹響這樣的請求極有可能判為技術犯規,他要求裁判執行這個暫停的時間再進行發球,整個比賽就剩下最后的三秒鐘。美國教練表示,蘇聯叫暫停的時候科林斯已經開始罰第二個球了,根據當時的籃球比賽規則,當科林斯進行第二次罰球時蘇聯并不能叫暫停,美國隊并不承認蘇聯有這個叫暫停的可能,而蘇聯將其歸類為由于場內的蜂鳴器太響,對方并沒有注意到。我們不禁發問,到底這個三秒鐘的暫停是否真實存在,據當時這場比賽的錄像資料顯示,技術臺的蜂鳴器確實在科林斯第二次罰球的時候響過,說明蘇聯的暫停請求技術臺確實收到過,但根據比賽的規則第二次罰球是不能暫停的,蘇聯的這個請求被判定無效。但故事的矛盾點并沒有結束,而是進一步升華,如果判定這個暫停有效,那么科林斯的罰球就無效,需要重新進行罰球,再次罰球并不能保證都會順利進球,顯然美國教練并不會允許這么做,因此,雙方的爭議進入到白熱化。裁判方雖然沒有判定蘇聯的暫停無效,但蘇聯由此獲得了重新發球的機會,時間為三秒鐘。蘇聯教練“加蘭津”乘著這個有效的時間重新布置了戰術,并且很巧妙地換了人,蘇聯隊從底線發球,球員保羅斯卡斯拿到球之后,剛準備拋球上傳時,終場比賽的哨聲吹響了,氣得保羅斯卡斯直接將球拋到籃板上,這在今天看來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場內所有的人都覺得美國隊已經勝出了,整個比賽已經落下帷幕。但是蘇聯又提出了第二次發球,理由是當時的比賽沒有停留在0秒,而是將時間定格在50秒當中。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并沒有什么意義,但是在當時的比賽當中,計時器與終場鈴聲是相分離的,蘇聯以此為由確實可以說得過去,由此獲得了第二次發球,但很遺憾的是本次發球到終場鈴聲結束并沒有三秒鐘,很明顯,我們已經感受到裁判的火藥味很濃。蘇聯并沒有對此善罷甘休,而是堅持要第三次發球,將這三秒鐘充分利用,但這次比前兩次運氣似乎好了很多,凱文·喬伊斯拿到球之后下意識地暫停了一下,將前方美國的守將晃開,在無人防守的情況下打進了這關鍵的一球,在落地的時候終場哨聲吹響了。最終蘇聯以51∶50的分數贏得了這場比賽。這樣的結果似乎讓人很難理解,蘇聯的三次發球到底合不合理,在整個比賽當中似乎很難確認,但從最終的結果上看出,蘇聯教練“加蘭津”確實贏得了整個隊員和國家的認可。
二、敘事性的雙重并置
電影《絕殺慕尼黑》盡管從影片題目上看就已經表明最終的勝利仍然屬于蘇聯,但從整部影片的敘事性來看,導演梅格爾季切夫將故事情節拍得是一波三折,通過球員之間的激烈表現和兩國教練之間的交鋒將整部影片送上了高潮。雖然《絕殺慕尼黑》影片是一部紀錄片,沒有科幻片那些玄幻的鏡頭,讓觀眾的視覺不斷跟著鏡頭切換引起內心的愉悅感。通過球員們之間團結的氛圍和教練“加蘭津”的英雄形象引起觀眾內心的共鳴,這似乎與后現代美學審美下的“反英雄主義”和“陌生化”主張相違背,“加蘭津”的英雄主義形象塑造并沒有引起人們的不適,反而在觀眾的心里教練“加蘭津”是一個鮮活的英雄。1972年的蘇聯正是窮苦時期,人民的生活捉襟見肘,在當時政治意識的折射之下窮苦坎坷的年輕教練帶著一群困難的球員進行比賽。從這方面看,教練“加蘭津”是一個英雄人物。
教練“加蘭津”上任之前,蘇聯的主教練就因為政治問題被革職,整個球隊一盤散沙。年輕的“加蘭津”剛上任就宣布要打敗美國的“夢之隊”,這在當時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整個球隊的內部充滿各種矛盾,教練“加蘭津”雖然是蘇聯國家籃球隊的主教練,但自身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他的孩子得了重病,急需要一筆錢為孩子治病,他必須保住這份工作;蘇聯隊的主力球員謝爾蓋因為在訓練時用力過度,膝蓋損傷極為嚴重,在比賽中已經減緩了速度,球隊的后衛已經不適合擔任了;二號球員別洛夫因為得了重病,導致訓練的時候時常因為疾病不能發揮出應有的實力,而且在感情上他由于重病與女朋友分手;剩下的保勞斯卡斯與扎爾穆罕莫多夫,一個因為打職業籃球收入太低考慮要不要出去尋找一份新的工作,另一個因為視力嚴重下降,擔心自己不能夠正常參賽而被取消資格。每一個球員都有自己的打算和問題要解決,教練“加蘭津”宣布要用這樣的球隊來打敗美國常勝近四十年的“夢之隊”,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這為教練“加蘭津”后續的英雄塑造埋下了伏筆。在即將要參加比賽的時候,別洛夫因為重病急需要治療,教練“加蘭津”毅然拿出本來為自己孩子治療的醫藥費為別洛夫治病,由此引發了“加蘭津”日常生活的窘迫和家人的不解。來自家庭的壓力和全國人民的期望讓“加蘭津”的壓力倍增,一場籃球比賽肩負著無數人的人生,他們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這場籃球比賽上,慢鏡頭下的婚禮和雪山前的溫馨鏡頭就是隱喻。
正是這樣的一支球隊,通過“加蘭津”教練的訓練和愛心的幫助,讓這個充滿各種問題的球隊逐漸在教練身上尋找到了“愛”與“團結”的球隊精神,整場比賽中的180°轉身扣籃、胯下的暴扣等激烈的球技讓觀眾眼花繚亂,讓人內心澎湃。在整部影片的敘事中,梅格爾季切夫在塑造教練“加蘭津”時采用敘事性的雙重并置,即將他大義凜然愛心救助隊員的事跡采用遙感鏡頭敘寫,又將球員們贏得比賽之后將厚厚的獎金信封放到教練“加蘭津”手中讓他為孩子治病。雖然說是一場驚艷的籃球比賽,而影片的敘寫則是一場“愛”與“團結”的籃球精神的呈現。
三、“加蘭津”形象的重建
我們知道,后現代審美下的影片都是反叛“英雄主義”,通過故事的邏輯敘事情節走向觀眾的審美,通過觀者的視知覺體驗從而產生對影片的重解,而在傳統美學下的美國大片則是通過鏡頭的不斷切換,通過視覺的刺激來引起觀眾內心的快感,達到內心審美的愉悅感。電影《絕殺慕尼黑》實質上是立足于視覺層面上對后現代美學和傳統美學的結合,因此,在敘事手法上不能單純判定它的審美方式是什么。由此,我們就必須對教練“加蘭津”的形象進行討論了。
教練“加蘭津”在人物形象的設置上筆者認為具有雙重屬性。“加蘭津”教練在現實中的人物原型是佛拉基米爾·康德拉辛,他是列寧格勒人,現實中的康德拉辛也是一位籃球教練,但是他的兒子并沒有患重病。這部電影的伊始最不滿的就是他的兒子耶夫根尼亞,他將自己的父親告上法庭,由此導演將影片中的教練名字改成了“加蘭津”。雖然是現實中的傳記,但這并不影響影片的成功,除了孩子之外其余都是故事原型的真實寫照,教練“加蘭津”為自己的球員治病,這筆錢本來就是為自己孩子使用的,到后來蘇聯的球員獲得了比賽的冠軍,他們集體將獎金送給教練“加蘭津”。這種形象的設置不是為了體現“加蘭津”個人的偉大,而是為了傳達教練“加蘭津”與球員們之間的信任和情感,從故事情節敘事上他們通過情感和愛心的升華,達到對電影主題升華的目的。由此看來,不論教練“加蘭津”的名字是何稱呼,也不論他的兒子是否生病,單從敘事性審美上看,“加蘭津”形象就特別符合后現代審美下“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每一位觀眾都是當下社會環境下的載體,都對當下的審美具有清晰的認知。因此,電影《絕殺慕尼黑》中教練“加蘭津”在人物形象的設置上具有多重性,既是“愛”與“團結”籃球精神的化身,同時也是后現代審美下“英雄”人物設置的產物,伴隨著一絲政治化的成分,是一個多元化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