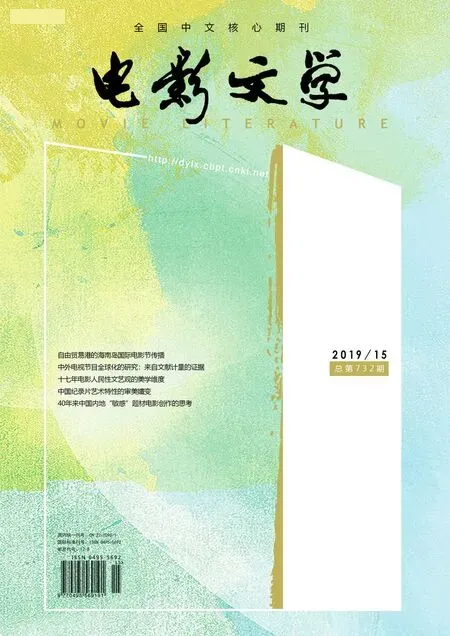文學倫理學批評下《死生契闊》的道德言說
郭智文(羅定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羅定 527200)
印度現實題材電影以其深刻的社會批判與人文關懷蜚聲國際。在文學倫理學批評視角下,這類影片通過聚焦印度社會中阻礙人性健康發展的道德現象,從倫理環境的構建與倫理身份的選擇上拷問倫理道德的真偽,從而完成道德言說。《死生契闊》為一部小成本電影,摒棄了寶萊塢式電影的宏大歌舞場面,但其卻利用雙線敘述、現實主義拍攝手法更直接深刻地揭示了印度社會新舊倫理規則下的沖突。影片以印度恒河邊的瓦拉納西古城為背景,交叉敘述了女主角戴薇和男主角迪帕克與各自男女朋友的悲傷愛情故事,利用悲劇張力讓人們對舊倫理下的既定規則進行深刻反思。
一、圣潔或骯臟:新舊倫理環境的構建
印度倫理觀歷經了由宗教教義約束到甘地圣雄感化再到法律制約的過程,[1]然而,由于宗教等舊倫理秩序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深遠影響,印度倫理法制化建設困難重重。影片所關注的種姓制度,雖然自印度獨立后,其在法律上就已被廢止,然而思想毒瘤卻影響印度至今。[2]該制度體現著宗教教義下的潔凈定義,規定人體糞便、唾液等、生死以及多次轉手的人與物品為不潔的存在,且與不潔之物接觸越多,其工種地位越低。隨著時代發展,這些舊倫理規則已經阻礙了法制社會發展。影片通過構建沖突的新舊倫理環境,讓人們不斷質疑圣潔和骯臟的定義。
首先,在拍攝藝術及敘述手法上,影片采用寫實手法揭示舊倫理秩序下神圣工作的虛偽性。其一,燒尸這一寓意“輪回”的神圣宗教環節被導演通過寫實拍攝手法祛魅。影片中燒尸工人醉酒渾噩度日,去儀式化后的工作目的僅為獲取洗尸灰后的貴金屬和每10年結算的燒尸紅利。另外,燒尸過程對環境的污化,在寫實鏡頭下被無限放大,強烈的視覺反差激發著人們對圣潔的思考。其二,戴薇父親作為圣壇專家,屬高種姓階層。他還曾是大學梵語教師,然而由于忙碌工作,忽視了重病的戴薇母親而導致其病亡。父親自責下辭去大學教職,從事圣壇儀式服務,然而他卻需要做梵語翻譯等多項兼職工作才能勉強維持生計。低薪的“圣壇專家”僅為茶余飯后被人嘲諷的談資。這也再次模糊了人們對圣潔的定義。
其次,以愛之名美化新倫理行為。在現實題材影片中,愛一直是用來撬動倫理桎梏的利器。例如《廁所英雄》中的男主角為了讓妻子不用早起行遠路如廁,不顧家人反對毅然自建室內廁所;《印度合伙人》中男主角為了讓妻子免受月經期痛苦而不顧家人和村民驅趕于艱苦條件下生產衛生巾;《起跑線》里中產夫婦為了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不惜喬裝貧民獲取教育機會等。《死生契闊》中也是如此,為了擺脫種姓制度下高低種姓不能戀愛通婚的舊倫理秩序,還有擺脫宗教倫理下的不潔行為定義,兩對年輕人毅然追尋美好的愛情。影片利用深景特寫等拍攝視角和為數不多的背景音樂美化影片中突破倫理桎梏的行為。影片中迪帕克樹下偷吻夏露,恒河中船頭害羞對話等鏡頭,都極具美感。影片中就連小孩潛水撿硬幣的賭博行為都用水下特寫的慢速鏡頭進行美化,當然這一行為也為主人公擺脫倫理束縛埋下了伏筆。
再次,設定教育為突破倫理困境的鑰匙。在全球化經濟背景下,越來越多印度年輕人通過網絡閱讀和接受大學教育,接受主張自由、平等的法制化倫理價值觀。教育不僅提供了突破能力也提供了動力。戴薇通過自學電腦并利用網絡接觸到小城鎮之外的倫理價值觀。通過教育,戴薇不再依靠家庭男性,具備通過網絡求職且獨立營生的能力。對迪帕克而言,倘若不接受教育,來自低種姓家庭的他便永遠逃不開燒尸生活。印度憲法實施“保留政策”保證低種姓人的受教和求職權力,迪帕克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印度理工大學的學生,并通過“擇優錄取”找到一份滿意工作,從而改變了社會地位。雖然底層賤民的出身讓迪帕克在追求高種姓女子的過程中極度自卑,然而教育提供并保證著兩人交往的唯一可能。
二、獸性或人性:主人公倫理身份的選擇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人的行為是獸性因子與人性因子互相作用的結果。獸性因子是指原始欲望的自由意志,而人性因子指倫理意識,表現為理性意志。[3]在倫理禁忌作用下,人性因子控制著獸性因子,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在沖突的倫理環境下,觀影者需要客觀理解主人公倫理行為或身份選擇,才能更好地理解影片的道德言說意圖。
首先,影片中最能體現戴薇倫理身份選擇的場景是她與大學生皮許約去旅店初嘗禁果的過程。她倆在計算機協會相知相愛,在原始欲望的“獸性因子”驅使下突破了舊倫理規則下的禁忌,卻被破門而入的印度警察暴力終止。當事二人截然不同的反應展示著不同倫理認知下的不同身份選擇。皮許的言行不斷詮釋著這是一場突破禁忌的“獸性”舉動。為了掩蓋這一行為,他在性行為前拉緊窗簾,調高電視聲音,較生動地表現了傳統倫理禁忌下獸性因子與人性因子的斗爭過程。然而,在警察進入后,禁忌的束縛力量再次戰勝了一切,皮許恐懼、求饒,并趁警察不注意躲進廁所。在印度警察用聯系家人恐嚇他時,皮許內心最后一道防線被攻破,違背禁忌的自責讓他果斷地選擇了自殺。戴薇的反應則截然不同。影片開頭以蒙太奇手法交叉特寫與中遠景鏡頭,交代戴薇面見男友的全部過程,包括面見男友前的刻意裝扮,使得戴薇急切、謹慎、喜悅的神態于銀幕前鋪開。性行為開始前的主動與對男友行為的引導都能看出她的果敢與坦然,在她看來,愛情與性是互相吸引且水到渠成的過程。同樣在面臨警察時,她雖然也表現得恐懼,然而通過她那“你們是否弄錯了”的發問再次確定了她倫理身份的選擇及與舊倫理秩序的格格不入。雖然皮許的自殺震驚了戴薇,但她卻始終不因被稱作“丑聞”的性行為而羞愧。為了付清印度警察的30萬盧比勒索款,她跟隨父親在當地找尋工作,同事卻因“丑聞”事件侮辱和騷擾她,戴薇果敢地辭去工作,通過網絡途徑找到了更高薪的鐵路臨時售票員工作,同時也確定了徹底離開瓦拉納西的決心。
其次,影片中最能體現迪帕克身份選擇的便是他與高種姓家族女子夏露的愛情。男主迪帕克在社交平臺上看到了夏露的相關信息并一見鐘情。在得知夏露來自高種姓的古普塔家族后,種姓差異讓他產生猶豫但并未讓他停止追求。在初次會面的餐桌上,迪帕克得知夏露愛好詩歌,愛聽廣播與音樂,便通過用電話錄音制成音樂帶的形式給她制作生日禮物,夏露最終在迪帕克的追求下答應與他交往。
在舊倫理秩序要求下,迪帕克與夏露的交往表明二人的“獸性因子”戰勝了“人性因子”,也預示著兩人將遭遇極大的阻力。兩人的首次沖突出現在一次外出游玩的過程中,迪帕克不滿夏露多次詢問自己刻意隱瞞的住址,他害怕夏露因種姓差異離開自己,終于爆發了怒火。然而夏露并未因此離開迪帕克,反而由于他的誠實與要強深深地愛上了他。全片從未露面的夏露父母不斷定義著兩人結合的“獸性”。在外出就餐時,夏露父親以畫外音形式說:“這菜好吃,就是不太干凈,如果老板來自我們的階級就好了。”父親將不潔與低等階級畫了等號。雖然父母不同意兩人結合,但夏露卻愿意在迪帕克找好工作后與其私奔。她倆選擇了主張個性與身體自由的新倫理身份,拒絕了舊倫理秩序,然而夏露全家因車禍死亡的事件讓這一突破倫理禁忌的行為再次以悲劇結尾。
觀影者不禁思考,戴薇與皮許的性行為、迪帕克與夏露的愛情是否真的有違倫理禁忌呢?作為“正義”的守護者印度警察“提起皮許一頓棍棒毒打”“猥瑣拍攝戴薇在床上的狼狽表情和狀態”“用聯系家人的方法威脅皮許”,以及皮許的極端反應和戴薇父親甘愿被勒索,似乎在告知觀影者,這兩位偷嘗禁果的青年男女確實違背了倫理禁忌,將被人所不齒,并且夏露全家車禍身亡也似乎預示著沖破禁忌的悲慘結局。然而在主角光環下的戴薇和迪帕克卻用各自不卑不亢的言行宣告了自己的倫理身份,美好愛情的悲劇結尾再次讓觀影者對“獸性”與“人性”定義產生新的思考。
三、悲劇或希望:自我倫理意識的提升
《死生契闊》中導演采用寫實的電影拍攝手法,雜亂的尸體焚燒,清洗尸灰的骯臟恒河水,還有毫無人性、無理敲詐的印度警察,都讓人們不斷質疑著舊倫理規則下正義與圣潔的真實。影片結尾以“無聲勝有聲”的道德言說似乎告誡人們:種姓制度等舊宗教倫理已經不再適應新時代的發展。年輕人應通過教育途徑摒棄了原來的舊倫理秩序,改變自己的倫理環境,提升自我的倫理意識。
(一)跳恒河:擺脫舊倫理束縛
在電影的表層敘述中,兩位主人公各自突破倫理的行為給兩個家庭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然而影片中的跳恒河行為,卻被儀式化地賦予了新的含義。迪帕克在女友夏露死后,萎靡不振,久久不能回歸到正常生活。與此同時,哥哥偷偷賣掉了屬于父親燒尸工作的紅利名額,得到30萬盧比,然后逃離了家。迪帕克本可賣掉燒尸中得到的夏露的紅寶石戒指,然后買回名額。然而他卻沖動地將戒指扔進了恒河,緊接著又跳進恒河打撈未果。電影用寓意明顯的跳恒河行為,滌去迪帕克內心對過去情感的眷念及繼續燒尸工作的可能性,從恒河走出的“嶄新”迪帕克決心繼續求學與求職生活,開啟了新的人生篇章。
在另一故事線中,警察拍下戴薇的視頻后,利用父親名聲對其進行勒索。戴薇父親想盡了一切辦法,甚至還參與到讓自己顏面無光的跳河撈錢賭博當中。對戴薇而言,家中收養小孩跳恒河的行為表面上是參與撈硬幣的賭博,然而也因此,他們才能從恒河中撈到迪帕克扔掉的紅寶石戒指,從而解決了被人勒索的危機,最終擺脫舊倫理的束縛。
(二)渡恒河:迎接新生活
電影中戴薇在皮許自殺之后,一直想通過聯系他父母表達自己的歉意。然而處在倫理困境中的戴薇無法鼓起道歉的勇氣。她在離職之后,通過網絡投遞簡歷的方式找到了鐵路售票員的臨時工作。由于熟悉電腦操作,她很快適應了工作節奏,也立下了就讀阿拉巴哈德大學的決心。她在讀書之前還只身前往皮許家中,雖然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其父母的咒罵,然而她的內心卻得到了解脫。迪帕克也通過努力學習尋求著離開的機會,由于他刻苦用功,他最終獲得了在阿拉巴哈德鐵路部門實習六個月的機會。戴薇和迪帕克,兩個努力突破舊倫理體制的沖鋒者,在電影的最后,一起坐上了去桑干的船。
“你第一次去桑干嗎?”“桑干應該去兩次,第一次獨自一人,第二次就有伴了。”此處迪帕克臺詞寓意著在這場沖突舊倫理樊籬的旅途中,雖然開始是孤獨的,但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踏上同樣的旅程。影片結尾導演用一個長達10分鐘的固定無聲長鏡頭記錄了戴薇與迪帕克一同渡恒河的過程,船夫輕搖著船槳,在落日的余暉之下,載著這兩位新舊倫理沖突中的“勇士”走向代表新生活的彼岸。“無聲勝有聲”的道德言說也代表著影片對新倫理的期待。
四、結 語
這部來自印度年輕導演尼拉杰·加萬自編自導的影片,用與主流印度電影不同的敘述手法,關注當代印度法制倫理建設過程中的疑難與阻礙。通過對舊倫理下所謂“圣潔”環境的現實化描寫,讓人對圣潔與骯臟、獸性與人性的倫理定義產生了新的思考。愛情悲劇的表層敘述之下似乎隱藏著對新生活的希望。電影中譯名引用詩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呈現著對美好愛情的追求與向往,更是寄托了影片對更具人性的法制化倫理前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