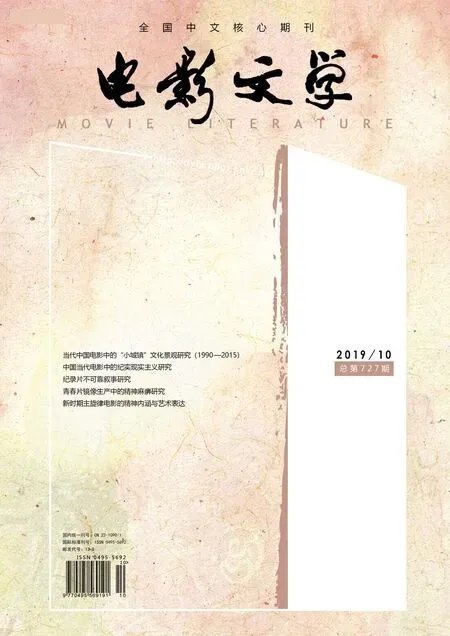國產青春片敘事的現實主義轉型
——從《狗十三》說開去
胡丹丹 (鄭州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2018年12月,沉寂五年再上映的這部 《狗十三》 以黑馬之勢,獲得一邊倒式的好評。上映之前就攬獲了第六十四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水晶熊最佳影片獎以及第21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等獎項。“這就是我的青春”“這就是我爸”“這就是我”等評論迅速蔓延在社交網絡上。在國產青春片美學與市場的雙重低迷下,這部沒有類型優勢、沒有流量明星加持、沒有視聽沖擊的作品卻大放異彩。究其成功的原因,跳出類型敘事的枷鎖,實現敘事上的現實主義轉型是不可或缺的一點。
現實主義是我國電影創作的優良傳統,支撐著民族影像藝術的發展,它以深刻的人文關懷思想和鮮明的批判精神滋養了許多創作。然而,縱觀近幾年的國產青春片,一直在用“回首”的視角去追憶,敘事上形成了以類型人物、校園愛情、懷舊敘事為主的模式化套路。現實主義以一種弱化和癌變的狀態,成為青春片的邊角料。盡管在去年的《閃光少女》《快把我哥帶走》中,國產青春片已經有意識地向著深層現實思考的主題上靠攏,但是現實主義批判的力度最終還是被電影美夢所消解。而《狗十三》通過文本、主題、藝術手法的三重功效,實現了國產青春片敘事的現實主義轉型。在當今現實主義回潮的大勢之下,為國產青春片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本文就從敘事文本、人物塑造、深層解讀三個方面探索《狗十三》如何進行現實主義敘事表達。
一、內外修辭的共同發力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成熟的創作精神或者文藝理論,從19世紀中期開始,已經影響了數百年以來的藝術創作者,并衍生出了一系列理論或者學說。在這些紛繁流變的觀點中,我們已然可以抽取出現實主義的核心,那就是:在作品中藝術地反映現實。這一核心毋庸置疑地對藝術作品提出兩點訴求:其一是要求藝術作品忠于現實;其二是藝術作品要傳達現實主義精神,這兩點訴求同樣也規定了現實主義作品中修辭的意義所在。《狗十三》從文本系統自身和社會意義兩方面入手,通過傾向于“審美認同”的內修辭以及傾向于“社會認同”的外修辭共同發力,達到了藝術地反映現實這一目的。
(一)作為內修辭的“塊莖文本”
就內修辭而言,《狗十三》采用的是一種具有后現代傾向的塊莖式思維。“塊莖”這一概念是德勒茲與其合作伙伴瓜塔里在其著作《千高原》中提出的一種具有解轄域化功能的思維模式,并將這種由“塊莖思維”生成的文本稱為“塊莖文本”。在德勒茲的觀點中,“塊莖文本”就是一個多元體,它不會依賴于某一中心,“塊莖自身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從分叉的表面擴展,朝向各個方向結成各種球莖和塊莖”。[1]并且隨著考察維度的變化又呈現出多變性,這與現實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與流變性相一致,因此“塊莖文本”的模式可以實現最理想的忠于現實的效果。前幾年的國產青春片,基本都是圍繞一個中心情節展開,這種文本模式背后是“樹形”思維,即從一個固定的點出發,沿著一條清晰的脈絡來拓展情節。而《狗十三》則采用一種去中心化的塊莖文本敘事。影片中的每一個人物、細節、場景,在不同維度的度量下,都能引發不同的思考,這些思考都是深刻的、真實的。在文本中,你可以解讀到初戀的迷茫、夢想的追求、社會化的殘酷、中國式離婚、代際沖突、家庭教育,等等,它們并不是從某一點生發出來,而是客觀地、安靜地滲透在敘事中。例如影片開始,吳老師勸說李玩與父親參加英語興趣小組的一場戲中,從這個開口閉口只談成績與升學的老師身上折射出當今學校教育的現狀;不尊重女兒意志強制報名,事后以金錢討好的父親是許多中國式家庭的圖景;而李玩的沉默、迷惑和倔強無疑是對青春期少男少女們心理的真實寫照。通過一個簡單的場景就實現了家庭場域、校園場域和社會場域的多元表達。由此看來,我們發現“塊莖式文本”就像一張網,每個點之間都是相連的,它沒有中心,因此可以進行多場域的同時和多向敘事。在影片高潮“吃狗肉”的片段中,一個中國式飯局將職場的虛偽、對傳統文化誤讀的諷刺、父權的強勢、弱勢群體的處境整個囊括其中,通過這些冰山一角去窺視整個時代的多面性。影片結尾更是巧妙地通過弟弟進行總結與升華,那個集萬千寵愛與一體的弟弟,依然被迫喝著牛奶,在溜冰場上摔倒、哭泣,那是中國式家庭教育的結果、是爺爺奶奶寄予厚望的孫子、是在飯局上背《三字經》討領導歡心的“工具”,更是多年前的李玩自己。《狗十三》正是通過這種不斷的解域與再結域,編織了一個復雜的網,在文本的多維立體綜合中,實現了對現實生活的多維透視。
(二)作為外修辭的現實批判
在真實的書寫現實層面,《狗十三》通過“塊莖”文本從縱橫兩個維度對現實生活進行呈現,那么在傳達現實主義精神的層面,就需要作為“社會認同”的外修辭來著重發力。外修辭是作品“對自身社會身份的想象,或者說是它如何界定自己與當下語境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自己與廣闊復雜的大時代之間的關系”。[2]因此,要實現社會認同,就需要創作者將文本放置在當下的社會、歷史、文化、政治等大環境中,去準確地把握真實的社會關系和傳達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本質真實,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所強調的“歷史的真實”。那么,文本在當下時代和社會語境中的價值深挖就變得至關重要,但是基于不同創作主體差異,文本價值取向也必然會具有強烈的主觀性。需要強調的是,在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中,對客觀真實性的需求與對主體傾向性的呼吁并非是一種悖論,相反,這種傾向性恰恰是現實主義的另一重要特征,即現實主義精神的傳達。“這是由現實主義藝術家所獨具的現實批判精神所決定的。”[3]從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開始,現實主義藝術家們便“開始以冷峻的目光審視資產階級社會現實。勇敢地直面現實、直面人生,以人道主義為武器來批判現實成為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根本特征”。[3]這種深刻的批判精神沿襲至今,成為衡量現實主義作品的一個標準。綜觀前幾年的國產青春片,導演為觀眾營造的是一個個肆意美好的夢境,所有具有二元項的對抗性張力都在夢結束時煙消云散,理性的思考讓位給了“羽化式”處理,作為外修辭的深度批判在作為內修辭的文本中被消解掉。這種抵牾,明確顯示出了創作者現實批判精神的失落。而《狗十三》則是在內外修辭的共同作用下,更加強化了這種批判和沉思的力度。基于這一目的,無論從宏觀的時代折射到微觀的細節刻畫,都帶有導演的現實主義審視。尤其是對家庭、教育、社會、青春、愛情、職場等多層思考的結果進行疊加,使其打出的每一拳都是一記重擊。這樣,觀眾才能在李玩平靜吃下狗肉時而無比心痛,在她跑到小胡同掩面痛哭時而心酸,在她麻木地觀望弟弟那似曾相識的命運軌跡時深感無奈。甚至到了影片結尾,導演也并未給我們一個完整圓滿的大團圓結局,而是讓觀眾帶著沉思回到現實世界。這些,都是影片對現實真實本質的探尋,同時也是對這些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的沉痛批判。在內外修辭的共同作用下,《狗十三》才能贏得共鳴,實現與觀眾的最佳交流。
二、人物形象的多維塑造
在現實主義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成功與否也需要通過是否藝術地反映現實這一標準來衡量,只有忠于現實才能使觀眾有代入感,從而引發共鳴。由于人性本身的復雜性,在進行人物塑造的時候必須要進行深入洞察和多維呈現。而國產青春片發展至今,人物的塑造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規范性的類型,大多是對觀眾最完美幻想的滿足,女神、學霸、帥哥等烏托邦式的人物類型呈現為一種懸空性,即反現實主義或者偽現實主義。以此反思,我們發現《狗十三》成功跳出了這種模式化,實現了典型人物和圓形人物的合圍。
(一)以小見大:典型人物個性與共性的對話
恩格斯曾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真實以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4]在此之前,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別林斯基、馬克思等都先后提出了自己關于典型人物的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文藝理論。從他們的論述中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典型人物就是個性與共性的有機統一。個性就是“充分體現社會生活反映某種本質的現象、表現必然性的偶然性,是具有規律性的感性實在”。[5]共性則是這種現象的本質、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具有真理性的本質。因此在進行典型人物塑造的時候,我們不僅要關注他是什么樣,同時還要揭示他為什么會這樣,也就是了解人物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前幾年國產青春片對人物的塑造都是禁錮于觀眾定向期待之內的,無論人物性格還是人物動機都是公式化的。而《狗十三》的成熟之處正在于綜合把握觀眾的定向期待與創新期待之后,塑造出既能獲得觀眾情感認同又具有獨特性的人物。李玩,一個13歲的青春期少女,她敏感又任性、封閉又成熟,從影片開始的大段獨白中,我們就一邊同感于青春期的困惑,另一邊也訝異于一個少女如此深刻的認知。她總是沉默地把自己隔離開來,隱忍地宣泄情緒,從默默地找狗、生日宴中的孤獨、平靜地吃狗肉到最后悄然痛哭。另一方面,她似乎又有著同齡人不具有的成熟,就像她對平行宇宙的執念,那是一個少女對世界的徹悟和美好期待。而這一切人物動機,都來自于時代的賦予。中國式離婚的家庭環境和教育方式、代際觀念的沖突和來自引導者強制規訓、青春期的迷茫與躁動,是這個鮮活李玩背后的無數個我們。父親這個角色亦然。父親,在中國式社會結構中本身就呈現為一種多面體:事業的打拼者、家人的保護者、長輩的贍養者、小輩的引導者。因此男性在擁有多面權利的同時也承載著多個角色賦予的壓力。影片中李玩的父親就是將這種權利與壓力的并存體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面使自己在家庭中處于領導的地位、在職場中處于被賞識的地位,由此付出的代價就是他要小心翼翼地討好女兒、父母、妻子、領導,由不得一絲任性。作為當下中國式父親的一個投射,他的個性化彰顯就表現為一種矛盾的并存。在外人面前他溫文爾雅,喜好詩詞,個性灑脫但極盡諂媚;對待子女他暴力與溫情并存。通過李玩和父親,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時代的多面性與統一性,通過微觀的李玩與父親,揭示出其背后的宏觀的時代面貌。在個性與共性的對話中,才能實現現實主義的真實反映與現實主義精神的傳達。
(二)二律背反:圓形人物流動性與復雜性的呈現
如果說典型人物的概念主要是“從它所呈示的社會學和哲學的范疇來制定”的話,那么圓形人物則“主要是從它們所呈示的藝術審美形態這一范疇來確立的”。[6]因此,在現實主義這一大的范疇之內,除了關注人物的個性與共性對話之外,還要關注人物性格內部的多重形態。福斯特的圓形人物理論要求創作者在塑造人物時,要進行全方位、多維度、多層面的藝術審視,塑造出飽滿的、復雜的、立體的性格,同時還要展現人物性格發展的真實過程,這種理念與人性本身的復雜性和流變形成直接的對照,因此我們可以從復雜性和流變性兩個方面來綜合考量人物。李玩的人物性格發展過程就具有一條十分清晰、流動的脈絡,即:養狗—丟狗—換狗—接受新狗—狗被送走—麻木這一過程。通過這個流變的過程,展現少女李玩如何一步步被規訓,成為大人眼中“懂事的孩子”。在愛因斯坦剛剛出現時,李玩像大多數青春期的叛逆少女一樣不愿意接受,盡管她心里是歡喜的,但是依然口是心非地說自己不喜歡狗。從這個小插曲中,我們看到李玩矛盾又叛逆的一面。之后,她慢慢接受了愛因斯坦,因為她發現愛因斯坦就是另外一個自己,孤獨又倔強。這個過程中,導演披露給我們的是叛逆少女內心對這個世界隱隱的失望,以及與對愛的渴望。愛因斯坦的意外走失,家人完全不尊重李玩的做法,讓她看清了成年人的虛偽,于是她反抗,跟家人爭吵、滿大街找狗,可最后也不得不在家暴與爺爺的受傷中隱忍。“新愛因斯坦”到來時,李玩已經學會了沉默著倔強,她不再跟家人正面沖突,將自己的情感小心隱藏起來,默默地尋找愛因斯坦,也尋找丟失的自己。弟弟的突然出現,不僅成為“新愛因斯坦”的對抗力量,也成為李玩進一步向成人妥協的標志。當家人為保護弟弟將“新愛因斯坦”送走時,李玩只能選擇接受。影片最后李玩在街上看到丟失的愛因斯坦時異常冷靜,任由別人帶走,這時少女的自我意志完全被剝離,已經收起自己的觸角,小心翼翼地去適應成人的法則。通過這條線,李玩這個人物在流動發展的過程中逐漸飽滿起來。當然,在橫向拓展的同時,影片也不斷地沿著橫截面進行縱向深度剖析。少女李玩抗拒父親、家人以為她好為名做出的一切努力,因此我們看到她是任性的、不懂事的。同時她又深愛自己的父親,好消息第一時間跟父親分享,期待父親陪伴的每一寸時光,為父親的傷心而心痛,此時的她又是柔軟的、乖巧的。在復雜的家庭結構中,李玩敏感、小心翼翼,就像她在參加弟弟生日宴上的不知所措,在跟弟弟玩耍時的試探。同時,她身上還具有放逐的、灑脫的悖論呈現,她跟李想去喝酒、蹦迪,又跟李想談平行宇宙,她將這個世界看得如此透徹。她具有青春期少女所有的單純、美好、懵懂、迷茫,同時有兼有同齡人不該有的隱忍、冷漠、成熟。這種二律背反的呈現,使人物更加具有藝術張力和感染力,也因此更加具有現實主義的力量。
三、敘事話語的深層闡釋
恩格斯認為,現實主義要真實地描寫社會關系,這種真實描寫絕對不僅限于藝術手法和文本的忠實性,而是追求一種“較大思想深度和歷史的內容”[4]。他要求我們在歷史的維度中,透過現象看本質,并將這種歷史的本質,化為真實的現實書寫。恩格斯的這種觀點,同樣體現在羅蘭·巴特的理論體系中。巴特認為,神話符號是“一種言說的方式”,它的原則就是將“歷史轉變成自然”[7]。在影視敘事的過程中,通過現象表現歷史的本質,或者將歷史本質轉換為自然,就變成了如何對敘事話語進行編碼和解碼的問題,變成了如何通過直觀的視聽語言來傳達深層含義的問題。《狗十三》通過將敘事語言符號化,完美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在影視藝術的現實主義表達中,符號的能指是以一種隱匿的不在場的狀態傳達意義的,這種不在場使作品在再現現實的層次上達到透明書寫的效果,而對所指意義的挖掘即是探尋歷史本質的過程。因而,對敘事話語符號的建立與深層解讀是直達現實主義的必經之路。
(一)內心外化的隱喻與轉喻性符號
影視藝術作為視聽藝術,要運用蒙太奇思維將一切可視、可感、可聽的事物通過畫面和行動的書寫表現出來,即使是人物的內心活動也需要轉化為視聽元素。在這一轉化過程中,雅各布森提出了兩種最基本的模式即隱喻與轉喻。“隱喻是通過相似性將一種事物轉換為另一種與之相關的事物”,如以“窗戶”隱喻“牢籠”。而“轉喻則是通過鄰近性用一個事物的名稱取代另一個事物”,[8]84如以“小鳥”來轉喻“天空”。并且他認為:“隱喻和轉喻作為一種手法被利用,其目的是為了使我們感覺事物更明顯,并且幫助我們理解它,總之,是為了表現出最大限度的真實性。”[8]85他明確地將隱喻與轉喻作為現實主義手法進行了強調。因此,只有深入闡釋影片中的隱喻與轉喻符號背后的真實性,才能實現現實主義表達。從“狗十三”這一片名開始,導演就已經明確賦予愛因斯坦以隱喻的特性,作為能指的狗,通過卑微、單純、無力等相似性特征成為李玩的隱喻符號,在當下的文化社會語境中,愛因斯坦成為千千萬萬像李玩一樣的青少年群體復雜心理的隱喻符號。除此之外,李玩口中反復提到的平行宇宙,也是作為李玩內心活動的轉喻符號出現的。它是少女李玩對現實生活迷茫、困惑、失望時的心靈休憩所。在李玩看來生活像紅毛衣或綠毛衣、夏天或冬天、現實與理想,一個是不可扭轉的生活,另一個就是在平行宇宙中可以被彌補的遺憾。這也是為什么導演在愛因斯坦走失、“新愛因斯坦”到來這種小高潮的情節中,都會出現李玩有關平行宇宙的暢想。在細節之處,影片還通過泡面、海報、文身等具有明顯狂歡性質的符號,來隱喻青春期少女的叛逆。在轉喻符號的提取上,導演似乎做了更加隱蔽和深層的處理。例如李玩每天聽到來自樓上精神病患者的鳥叫,這個與劇情發展似乎毫無關聯的人物,卻具有豐富的所指意義。在家庭、社會、學校的多種束縛下,李玩是壓抑的,因此她渴望掙脫所有的束縛,實現自我的自由。因此,導演就埋下了這一神秘的意象:“學鳥叫的精神病患者”轉喻著“自由”。但是在這個社會語境下,所有的人都是被規訓的,必須要按照一定的世界法則而生存。而打破這個法則的人就是異類,最終還是被送到醫院,回到社會法則之內。通過這個轉喻,將李玩渴望—掙脫—被規訓的內心世界展現得淋漓盡致。為了強化這種心理,導演還設計了教室中被老師打死的蝙蝠、家人每天端過來的牛奶等轉喻符號來豐富情緒。在這些符號中,影片的敘事話語達成了層的編碼,這才使我們在解碼的過程中,得以深入人物心理,揭示社會真相,探尋歷史本質。
(二)現實批判的意指性符號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通過二級意指系統,揭示了符號的意義產生過程。他指出,第一級系統中的能指與所指構成符號的直接意指層面,同時,這一能指與所指的共同體成為二級系統中的能指,并與所指一起構成符號的含蓄意指層面。因此含蓄意指系統是復雜的,它與不同的個體背景、社會認知、所處環境與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狗十三》形象地展現了少女李玩在多重閹割下,最終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犧牲品的過程。影片貫穿始終的批判精神,主要來自于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巴特還認為,在人類文化的變遷中,符號往往會脫離事物的原意,而具有特殊的意義,即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必須要從這些意指性符號著手。《狗十三》通過強化“牢籠”這一意象,直指意識形態陣地的占領者,即中國式職場、父權、應試教育、傳統固化思想、重組家庭等社會現實問題。第一個明確的意指性符號就是“窗欄”。如影片中多次出現李玩一人在窗前的畫面。叛逆少女在窗前吃泡面、見識到成人的虛偽后在窗前痛哭、聽到樓上鳥叫時向窗外的探望等。鏡頭都是隔著窗戶從外向內拍攝,“窗欄”就隔在李玩面前,束縛著少女的生活。在直接意指層面,“窗欄”的符號意義是束縛、隔離、保護,而在二級意指系統中,圍欄就是代表著成人法則的社會,它將少女的一切異枝全部折斷,規定她只能在法則內生活。第二個層面的“牢籠”意象來自于道德的審判。在李玩的生活中,所有的家人都打著“為你好”的旗號,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要求她。李玩無數次地表明自己不喝牛奶,但奶奶和父親完全忽視,認為小孩子就應該喝牛奶,這是為你好,甚至這位父親在酒局上讓李玩喝酒找到了正當的借口:你自己不喝牛奶。在一級意指系統中,牛奶的符號意義往往和營養、青少年等聯系在一起,但本片賦予它二級意指以諷刺的內涵,即成人的道德牢籠。影片最后,當李玩看到曾經的愛因斯坦,準確來講,是曾經的自己之后,被規訓的李玩平靜地接受它的離去不做任何努力。她獨自走進胡同,失聲痛哭。此時,頭頂的尋狗啟事以及背景處的教堂將分別作為兩種牢籠的代表出現在畫面中:尋狗啟事那是李玩被閹割的青春,教堂作為最神圣的符號對這一切進行道德審判。盡管“真實書寫”與“符號”之間有著歷史性的悖論,因為符號化的藝術往往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的,但是《狗十三》似乎打破了這樣的教條,因為這些意指性符號不僅僅停留在藝術層面, 重要的是符號背后的意識形態,這才是現實主義批判的直指對象。
在呼喚電影人現實主義意識覺醒的大勢之下,《狗十三》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借鑒的。它通過修辭、文本、人物和敘事話語的多重發力,在當下眾多具有現實主義品質的作品中,所達到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少有的。可以說,它代表了國產青春片進行現實主義深耕的輝煌成就。不可否認的是,盡管《狗十三》在日漸追求“高質”的電影市場中口碑過關,但是5000多萬的票房在當下動輒幾十億的票房神話中,著實有些凋零,即使與前幾年青春片的幾億票房相比也是相形見絀。那么,國產青春片今后的發展該指向何方呢?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青春期作為人類共同的人生階段使青春片帶有與生俱來的情感認同優勢,但是從影片類型發展的成熟性、豐富性、創新性與靈活性來講,國產青春片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因此,在現實主義回潮、時代變革、電影市場深度產業化的多重語境下,如何使國產青春片永葆青春是值得我們持續探討和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