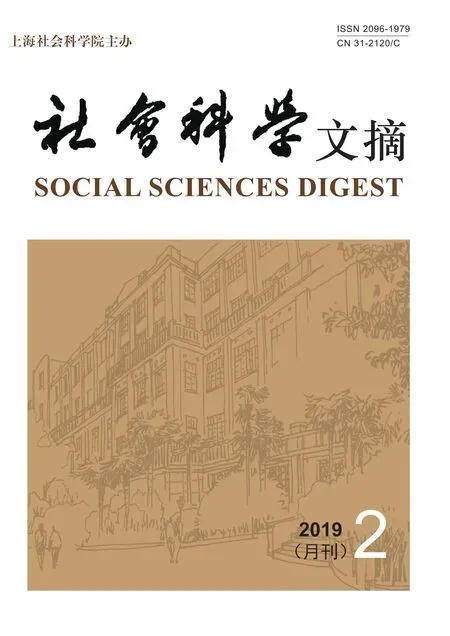實踐邏輯視野下的新型國際關系建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標志著冷戰結束后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征的世界秩序處于衰敗、危機和轉型之中,而對應于這種危機的另一面是新自由主義制度范式之外的另類大國——中國的欣欣向榮與國力增長。這一切不僅反映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使得新自由主義的制度范式及其背后的價值受到了全面質疑。在這種世界性結構嬗變的岔路上,由于過去形成的沉淀思維及其相關實踐不再適應于這種結構性嬗變,無論傳統守成大國還是許多發展中大國或多或少都面臨學習與適應問題。在這樣一個世界秩序的嬗變過程中,建立一個適應新情勢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只有在新的形勢下,經過長期的實踐,各國從中培育出新的慣習(habitus),進而在國際關系領域不自覺地形成相互適應與互動的實踐感(practical sense),一種新的社會事實才會實現,新的國際關系和秩序才能水到渠成。要感知與推動這一過程,必須知曉實踐過程中的相關知識及其邏輯。這些知識與邏輯較之一般我們熟知的國際關系理論知識更能貼切地反映國際關系中的實際過程。
表象知識與實踐知識
在國際關系領域,外交官們常抱怨學院派理論研究者提供的知識不實用,而學院派理論研究者又往往認為其理論知識是經驗的總結與升華。這種認知差異其實是對兩種不同知識認知的差異,即表象知識(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與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認知差異。
表象知識是觀察人類某個領域的實踐后,經過抽象概括與歸納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識。對表象知識最通俗并且帶有簡單化的概括就是理論知識、基本教義、一般概念,或者中國人常說的書本知識。這種知識有以下幾種特征:認知狀態是有意識、有目的和能用言辭表達的;它的獲取方式是通過正式的計劃或反思;它與實踐的關系是在實踐之后,具有實踐的事后性;它的推導性質是易于理解、便于證明的;思想與世界匹配的方式是從思想到世界(觀察);它的理性過程是,如果出現X情形,出于工具性或規范性理由,應該做Y;人們熟知的范疇是圖式、理論、模式、盤算和推理。
而實踐知識是人們在實踐中積累下的經驗和專門技能(know-how),中國人常常用經驗、技巧、竅門來表述。實踐知識在許多方面與表象知識具有相反的特征:它的認知狀況是默示的、無法連貫說清的(inarticulate)、無意識的;它的獲取方式是在實踐中或通過實踐經驗性地習得,或者是難以解釋地習得的;它與實踐的關系是與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是執行中的知識;它的推導屬性是隱含式的,不言自明的;思想與世界匹配的方式是從思想到世界(從“做”中來體驗);它的理性過程是,在X情形下,Y產生(不加思考的);人們所熟知的范疇是經驗、常識、竅門、技巧、直覺等。
實踐知識由于無法通過核心概念來表達,完全是從實踐獲得,不遵循邏輯學家的邏輯,是一種靜默的實際經驗積累,是一種親身體驗的知識(bodily knowledge)或者背景知識(background knowledge),因此具有地方性(local)、具體性,無法總結出適用于一般的規律。由表象知識抽象而來的概念往往只告訴人們完工的成品(opus operatum)而沒有告訴人們實際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它往往以犧牲具體操作的過程性知識或背景知識或實踐知識為代價。或者說,表象知識只告訴人們什么是最理性結果(結果性邏輯)、最符合某種規范(適當性邏輯)、什么是真理(爭辯性邏輯)以及完成這些成品的簡約式路徑。但沒有說明在具體的千差萬別的情形下,如何行為才能實現最佳結果,才能符合規范和獲取真理,“漏掉”了許多細節和背景。因此,人類要成功地實踐不僅需要表象知識,還必須要有實踐知識。
實踐與實踐邏輯
什么是實踐?實踐與行為(behavior)、行動(action)有什么區別?“實踐是模式化的行動,這些行動是嵌入具體組織背景中的,而且本身相互貫連成特別類型的行動,是通過學習與訓練社會性地發展出來的”。實踐與行動相比還有一個重要特點:行動在時間上是具體和有限制的,而實踐是整體的一類行動,盡管處于某一社會背景之中,但不是某次具體的行動。實踐具有五個特征。第一,實踐是一種表現(或表演performance),即一個做什么的過程;實踐只在其行動展開或過程中才存在,實踐的表現伴隨著和構成了歷史的流動。第二,實踐是模式化的行動,即在一定時空內通過相似的行動,傳遞出一種固定的社會意義。比如中國軍艦定期巡航釣魚島海域,傳遞著“宣示主權”的信息。實踐模式化并不是說實踐是嚴格重復的行動,而是存在著一定的變化與擺動。第三,實踐成功與否需要從社會意義和社會認可的意義來看。第四,實踐依賴于背景知識,實踐的過程就是同時地體現、展示和具體化背景知識的過程。第五,實踐既需要話語實踐,也需要物質手段。所以,實踐是把主觀與客觀相統一,施動者與結構相結合。與實踐知識融合在一起,既可維持穩定又能促進變化。
實踐行動的內在邏輯不同于其他行動邏輯。理性行動遵循的是結果性邏輯,認知行動遵循的是規范性邏輯,爭辯性行動遵循的是真理性邏輯,而實踐行動遵循的是實踐邏輯。布迪厄認為實踐邏輯具有四個特點。第一,實踐的邏輯不是邏輯學家的邏輯。它不僅不能用正式的公理來體現,而且由于經濟簡約性和有效的多義性而缺乏必然性邏輯的嚴格性和穩定性。雖然科學無法分析運行中的實踐邏輯,它卻是建立在一個客觀連貫的、具有生成和組織作用的心理籌劃的體系之上的。這種籌劃經常以一個不明確但卻是系統性的選擇原則來發揮作用。第二,實踐的邏輯總是有一定的時空性,在特定的時空內展示出來,不能與時空的流動分離。因此,實踐的邏輯內在地具有不可逆性和指向性。第三,實踐邏輯只有在脫離時空后才能得以感悟。第四,實踐的邏輯不能在理論上被掌握,不能通過概念來操作。
布迪厄用“慣習”、“場域”和“實踐感”三個概念來解釋實踐邏輯。首先,慣習是實踐邏輯的核心,它是塑造實踐的心理體系或結構,即“持久的、可移位的習性體系,(是)預先發揮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作用的有組織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就是過去的經歷形成習性,這種習性中蘊含著社會領域各種結構性影響的歷史沉淀,這種沉淀像一定結構一樣影響著當下人的實踐,使人在不自覺中在特定的條件下表現出某種行為模式。其次,場域是慣習發揮作用的外在的特定環境,是由三個維度形成的結構化的社會構造:權力關系、爭奪目標和視為當然的規則(taken-for-granted rules)。對歷史中形成的各類資本的控制決定了權力關系的結構和由此產生的個體地位差異。每個場域中參與者一致認同的追求目標,如政治場域的政治權威、藝術場域的藝術威望等構成了場域的競爭目標。而且每個場域都有大家視為當然的游戲規則,這是一種權力的產物,主要是象征性權力(symbolic power)的產物,或者說是一種類似于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話語權,大體是一種話語結構。最后,實踐感是慣習與場域相互發生作用所產生的適當地做什么的務實感。實踐感使得實踐邏輯相較于其他行動邏輯有一種本體上的優先性,即人們在面對直接要解決的問題時,過去的經驗/經歷往往成為行為最直接的參照,不是進行功利的盤算(結果性邏輯)、規范性思考(適當性邏輯)、相互溝通(爭辯性邏輯),而是更多地出于直覺、經驗和常識,條件反射地來行事。實踐邏輯的優先性并不表示其他行動邏輯對人們的實踐不起作用,相反它們往往是通過實踐邏輯發揮作用,事后可以在實踐中找到其他行為邏輯內含的功利、合理或規范的理由。
實踐邏輯并不意味著實踐是使現狀永遠延續下去,因為慣習是可以移位的。而慣習的移位又與場域變化有關,隨著場域的變化,舊慣習會隨之逐步變化。權力格局的變化可以說是場域變化最重要的基礎。在新的權力格局下,新興力量的出現意味著物質基礎的變化,借助物質力量,通過話語實踐形成新的行動模式,由此它們告訴人們“這就是事物的新狀態”(具體地表述一個新世界)。然而,在這種變化過程中也存在遲滯(hysteresis)現象。如果場域發生了變化,或者場域中的權力格局、規則發生了變化,而實踐者仍然按過去的慣習去實踐,就會導致遲滯現象的發生,導致個體無法適應新的場域或場域的變化,進而在工作中飽受挫折。然而,挫折與失敗也可能使人重新獲得實踐知識,進而不斷地調整個體的習性,形成正確的實踐感。
實踐邏輯與新型國際關系構建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建立。從實踐邏輯來看,新型國際關系就是要在國際社會形成一種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實踐共同體。要實現這種國家間關系的轉型,就必須依賴于實踐,即在不斷的實踐中養成各國相互交往的新慣習,在國家間互動中反復踐行、展示和具體化新型國際關系的內在理念,并逐步使這種實踐模式化。因為只有實踐形成的新模式才能形成各國交往的“可能性條件”,規約著各國的對外行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重塑各國對外交往的主觀結構,形成新的主觀認知,培養適應于新型國際關系的慣習與實踐感,使對外行為符合“常識”。因此,實踐是促使舊的國際關系向新型國際關系轉型的基礎,也是新型國際關系最有力的保障。
但從實踐邏輯的角度來看,新型國際關系必須建立在一個最重要的外部條件基礎上,即場域的變化。當今國際關系場域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西方大國的權力地位發生了重大衰落,舊世界秩序范式已經造成了世界性動蕩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失序與危機;第二,相互依存的現實使得僅憑少數大國的力量無法左右許多領域的國際事務,必須借助各國的力量特別是新興大國的力量來共同應對問題;第三,美國反復無常的政策和行動破壞了過去慣習的實踐模式以及國際規則,極大地動搖了國際社會原有的共同預期。然而,這種場域的變化并不能自動生成新的秩序,必須通過重新學習和實踐來克服慣習的遲滯。由于過去長期的實踐,在新歷史變局下,許多國家尚沒有適應新的場域變化,沒有做好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的準備。因此,克服慣習遲滯,加速新慣習形成,必須依賴于新實踐。
新實踐的模式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長期的學習與訓練的過程。因此,在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的過程中有效的實踐才是建設的保障,這種有效的實踐應當體現兩個特點。第一,必須有效地傳達相應的社會意義。即在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建立的過程中,倡導國在對外交往中不斷反復且有效地展示、演繹與具體化新型國際關系的三個內涵:彼此充分尊重對方的主權和核心利益;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弘揚公平正義;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堅持合作共贏。只有通過有效的(competent)、長期的有社會意義的實踐才能從現實中宣示:“這樣做就符合新型國際關系含義。”第二,獲得國際社會認可,即贏得“觀眾”。在與一些國家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表演”過程,當作為“觀眾”的國家用你的“表演”闡釋的社會意義(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來衡量其他國家的對外行動時,就意味著已經成功地贏得了“觀眾”。成功的有效性實踐傳遞的社會意義在于不斷的反復行動過程中贏得各國的認同,作為觀眾它們又會反過來以此評價國際實踐,并形成了一個國際性的主觀結構;這種結構不斷地強化著國家對這一結構的內化(通過行動不斷地再現結構),促使舊慣習的轉型和新慣習的形成。
“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推動新型國際關系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實踐平臺具有重要意義,其實踐的好壞影響著整個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成敗。然而,“一帶一路”國家由于其獨特的文化、外交傳統、利益追求以及浸淫于舊國際秩序程度的差異,都有自己傳統的外交實踐知識,其慣習的轉型也存在巨大差異,不可能適用于一個統一的量化標準。在促進各國獨特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知識界和外交界的任務應當是不同的。就知識界而言,應當是向有關方面(如駐當地的使節、中資企業)提供感悟其實踐知識的歷史素材(語境)。通過歷史研究與歷史故事的敘述,提示產生實踐知識的具體語境,讓外交官們更好地去感悟(當然這個感悟也需要外交官們接觸當地社會)有關國家對外行為的實踐知識。這是實踐知識的特點所決定的。就外交界而言,最主要的實踐者是外交官與走出去的企業家。實踐者首先需要對客觀環境和自身使命有正確的把握,具備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才能學習與內化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社會含義。另外,至少要在以下四個方面下功夫:融入當地,多了解當地社會;學習歷史知識,知曉當地的歷史文化;借鑒案例,豐富閱歷;多打交道,積累經驗。通過不斷的學習與訓練去感悟與養成實踐智慧,培養踐行新型國際關系的慣習。
結語
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是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新型國際關系是一個重塑國際關系話語結構的偉大愿景,實現這一愿景必須通過實踐來完成。實踐是以實踐知識引導的賦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實踐知識與智慧只能通過不斷的學習與訓練來獲得。這種知識是一種脫離了實踐就無法連貫說明的知識,它是一種外部主觀結構內化的產物,是實踐者慣習養成的基礎;慣習可以使實踐者具有一種在場的實踐感,這種實踐感是對場域權力結構與規則的正確而恰當的把握。實踐邏輯體現了一種對理性、規范與真理等主觀結構更深沉的洞悉與領悟,它是結構“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映射。因此,實踐邏輯較其他行為邏輯具有一種本體的優先性,這種優先性反映在不自覺地踐行著內化的話語結構。同時,由于這種內化,也會在場域變化后產生一種慣習的遲滯現象。
通過實踐來促進新型國際關系的實現,就是要通過實踐的行動來重新塑造各國相互交往的慣習。目前,由于國際關系力量格局的變化、相互依存的不斷加深以及美國政策的反復無常,國際關系場域的變化成為可能。關鍵是通過實踐來克服舊秩序影響導致的慣習遲滯。中國實踐者要實現慣習轉型需要實踐智慧,需要具有正確的實踐感,而正確的實踐感依賴于正確的歷史感、大局感和角色感。因為這種實踐智慧的獲得不是表征知識可以提供的,必須通過學習歷史、研究世情和國情來感悟。為此,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者需要為中國實踐者提供的知識是一種理解背景的素材,領悟慣習養成的語境分析,或者是對國際關系場域變化的正確評估。因此,基于歷史研究的國際關系研究應當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而那些基于統計量化的研究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測量慣習轉型的參考(如果可能的話),不能作為一種普遍的經驗,不分地域和國籍地套用。這是由實踐知識的地方性和特殊性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