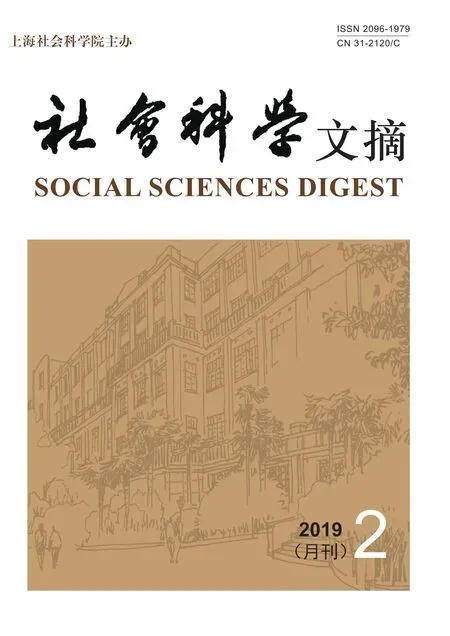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理論影響因素分析
引言
2019年中國開始實施有專項附加扣除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關于個稅改革方案的選擇的爭議反映人們對個稅理論認識的差異。近年來,關于個稅改革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不同作者分別從自己的視角探討中國個稅制的改革方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個稅改革設想。近年來,一些從稅收基礎理論視角研究個稅改革研究文獻也值得重視。總體而言,個稅改革的理論基礎研究相對較為滯后,有些屬于常識層面的專業基礎理論尚未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個稅改革共識的形成。基于此,本文擬分析個稅改革的理論影響因素,并探討未來中國個稅改革的相關現實問題。
個人所得稅的計稅依據的基本原理
(一)對個人收入扣除成本費用之后的所得課稅
個人所得稅依據個人納稅能力征收,此即量能課稅論在個稅制度設計中的應用。任何收入的形成都需要付出成本費用。收入只有轉化為所得,才可以進行課稅。不扣除任何成本費用,就直接對毛收入額課稅,只會損害收入的可持續性,破壞未來稅源。
個人所得稅計稅依據的確定,只能先對毛收入作成本費用扣除。從理論上說,所有為取得收入所產生的成本費用所應扣除。個體差異決定了這樣的設想不可行。征稅機構無法深入個體內部,找到差異因素,只能對成本費用作一刀切的統一處理。工資、薪金所得需扣除多少成本費用,爭議就很大。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給出自己心目中的免征額。
對于工資薪金所得,免征額對應的是個人(家庭)的基本生活費用。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工資至少應能滿足個人和家庭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工資應能反映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個人勞動時間的差異,肯定會讓個人對工資水平高低有不同的理解。但工資決定的基本原理沒有改變。基本生活費用至少對應衣食住行的基本費用。不同時期,衣食住行的費用支出占比大不相同。在當今的城市中國,多數人居住費用占比最高。如果居住費用問題可通過住房貸款利息支出或租金支出扣除解決,那么免征額只要反映居住之外的基本生活費用即可。
(二)基本生活費用扣除標準的爭議
2018年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每年綜合所得扣除6萬元(合每月5000元)有爭議,就是多數人考慮到居住費用因素所致。如果6萬元對應的是非居住類基本生活費用,那么爭議就會大幅減少。若2011年9月份每月扣除3500元合理,則如今5000元免征額也是合理的。如果基本生活費用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調整,那么3500元無論如何都難以調整到5000元。2011—2017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以上年為100)分別是105.4、102.6、102.6、102.0、101.4、102.0,2018年前8個月的CPI也相對穩定,最高的2月份為102.9,其他的多在102左右。如果只考慮CPI變動,每月5000元的免征額有一定的前瞻性。當然,CPI指標是否能全面真正反映物價漲幅,也有爭議。無論如何,免征額應反映基本生活費用。CPI肯定需要動態調整,但這是否應有自動調整機制,也有爭議。支持者聲稱自動調整可以更好地體現個人所得稅的公平功能;反對者認為調整可以通過法律修改,同時審視個人所得稅制的其他問題。
專項附加扣除的理論基礎及中國方案
(一)專項附加扣除的理論基礎
專項附加扣除更有針對性,可以直接促進特定民生問題的解決,但爭議也不少。反對者認為,這令個人所得稅制更復雜,留下更多稅收漏洞。在現代社會中,專項附加扣除往往直接面對民生項目,政治上易得到支持。
現在的問題是,在個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比例較低的情況下,專項附加扣除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民生問題的解決?公共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的是一整套政策工具體系。國際稅收競爭以及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改善,導致用個稅來促進社會公平的做法越來越不流行。利用專項附加扣除實現社會公平目標,需要統籌規劃。如果養老保障制度已經足夠健全,那么贍養老人支出扣除就完全沒有必要;如果繼續教育在個人所服務的機構已做得很好,那么相應的支出扣除也沒有必要;義務教育、子女撫養的社會福利已足夠好,相應的支出扣除也沒必要。社會各界對住房相關支出扣除的高期待,反映的是住房領域的其他公共政策工具尚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現實。問題是,其他公共政策工具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個稅就可以做到嗎?為此,需從理論上澄清,專項附加扣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個人,而無法代替個人自身的努力。例如,住房價格和個人收入之比嚴重不合理,就意味著如果住房貸款利息全部扣除,不少人最終都不用負擔個稅。因此,支出比例或金額封頂勢必成為具體稅制設計必須考慮的問題。
(二)考慮現實的專項附加扣除制度設計
專項附加扣除制度要做好,必須有適當的稅收征管制度配套。否則,專項附加扣除只會帶來新的不公平。在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推出之后,越來越多的個人需要自行納稅申報,且不少人需要退稅或補稅。
自行納稅申報不能免除收入支付者作為扣繳義務人代扣代繳的義務。專項附加扣除環節前置,可最大限度地減輕個人的負擔。專項附加扣除在平時可能很難處理到位,相當部分工作需要等到年度結束之后的匯算清繳期才能進行。專項附加扣除往往涉及較多的個人信息。這些信息,或由個人申報,或由有關部門和機構提供。即使相關部門和機構積極配合提供,稅務部門在信息收集之后,還要加以處理。各類專項附加扣除的落實,都要求自然人稅收征管體系的盡快健全。
專項附加扣除制度要真正造福有扣除需求的個人,還應優化扣除程序。在綜合所得與分類所得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下,補稅退稅將成為家常便飯。不少人的申報工作需要稅務師、會計師、律師等專業人員的幫助,稅收遵從成本從而增加。為此,根據不同的所得水平,可設計兩種申報方式:一是簡單的標準專項附加扣除,二是較具體的專項附加扣除。前者設定標準扣除的金額,直接扣除即可。后者則需分門別類,一一計算專項附加扣除。后者也有一定的優化空間,如子女教育可以年齡和人頭為依據,直接給出每名子女的扣除金額,而不必要求出示發票才能扣除。總之,專項附加扣除金額較低者可采用標準扣除方式,需分項扣除的申報程序也應盡量簡化,能不通過發票佐證的就應盡量不要求,以最大限度方便個人。個人提供的信息應盡量采納,除非得到舉報。這樣的信息處理原則切合個人(家庭)基礎信息不夠健全的現實,可以讓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更方便造福個人(家庭)。總之,專項附加扣除制度的設計應盡量簡單化和標準化。
實物收入和現金收入的公平課稅理論
(一)實物收入課稅的公平理由
從納稅能力來看,同樣收入水平,無論是現金收入,還是實物收入,都應平等對待。否則,實物收入不納稅或少納稅,現金收入就可能轉化為實物收入,從而不利于稅收征管。當然,現實中的一些小額實物福利,應該免稅。中國也有必要引入這樣的制度。小額福利免稅對稅收收入影響微乎其微,且可以讓個稅更人性。
實物收入最大的不公平來自住房分配制度。有機會得到福利住房的個人,與只能購買商品房居住的個人,即使后者現金收入更高,福利狀況也不見得比前者好。房價居高不下,后者就需要將收入中的大多數,甚至還要舉債,才可能買到商品房。福利分房得到的住房,即使在出售出租上有限制,也可以折算成現金收入。在現實中,福利分房不算個人收入,不用納稅。如果連代表實際支付能力大幅提升的福利房都不能折算為現金收入,那么所得稅的公平功能肯定要大打折扣。
(二)住房福利轉化為收入課稅的可行性問題
福利房轉化為收入課稅的前提條件是獲得住房的個人有稅收支付能力。有機會獲得福利房的多為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福利房地段可能較好,折算成現金,就是一大筆收入。要為這樣的大筆收入付稅,要求個人有更高的工資水平。從計劃經濟時代演變過來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雖有變化,但工資的“零花錢”屬性還在。住房部分的收入即使在工資單上體現為購房補助和提租補助,與房價相比,也只是毛毛雨,且補助標準已多年未調整。因此,缺乏個人收入基礎,福利房轉化為現金收入再課稅不可行。但是,個人收入的稅收公平待遇問題必須解決。可行的方案無非是讓沒有機會得到福利住房的個人有相應的等額住房費用扣除。住房貸款利息支出或住房租金支出專項扣除,提供了合理的機會。關鍵是要讓扣除水平能與福利住房所代表的收入水平大致相當。從公平的視角來看,那些已還清貸款或者全款購買商品房居住的個人,也應有同樣的費用扣除機會。
(三)實物福利收入問題的統籌處理
實物福利不僅表現在住房福利上。公車改革之后,不少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取消班車接送,但與此同時,班車接送成為新興行業的諸多公司的標配。而且,過了班車接送時間,還可以打車報銷。這類公司內部通常有很好的免費餐飲及其他福利提供。這同樣也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問題。
實物收入的爭議說明個稅在具體征管操作中,需要適當的配套措施。公平的個稅需要公平地面對各種收入。實物收入不僅指福利收入,各種遺贈同樣包括在其中。遺產稅和贈與稅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相關的稅收公平問題。但對于未開征此類稅的國家來說,類似問題并未得到解決。具體稅收制度的設計常遇現實挑戰。在國際上,遺產稅和贈與稅越來越不流行,即使不取消這種稅,稅率下調、免征額提高等各類減輕稅負的措施紛紛出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個人財富觀的變化,老一輩不想將過多的財富留給年輕一輩,年輕一輩也想憑借自己努力獲得財富而不是“不勞而獲”。這樣,遺贈稅所要促進的社會公平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動完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不能被侵蝕。這樣,并非所有可以增加個人納稅能力的收入都應列為應納稅所得額。是否列入,需要服從市場經濟更高的要求。
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政治哲學和最優稅收理論基礎
(一)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政治哲學基礎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是個人,收入水平高的個人多納稅,這樣的稅與公平有著天然的聯系。富人多納稅,這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富人為什么要多納稅?純粹的公平理由能成立嗎?
20個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兩位哲學教授的爭論至今仍有廣泛影響。先是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于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主張一個社會的福利狀況取決于這個社會處境最差的人,因此需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當今世界各地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線,都可以從羅爾斯那里得到支持。幫助處境最差的人,就得對處境好的人多征稅。羅爾斯假定由于存在“無知的面紗”,每個人都看不清楚自己的未來,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每個人都要考慮萬一自己處境變慘的情形,這樣,分配就有了正義性。
同是哈佛大學教授的諾齊克(John Bordley Rawls,1938—2002)于1974年出版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觀點截然相反,主張只要一個人財產的持有是正義的,沒有人可以拿走他的財產。現實雖然更偏向羅爾斯,但是諾齊克的理論也沒有因此失去意義,在公平正義理論中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個稅如何促進公平正義的討論,自然不能擺脫羅爾斯和諾齊克的影響。
羅爾斯沒有說明應該從收入多的個人那里拿走多少。在缺乏嚴格證明的條件下,不少人只是原則上認為收入越高的個人應繳納更高比例的稅,于是超額累進稅率就成為個人稅制度的標配,但現實對高稅率作出強有力的回應,勞動供給往往因此下降。未來個稅改革,必須重視公平理論的影響。
(二)最優稅收理論對個人所得稅稅率的影響
在20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1936—2018)想用數學方法證明累進稅制是對的,但最后的結論是稅率先升后降,最后一個單位收入的稅率為零,即稅率曲線是“倒U型”的。理論雖未成現實,但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的下調在1986年美國稅制改革之后就變成現實。為什么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個人最高收入應適用零稅率呢?答案是:稅率太高,個人可能不愿意干活,從而導致稅源萎縮;個人沒有收入,所得稅也就沒得征。與其如此,不如大幅降低稅率。這樣,即使最高邊際稅率不能為零,也應大幅下調最高邊際稅率,并相應下調其他各檔稅率。
在莫里斯之前,個稅是否應該適用累進所得稅制早就有爭議。累進所得稅制最終所導致每個人的稅后收入一樣。平均收入的做法,在多數情況下不能為人們所接受,“均富”可能變成了“均貧”。累進課稅與受益課稅理論也有一定矛盾。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認為,由于財產保護存在規模經濟,累退課稅才是公平的。當然,多數人不接受這樣的理論。
個稅改革應基于什么樣的公平觀,受制于經濟社會環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和剛剛擺脫貧困條件下的可接受的個人稅制度肯定不一樣。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勞動成為第一需要,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可能就會大大淡化,而且到那時政府籌集收入的方式可能還會變化。剛剛脫貧的發展階段,意味著財富對于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過多地調節個人收入,肯定會影響人們創造財富的熱情。觀念的轉變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一個社會認同“富人的存在是窮人存在的理由”時,所得出的政策含義肯定是“吃大戶”,讓富人不富。顯然,這不是事實。合法致富的個人可能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帶來更多的投資機會,而這更準確的表述就變成“富人的存在讓更多人共同富裕成為可能”。
聯系到現實,綜合所得適用的最高稅率亟待下調。考慮到個人所得稅制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營商環境改善的需要,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再固守已堅守1980年確定的45%最高邊際稅率。高稅率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能用來幫助中低收入者的稅收收入因此減少。結果只會是那些希望強化收入再分配者所不想看到的。事實上,關于如何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解決收入差距通過面向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性支出效果更為顯著。
結語
作為個人所得稅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專項附加扣除一方面令人期待,另一方面也蘊含著諸多稅收征管上的挑戰。設計良好的個人所得稅制必須適應稅收征管實際情況,否則最終結果可能事與愿違。個人所得稅改革是中國稅收制度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改革順利進行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國稅制現代化的進程。關注理論對個稅改革的影響,可以讓改革少走彎路,畢竟理論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借鑒制度是借鑒,應用理論同樣是借鑒。立足國情,個稅改革將更適合中國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