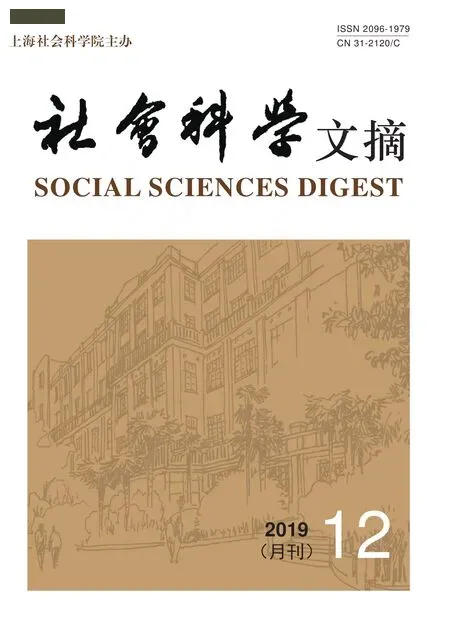與國家命運共振:70年中國政治學的蜿蜒綿亙
文/任劍濤
從歷史進程上看,70年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經過了五個階段:建國初期在政治升格中的學術降格,20世紀60年代的點式重建,80年代的急起補課,八九十年代的蓬勃發展,跨世紀以來的學科重組。以此可見,中國政治學與同一時段動人心魄的國家命運是處在共振狀態的。政治學屬于實踐知識,它與國家命運的共振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中國政治學在中國國家命運劇烈變化之際的學術呈現似乎尤其曲折離奇。在中國堅韌的現代化嘗試中,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的復雜互動史,值得深沉回味與深入探視。這不僅是鑒往知來的歷史興味使然,也是尋求中國更為順暢的現代之路的當下關懷所致。
升格與降格
1949年是一個具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年份。“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法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法對1949年成立的國家基本性質做出的政治規定基點上,人們完全可以理解新政權所展開的雷霆般的政治組合拳。“新中國”成立以后,必須借助政治運動以穩定國內政權,依靠政治同盟強化國際陣線。“盡管社會主義改造的后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四九年畢竟已根本不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它使全國的各項工作得以在一個新的制度基礎上前進。”
由上可見,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是一個政治顯著升格的年份,也是一個由政治力量驅動的嶄新國家體制。在一個國家的諸社會構成要素中,政治的升格,必然意味著其他社會要素的降格:經濟發展是政治布局的成果,社會重組是政治謀劃的產物,文教變化是政治變遷的結果。如果說1949年以后的中國確實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變局意義的事件,僅從中國政治學的重大調整來看,完全可以得到一個局部的準確印證。
中國政治學的重大調整,是中國教育結構性調整的一個組成部分。前述國家結構的決定性變化,為之確定了基本方向和大致框架。教育政策上的重大轉向則構成這一變化的直接動因: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講,必須以新的執政黨性質與國家性質作為教育結構性改革的政治指南。因此,終結1949年以前的教育機制,開啟全新的、由政治絕對主導的新機制,就是國家轉向的題中應有之義。1952年實施的大規模院系調整,就發揮出這兩種相倚的政治效用。院系調整是一個復雜的歷史故事,需要專門講述。僅從政治學退出大學舞臺來看,就可以知曉中國大學確實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
從大學院系結構中退場的政治學變換形式保留了一些學術血脈:盡管它已經不再成其為一門獨立學科,但它終究靠依附于法學學科而仍存一線生機。政治學的降格本來是不符合新生國家的執政黨與國家性質規定性的,但因為執政黨-國家領袖人物認定政治學的問題遠不如政治的問題重要,而解決政治問題是政治家的專長,這必然讓政治學家顯得有些多余。因此,讓政治學降格到學術附庸的位置,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政治學初踏歸程
政治學的降格求存為時不長。從1952年院系調整到1960年,前后差不多8年時間,政治學系從中國大學體系中消失。但到1960年,由于中國所處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讓政治學有了回歸的深厚理由。
1960年代初期,政治學初踏歸程。但這時政治學的學科內容與教學研究任務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學還有較大差異。一是高度政治化的中國政治學之所以在學科建制上重回大學場域,是因為原來高度依附于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兩國政治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不再能延續這種依附關系,因此不得不另起爐灶,讓大學探究不同于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二是中國當時恢復的政治學建制,恢復的是專指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這種恢復是基于中蘇兩國之間競爭馬克思主義正統解釋權的需要,因此是一種專注于發現中蘇兩國馬克思主義差異性而不是統一性的政治理論。三是這次被恢復起來的政治學并不是泛指意義上的政治學,也就是說,“在政治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問題,諸如關于中國政治制度如何進一步完善,關于立法、行政與司法的權限及其相互關系,政府結構與體制、黨政關系、國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決策程序、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等等重大問題,均缺乏科學研究”。
起因于中蘇之間的廣泛政治爭論,政治學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初踏歸程。從中國國內來講,由于大躍進帶來的后遺癥,以及大饑荒造成的政治困局,黨內的政治形勢驟然緊張。對主政者來講,如何防止“篡黨奪權”就成為頭等大事。就國際形勢而言,尤其是從對中國影響十分廣泛而深刻的中蘇關系來看,中蘇兩黨的分歧日益加劇,以至于不得不擺上臺面一爭高下。
正是在國際政治如此特殊的處境中,政治學獲得了不同尋常的回歸契機:今天作為政治學二級學科之一的國際政治學,驟然間成為關乎國家發展、前途與命運的重要學科。
1960年代初期,中國政治學初踏歸程。這證明了政治學的學科韌性:盡管國家在誕生初期仿效蘇聯,將政治學逐出大學門墻,但國家發展中必定遭遇的政治問題,隨時隨地在召喚政治學的回歸。即便政治學僅僅是以今日所謂“二級學科”之一的國際政治學形式實現局部回歸,但政治學與國家政治發展的內在關聯性已經呈現給人們。政治學不可能被完全排斥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對政治世界的種種復雜事務完全作壁上觀。政治學前路蜿蜒,但仍能韌性綿延。
“補課”:政治學的黃金時代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緣故,剛剛踏上歸程的中國政治學,再一次陷入了低潮和步上了歧路。從最嚴格的角度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政治學”主要工作基本上屬于政治圖解,甚少學術含量。
1978年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的理論任務被提上臺面,而謀求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實際任務也橫亙在國人面前。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期間明確指出,在多談點經濟、少談點政治的大局下面,要在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急起“補課”。
20世紀80年代政治學的“補課”之功有目共睹:除開大學和各級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機構的廣泛設立之外,政治學的基礎研究與現代政治學知識的疾速引入,政治學研究釋放出的學術能量令人矚目,而政治學研究與中國政治發展進程的相互促動局面,尤其令人感到鼓舞。正如鄧小平所期待的,在致力于發展經濟學以助推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政治學的補課也應該與中國的政治發展緊密扣合起來。當中國穩步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時候,中國經濟學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一派繁榮景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收到巨大成效,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浮出水面,成為繼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的又一熱門話題。這直接催生了政治學學科的迅猛發展。自建國以來,政治學終于迎來一個黃金時代。
20世紀80年代生機勃勃的改革開放與政治學教學研究相互促進的火熱發展局面,令人印象極為深刻。在這期間,大學所設立的政治學系、國際關系系明顯增多。在研究主題上顯著多樣化。在研究成果出版方面,不僅在政治學原理方面編著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教材與不同主題的專著,而且在兩史方面(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上收獲頗豐。這些都屬于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在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外交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政治學界編輯出版了《政治學研究》《國外政治學》《政治學參考資料》等刊物,成立了中國政治學會(1980年)、加入了國際政治科學協會(1984年),并編輯出版了引人矚目的政治學叢書。政治學研究需要接著完成的任務是融入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為政治體制改革出謀劃策。正是基于這一積極互動情勢,中國政治學迎來了它在當代的黃金發展時期。
在政治學學術研究的收獲方面,這一時期主要集中于幾個方面。第一,圍繞建國后的前30年種種失誤展開反思。這類反思,一方面體現于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與發展主題上,也體現在鄧小平直接指出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對終生制、個人領導作風等問題進行了有深度和直接性的研究。第二,在共和國的政治史研究上取得了明顯進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高度關注的初步成果。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了理論清理。第三,因應于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對一些重要的政治理論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可以說,在當時的社會科學主要學科中,政治學留人以一騎絕塵之感。
政治學研究的這個黃金時代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過短暫中斷。原因眾所周知,毋庸多言。但在鄧小平南方視察講話發表以后,這個黃金時代成功接續起來。
政治學的這個黃金時代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黃金時代的說法,是一個相對于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發展積極互動的特定意義上的形容性說法,也是一個學科、學術蓬勃發展顯出一派生機與活力而不囿于知識界自娛自樂狀態的狀描,更是一個基于相鄰學科而顯現出的強大競爭力基礎上的斷言。
生機與危機
斷言中國政治學的黃金時代止于20世紀末,并不等于說中國政治學此后全無發展。倒是相反,進入21世紀,中國政治學其實取得了長足進步。
在學科、學術上講,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政治學仍可謂生機勃勃:發表學術成果之多,明顯勝于以往;成立機構之多,顯著超過此前;學術研究的方法自覺意識之強,遠非過去可比;與國際同行的深度交流之多,先前難以想象;學術身份的自認與互認,甚至可以讓政治學界驚嘆;學術研究的新增長點之多,讓政治學界有些目不暇接。這是怎樣的一種學科生機,直讓界外人士心生羨慕。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上述政治學的統計數據,有些是政治學的自我做大結果:已經成為中國最龐大學科群之一的公共管理,其機構、人員、學術成果、智庫報告等等,有相當部分被納入政治學范圍計算。尤其是不少綜合大學,由于學科建設的傳統與組織因素,政治學與公共管理處于混生狀態,彼此學科邊界不清、人員交叉使用、成果統計容有重復。其中,尤以邊界很不清晰的行政學、行政管理學與政治學的混生狀態最為顯著。無可諱言的是,當下一些綜合大學中的政治學已經處在借行政學或行政管理學之殼求生的狀態。因此,用以顯示政治學繁榮發展的一些指標的準確性與可靠性是令人存疑的。在一些全國高校排位非常靠前的著名大學中,為了保證學科評估中重點學科排位的進一步靠前,已經將不太可能靠前排位的政治學專業取消掉了。僅就政治學的學科處境而言,已經足以說明政治學的黃金時代不再。
政治學在生機之中隱然顯現的危機,問題當然主要出在政治學的自處之道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政治學的盎然生機與巨大活力相比,跨世紀之后的政治學愈來愈滿足于學術象牙塔中的自得其樂,明顯喪失了學術的實踐進取心與研究的理論雄心。因此,一種自限天地的自娛自樂使政治學喪失了實踐活水與思想動力。這是20世紀后期與21世紀初期兩個階段政治學呈現出明顯落差的主要原因。固然這與政治體制改革話題熱度的顯著下降有密切關系,但也與政治學的固步自封、自我禁足內在相關。實踐知識自我閹割了實踐針對,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這也是政治學黃金時代不再的深層原因:一個自愿從它本身應當毫無借口、無需理由挺立于政治實踐世界的學科,竟然或有意或無意地退出、甚至是拒絕進入政治生活世界,那么它的生機從何而來?又如何強力維持呢?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的積極互動狀態是否在根本上已經生變?是政治學在學科上已經出現失語而無法與生動活潑的中國政治互動了呢?還是生動活潑的中國政治實踐根本不需要政治學介入其中了呢?這是極為嚴肅且緊密相關的三個提問。對此稍加思考,可以給出三個否定性的答案。一者,今天中國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兌現的關鍵起步階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中所包含的繁多改革任務,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向中國政治學界提出了極為繁重的實踐與學理研究任務。中國政治發展與政治學需要的深沉互動,大局未改,只待政治學界的積極響應。至于中國發展展現的全球向度,在“一帶一路”倡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路中,已經得到充分呈現。政治學需要對之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除非政治學界同人攜手而為,否則就會錯過一個再次激活政治學研究巨大能量的歷史契機。
二者,中國政治學確實需要重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所謂全球化話語與本土化話語之爭、整全性知識與專門化知識之辯、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之別,都只是展現政治學研究張力的不同進路,而不是勢不兩立的排斥性取向。最為關鍵的是,中國政治學的健康發展亟需全力融入到中國的實際社會政治生活之中,即便是基于純粹知識興趣的政治學研究,也對描述一個真實的中國具有不可拒絕的幫助作用。對今天中國來講,政治學研究如同所有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必須全力避免雙失的研究局面:宏大話語的建構不足以引導國家向現代化的縱深健康發展,而微觀實證研究又完全扭曲國家的每一個局部真實。相反,應當盡一切可能追求一種雙贏的結果。
三者,今天的中國是最需要政治學為國家發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時代。誠然,中國改革開放處于深水區,執政黨與國家權力方面的頂層設計極為重要和關鍵。但相關的頂層設計,在技術上需要相關的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和管理科學的精確知識支持,在理念上則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理論證,而在實際舉措上需要所有學科的專家集群集中智慧以確保可行性與可靠性。由于國家權力方面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因此讓國家權力保持清醒理智的政治學,也就必須擔負更為重要的前引后導責任。政治學者的擔當意識、學術責任、政治勇氣、研究素養和理性精神,會極大地影響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發展的互動狀態。因此,政治學研究共同體必須制定有形的與無形的學術紀律,以求維護自己的學術尊嚴,并得到國家權力的尊重,從而為雙方的有益互動提供適宜條件。可以說,對中國政治學研究共同體來說,重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燦爛呈現過的積極實踐品格,杜絕犬儒式的媚權媚俗,是其重現輝煌的學術研究共同體自我準確定位之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