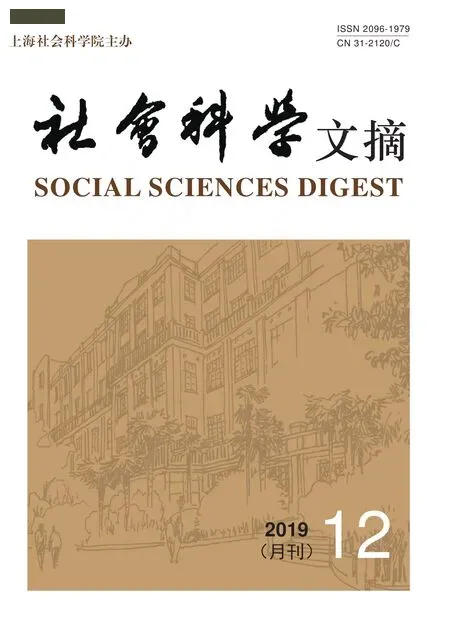鄉村治理70年: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
文/呂德文
中國是一個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國家,有悠久的鄉村治理傳統。尤其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鄉村治理體制經歷了多次變革。總結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體系,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角看,鄉村治理具有雙重性。它既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表現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又是鄉村自治能力的運用,表現為農村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
新中國鄉村治理的三種模式
近代以來,鄉村治理被納入國家政權建設的軌道,但這一進程在清末民初并不順利,一度因為國家政權建設的內卷化而產生鄉村治理危機。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通過建立基層黨組織、基層政權和各種群眾性組織,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建設。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家權力下沉。鄉村治理不再是單純的基層自治,而是服務于“權力下鄉”,農村事務被納入國家權力的監控范圍。二是規劃性變遷。鄉村治理不再是“無為而治”,農村資源的汲取、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供給等,都被納入“趕超型”國家戰略。三是制度化。鄉村治理不再主要依賴于地方性規范,而是被納入制度化軌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制度化是以官僚化和行政理性化的形式呈現出來的。隨著實踐需要,鄉村治理的制度化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著力于建立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
新中國70年的鄉村治理實踐,經歷了人民公社、鄉政村治和“三治”結合這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在治理的主體、內容和方式上,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1958年,經過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制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基層政權組織。它以汲取資源和改造基層社會為主要治理目標,塑造了政治機構的權力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的全能主義治理形態。而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意味著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而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它雖承擔著向農村汲取資源的任務,卻不再干預村莊生產和生活領域,具有鮮明的簡約治理色彩。而黨的十九大提出建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主要是服務于“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這一目標。因此,這一新的治理體系,更加注重多重治理機制的協同性。
鄉村治理變遷的軌跡
從歷史視角看,新中國的鄉村治理變遷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產物。鄉村治理處于特定的環境之中,不同區域、不同歷史時期,鄉村治理實踐也不盡相同。
具體而言,新中國鄉村治理變遷軌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治理主體的變遷。大致而言,新中國治理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變遷軌跡。在人民公社時期,鄉村治理主體比較單一,嚴重依賴于政社合一的政治機構及群眾動員機制。在“鄉政村治”模式下,鄉村治理主體逐漸多元化。一方面,基層政權的形態復雜多樣,不僅有鄉鎮黨委政府,還有由七站八所組成的數量龐大的事業單位;另一方面,村級組織也逐步多元化,村干部、黨員和村民代表成為村治主體。而在“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中,不僅鄉鎮黨委政府和村兩委是鄉村治理的主體,各類社會組織也將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二是治理內容的變遷。總體上,鄉村治理的重心逐漸從“政務”轉向“村務”。鄉村治理內容包括“政務”和“村務”兩個方面,前者指執行國家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的各項行政任務,后者指自主管理村莊公共事務。大體上,人民公社時代的鄉村治理內容,主要是服務于農業剩余的汲取,“政務”主導“村務”;在“鄉政村治”模式下,“政務”和“村務”既分而治之,又相互配合;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下,“村務”成為鄉村治理重心,大多數“政務”如民政、社保、計生等都是服務于村莊事務的,從村莊汲取資源的行政任務已經越來越少。三是治理方式的變遷。概言之,鄉村治理方式變遷具有鮮明的制度化特征。制度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鄉村治理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二是鄉村治理的制度執行能力也不斷提升。人民公社時期,鄉村治理主要依靠國家權力,尤其依賴于政治動員和基層干部的工作經驗,制度化程度比較低;而在“鄉政村治”模式下,雖然行政理性化不斷加強,但其制度執行能力較差,在很多情況下依賴于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十八大以來,鄉村治理現代化被提到議事日程,建立“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也意味著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
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機制
鄉村治理中比較成熟的治理機制主要包括兩個:
一是壓力型體制。壓力型體制是指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將這些目標分解為數量化的任務和物質化的指標體系,層層量化分解,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為了保證實現目標,一般配以目標管理責任制,重要的指標則實行“一票否決”制。在這一體制下,每一級政治組織都在這些評價體系的壓力下運行。
二是運動型治理機制。基層運動型治理是一種常規化的治理機制,它和科層制等治理結構有機結合,成為推動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這一機制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群眾工作中萌芽,成型于新中國初期的土改、剿匪等建政工作;在人民公社體制中,基層運動型治理機制得以發展,如在農業生產和興修水利等過程中,借用軍事化的管理技術,動員群眾參與“大會戰”。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群眾動員雖然不再進行,但運動型治理機制在鄉村治理中得以延續。
壓力型體制是科層體制自上而下運作的動力機制,以目標責任制為中心,促使下級有效落實上級行政意圖。運動型治理則是官僚體系內部門聯動的動力機制,以政治動員為核心,打破部門壁壘,加強部門間合作,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兩個治理機制的背景、核心制度和解決的問題雖各不相同,卻相互補充、相互支撐,構成了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機制。
當前鄉村治理面臨的挑戰
鄉村治理具有雙重功能,既是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重要手段,又是維護鄉村秩序的基礎;反過來說,鄉村治理也嵌入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結構之間,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直接影響到鄉村治理變革。本質上,鄉村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國家治理體系的調整必將影響鄉村治理實踐效果。具體而言,央地關系的調整直接影響鄉村治理實踐邏輯。
當前,央地關系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之中,需要從各個方面理順關系。同時,這也意味著,新型的央地關系并未完全建立起來。從“理順關系”的角度看,當前的鄉村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包括國家與農民關系失衡、鄉村治理內卷化,以及鄉村治理去政治化等問題。當前,如何在充分吸收新中國70年來鄉村治理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重構鄉村治理新體系,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有效應對當前鄉村治理挑戰的必由之路。
鄉村治理新體系的歷史延續與演進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的目標。我們認為,“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成果。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是在傳統的“雙軌政治”和新中國建立的鄉村治理體制和機制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也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當前,一些行之有效的鄉村治理創新正在構建“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已經成為構建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抓手。客觀上,通過黨的政治統領,發揮黨組織動員、組織群眾的優勢,是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很多地方正在借助于技術治理,不斷提高鄉村治理的規范化水平,從而將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機整合起來。概言之,當前的鄉村治理新體系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拓展鄉村治理空間的形式呈現出來的。“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是一個富有彈性的鄉村治理空間,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回應了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因此,“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并不意味著對原有治理體系的簡單替代,而是對原有治理體系的再造。
結論
鄉村治理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同歷史時期,鄉村治理所處的環境、歷史使命有所不同,導致其主體、對象、方式也不盡相同,它們之間組成的關系、結構、機制也不一樣。新中國的鄉村治理實踐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它承接了近代以來國家政權建設的任務,真正意義上完成了現代國家建構,并在此過程中為工業化和城市化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同時,它也開啟了治理現代化的歷程,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自治、法治、德治等諸多制度選擇。尤其重要的是,70年來的鄉村治理實踐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