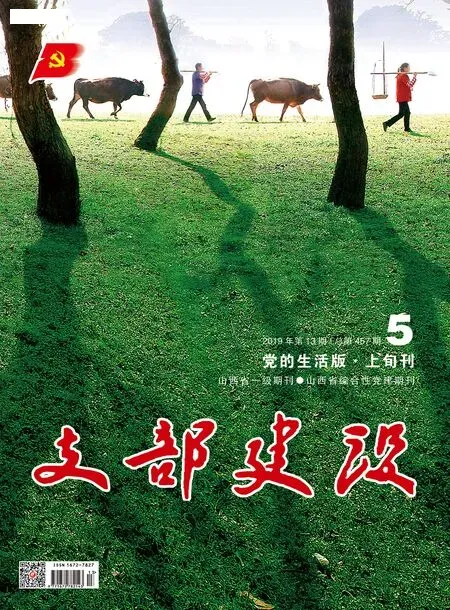黃土地的變遷
◎ 梁 冬
年近90歲的老爸,精神矍鑠,腿腳利索,記憶滿滿。他經歷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經歷過居無定所、逃荒要飯的戰亂;他見證了改革開放的兩重地,更有著豐衣足食、晚年幸福的滿足。新春,我回到芮城看望年過八旬的老父。一天早晨,我與父親漫步村外,望著奔騰不息的黃河,踩著腳下的黃土地,不知不覺來到一塊麥田。老父突然問我:你還認識這塊地嗎?我不假思索地說:“70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記。”老父揣著白胡須,不住地點著頭,我眼前卻浮現出一幕幕難忘的往事……
70年前,也是一個大地回春的日子,20歲的父親、母親拖著我,來到這塊剛分給我家的土地。我依稀記得,父親跪在地上長跪不起,兩行眼淚流在黃土地上。當時,我不了解父親這份真摯的情感,長大后才知道,為了一塊養家糊口的土地,爺爺和父親,給別人打工扛活,最終都沒有買下一畝地。解放了,人民當家作主,分到了土地,父親怎么不激動萬分、感慨萬千呢!父親雙手捧起一把黃土,喃喃地說:地是生命之本、生活之源,我們要靠你養育全家啊。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也是我們全家的希望。父親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幾畝土地上,要靠這幾畝地養育全家。但那時落后的生產力,使父親叫苦不迭。秋天把小麥播種在地里,春天常常是卡脖子旱,看著腳下滔滔奔流的黃河水,卻只能期望吝嗇的老天下幾滴雨。有時滴雨不下,父母親只能到一里外的黃河邊手提肩扛黃河水澆地,但那只是杯水車薪。播種的小麥往往連種子也收不回來,像人們常說的種一葫蘆打一瓢。即使遇到好年景,一畝小麥收成也只有一二百斤。我記得,一年生產的糧食,頂多只能吃八九個月,到三四月份,父親就要挾著口袋東借西湊,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兄妹挖野菜,拌湯喝糊糊充饑。那時盡管缺吃少穿,但一想到有了土地心里便有了幾分安慰。總是想,好生活只是剛剛開始,有共產黨的領導,土地一定能生金,我們一定能過上好日子。
1968年,我中專畢業來到部隊,1978年回到地方,盡管在外地工作,但心里一直放不下家鄉,放不下父母,放不下生我養我的土地。一次,我回到家鄉。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不久,農村正在醞釀一場大的變革。在農村當了20年村黨支部書記的父親,已經卸職,他被無休止的運動搞得疲憊不堪,想靜下心休息。當他聽說要土地下放,包產到戶,一顆對土地不抱希望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熱望。父親對我說:“我想把咱土改時分的地承包下來,我不信產量上不去。”可是我心存疑慮,20多年的集體化,又一下子回到解放時,再說土地包產到戶,群眾能同意嗎。父親看出我的心思,說:“幾十年的大鍋飯,把人心搞散了,使人變懶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你放心吧,只要分田到戶,土地就能變成金。”之后,那塊土改時分的地又讓父親承包了,果然,產量年年提高,畝產達到八九百斤,生活也像芝麻開花節節高。黃土地解決了農民的溫飽,使人們奔上了小康之路。
時光如梭。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又迎來了建國70周年。在這個明媚的春天,我與父親又一次來到這塊黃土地。父親盡管80多歲了,身骨子還硬朗,他蹲下身,拔起一縷麥苗,說:“這些年,小麥連年高產,除了科學管理、種子優化外,還有黨的好政策凝聚了人心。你看,去冬今春無雪,是50年少見的大旱,但我們不怕,有了電灌站,引上黃河水,兩天時間,這些麥田就可以澆一遍。如果沒有大的天災,畝產一千三百斤問題不大。”聽到父親這番話,我不由發出這樣的感嘆:同樣是這塊黃土地,為什么產量能從解放之初的一二百斤,包產到戶的八九百斤,到現在的一千多斤,這里面既有土地的潛力,科學技術的魅力,更有人的精氣神。然而父親的話,更是發人深省:近十年來,中央堅持科學發展觀,讓人們有幸福感、獲得感。中央連續多年出臺一號文件,刺激生產,關注民生,注入活力,取消了農業稅,這種多予少取的政策,激發了人們對土地的熱愛,對土地的投入。真正使黃土地變成金的是黨的好領導、好政策。看到眼前的一切,聽了父親這番言談,我怎能不為我們的祖國不斷富強而自豪,怎能不為我們的黨走向成熟而自豪,怎能不為我們的人民自信而自豪。站在這黃土地上,觸景生情,我以黃土地為杯,以黃河水當酒,飲歌一曲:為我們生生不息的黃土地干杯,為我們蒸蒸日上的祖國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