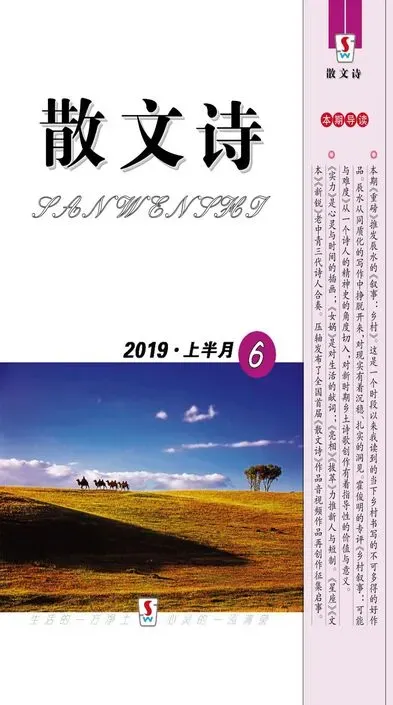鄉村敘事:可能與難度
◎霍俊明
我和辰水是同時代人,這不只是強調我們的“出生時間”,而是為了突出我們處于同一時代的生存語境和現實命運之中。辰水最初的詩歌寫作就將精神視線投注到了鄉村(安樂莊)事物和鄉野普通人物的命運上,并且多年來他一直都保持著“鄉村見證人”的精敏身份。其最新的作品《敘事:鄉村》(散文詩)我并沒有著意按照“詩歌”或“散文詩”的形態來閱讀,我只是將之視為一個當代寫作者的精神縮影和文本檔案。
就辰水的鄉村(鄉土)詩歌寫作以及《敘事:鄉村》而言,我們不得不再次關注一個自新世紀以來的寫作倫理:為什么寫作鄉村?鄉村發生了什么?“鄉村敘事”是否正在經歷著復寫的瓶頸期?
“詩人”與其他文體作家的一個重要區別即在于他具有不斷強化的“精神肖像”,他的精神生活得以在文本世界中不斷塑型。
顯然,辰水是一個詰問者和游走者,同時也是困守者和出逃者。對于鄉村倫理、人世萬象以及新舊時代的碰撞,辰水都更像是一個夜晚的失眠者和游蕩的幽靈。他也因此持有了傾聽的耳朵和眼力的可見度,甚至更像是一個鄉村的辨音師。在辰水這里,我甚至還目睹了當年魯迅筆下的那個“黑衣人”——走投無路、虛妄空誕、向死而生、長歌當哭。
顯然,辰水并不是孤立的鄉村敘事者——卑微而虔敬、冷峻而分裂、寧靜而屈辱、自責而虛妄。與他同時代的寫作者都經歷了類似的裂變過程,曾經熟悉的鄉村已經消解,煥然一新的時代已然到來。實際上,很多人都成為了過去時鄉村的懷舊者,這一回溯的眼光使得過往也蒙上了理想主義的色調——“我試著倒退著找回從前的自己”。與此同時,猝然降臨的現代城市和現代性也使得包括寫作者在內的鄉村經驗者們深感不適,各種尷尬、分裂、不滿以及懷疑就紛至沓來。顯然,作為閱讀者和批評者,我也深處這一裂變之中,和辰水一樣地感同身受。但是,我還不能在此止步。因為,詩歌和文學畢竟不同于現實生活,或者說二者是不能劃等號的。詩歌在涉及鄉村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時候對詩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詩人不只是一個觀察者和鏡像描摹者,也不能成為社會報告式的平面分析者。詩人和詩歌應該通過特殊的文字世界完成精神生活,完成對一個時段的深層經驗和內在動因的剖析和命名,甚至更為偉大的寫作者還能夠通過普世性經驗和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完成對時代的超越。也就是說,詩人不只是具有反應和傾聽能力,還應該具有過濾、變形乃至提升的能力,不僅觀察可見之物,而且對不可見之物予以發現和揭示。唯其如此,詩人也才能承擔起布羅茨基所說的“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
這不只是我對辰水的閱讀期待,甚至是對整整一代人的期待。當然,這一期待和要求顯然是在文學史的層面提出來的,而很多寫作者顯然不能對此做出完滿的應答。而辰水近期的寫作尤其是《敘事:鄉村》讓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復雜性,也就是說,鄉村敘事不是類型化和符號化的,甚至也不是倫理道德化的,而應該是在文本內部完成的更為復雜的疑問和省思。顯然,辰水正試圖對此做出個人化的努力。
辰水成了一個面對鄉村事態和命運淵藪的精神自審者。他將自己置身于懸崖地帶,在烈焰的烘烤和冰雪的淬煉中,一直敲打著自己的頭顱。詩人并不是萬能的解決難題的高手,而更多時候是問題的提出者。辰水也只能在彳亍和反復的詰問中,變成了黑夜里的希緒弗斯。
辰水既是貼近鄉村現實的剖析者、凝視者,也是形而上的游離者和語言刀鋒上的歷險者。閱讀辰水的文字,并不是一個輕松的過程。這種緊張和不安正來自于同時代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也許,詩人的責任在于黑夜中扔下一個秘密的漂流瓶,里面充塞著種種疑問。隨著時間的洪流,那個撿拾起這個漂流瓶的人也許會給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疑問以答案,也許一切都未為可知。
荷戟獨彷徨。
這句話也適應于辰水的寫作和精神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