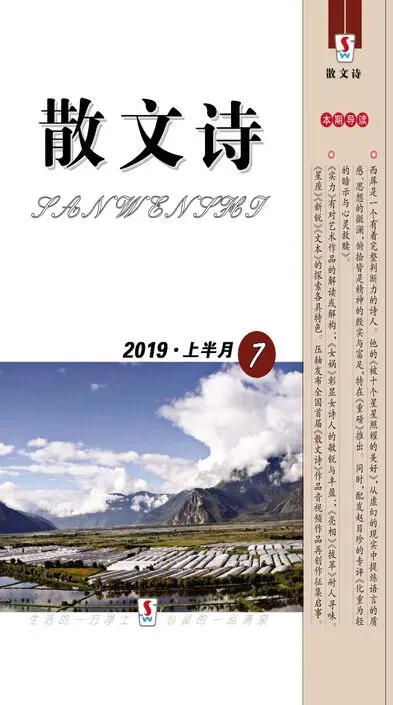化重為輕的暗示與心靈救贖
◎趙目珍
魯迅先生曾把寫“小感觸”作為自己對《野草》的自謙性評價,實際上讀過《野草》的人都能夠深刻感受到其中所蘊涵的情感力度,尤其是其中對靈魂內省的那種深度與高度,真是令后世作者難以望其項背。當然,魯迅先生創作《野草》之時有其特定的生存時代作為背景,不同時代的散文詩應該體現不同時代的散文詩特質。但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散文詩,其間有一個一直沒有間斷的寫作理路,那就是通過各種媒介的會通來實現人對心靈的救贖。
從具體的寫作實踐來看,西厙的散文詩很好地實現了這一點。盡管他表面上為我們設置了一個“被十顆星星照耀的美好”這樣的場景,但是細讀其散文詩,我們能夠發現其中所滲透著的對個人命運以至萬物命運的深沉思考。因為他所謂“被十顆星星照耀的美好”實在是個人“心底”深處的一種“生發”,而“生發”的時候,他正“努力睜著一雙病目”,并且“在十顆星星下”佇立了很久。再認真細讀《被十顆星星照耀的美好》,我們發現這其中的奧秘又不僅是寫作的背景深沉如此,作者為自己曾忽略星星而作了三種可能的假想,而這每一種假想都讓我們對人和萬物的命運產生一種形而上的思維或者洞見:“有一種可能:星星是終于荒老的宇宙鬢邊偶見的華發?/另一種可能:因為命運賜我一雙病目,星星在我的仰望中太容易遁形?”詩人所敘述和提示的這種命運意識太宏闊,也太讓人震撼。我相信這絕不僅僅是一種對仰望星空的暗示,尤其是在當下,在人類更多的情感遭受麻木或者剝離的時代,這是一種對心靈更高層次的救贖,它將我們的命運導向了一種“星空”意義上的問詰與反省。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高屋建瓴的“喚醒”,詩人在對于散文詩的各種“播撒”中都一以貫之地保持著其“終端所指”,那就是詩人處處以“經驗與自然”的合流在實現著對于個體或者人類靈魂的救贖。比如其《另一棵槭樹》,敘述中就直接點出了槭樹“豐富的救贖之光帶來治愈的安寧”的人生啟示;《與河流一起散步》則指出,庸常之輩在孤獨的散步中,河流提供了陪伴,同時“提供了思的可能性”;《悲喜》指出,人間悲喜“常附麗于櫻花的開落”“櫻花因此而有了不堪承受之重”;《偶得》則借對“白玉蘭的盛景”的思考,領悟出人生與花的命運相似的哲理;《閑章句》借由“閑”談說出“愛恨自便,悲喜自便,生死自便”的人生意義;《人們愛雪,是人們覺得雪是善的》到最后也點明“救贖”的用意:“這一丁點雪意和孩子氣,恰是人們終獲救贖的本質起點。”而《在油汀旁想起火爐》比起《閑章句》來更寫出了人生的一種閑適:“更多時候我都不用語言,不用表情,也不用手勢,只是用打盹,就能和它談到午夜。它兀自噼啪作響,像一個最負責的看護人,是那么健談。”應該說,在各種明朗、有效的人生意義退居生存真相之外的今天,西厙的散文詩透過對物——人關系的思考恢復了被遮蔽良久的世界關系本身,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義。
西厙散文詩的這種成功很顯然與其對散文詩的建構方式有關。其散文詩常用的生成方式,即“知覺某物”—“體味某物”—“思想某物”。所謂“知覺某物”即詩人以外在的某物為觸發點來實現自己的情感著力,以其具體的寫作來看,詩人所觸即有星星、槭樹、河流、櫻花、白玉蘭、雪、油汀等物。所謂“體味某物”即詩人借由事物入手來實現自己對事物的進一步或者深層認知,很顯然,這一步是為“思想某物”做鋪墊的。以《另一棵槭樹》來看,詩人寫了院子里有六七棵槭樹之后,便指出“這些槭樹仿佛各有稟賦”,并通過它們“顏色”的不一致來點出他所要指示的“另一棵”。所謂“思想某物”即詩人借由“體味某物”進而對該事物進行思考,并由此貫穿起物與人的深層內在關系,或建構起其所隱喻的理想精神世界。以《與河流一起散步》來看,詩人在體味到“中年散步,沒有比河流更相宜的伙伴”等人生經驗之后,便進一步思考了河流與人生的永恒聯系:“是啊,與河為伴的無一不是孤獨的散步者,無一不是孤魂。”至此,詩人要在散文詩中所彰顯的“孤獨”主題便也裸裎出來了,散文詩的精神也隨之得以凸顯。不過,如果在閱讀中我們不深入詩人的情感脈絡,我們很容易被美感所迷惑。在詩中,詩人常常借用花朵、河流、星星、槭樹等美好的意象來實現詩的審美構成,而美感的生效常常掩藏至少遮蔽“思想”的巨大意義。其實認真思考詩人所要表達的主題,我們就會發現,詩人采取的是一種“化重為輕”的暗示。這也是我們最后需要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