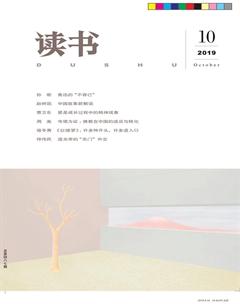闡釋與建構
耿文婷
美學應該如何發展?對于當代美學家們來說,是一個都要思考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學界,美學仍然保持著相當的熱度,其標志在于流派紛呈。除對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實踐美學的紹述與批評,還有以楊春時為代表的后實踐美學,以潘知常為代表的生命美學,以劉悅笛為代表的生活美學,以王曉華為代表的身體美學……當然,還有其他若干美學理論旗幟的張目。這些美學流派,表征著中國美學的發展與繁盛,在世界范圍內也是蔚為大觀的。
涉及中國美學思想史的梳理與整合,近年來也是頗有實績可彰的。在李澤厚、劉綱紀兩位合著的《中國美學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之后,最近若干年有張法的《中國美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葉朗、朱良志兩位主編的《中國美學通史》(八卷本,江蘇人民出版社版),曾繁仁主編的《中國美育思想通史》(十卷本,山東人民出版社版),朱志榮主編的《中國審美意識通史》(八卷本,人民出版社版),以及祁志祥以一人之力獨撰的《中國美學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這些美學史著作的問世,同樣彰顯了中國學界對于美學研究的最新水準,也都體現了作者的美學史觀。
從學理層面如何提升中國美學?尤其是:如何立足于本土的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創作與批評的文獻資源,熔煉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范疇或命題?我感到,以多元化的思維來看當下的美學研究,或許可以發現具有示范意義的途徑。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對于學者思維方式的解縛,應該是最為重要的收獲之一。美學研究的多元化,使許多卓有建樹的美學成果破土而出。近來讀到張晶教授的六卷本學術文選《美學與詩學》,對于美學研究的路徑與當下理論價值,有了新的體認。這六卷文選,內容相當豐富,涉及美學、文藝學及中國古代文學、文論和當代審美文化,其中體現出來的思想力量和創構銳度,貫穿于其各個領域的論著之中。
因為專業的緣故,我對此書的關注點,更多的還是在美學和文藝學方面。張晶扎扎實實地建構起自己的美學理論,而這些美學理論,又多是以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理論資源作為根基和內核,同時,又以西方的哲學、美學等相關思想作為參照,從而生發出具有當代美學理論價值與現實指向的話語。第二卷中收入的《神思:藝術的精靈》,第三卷中的《審美感興論》《審美驚奇論》《審美回憶論》《論審美享受》《論審美抽象》《中國古代詩學中“偶然”論的審美價值意義》,以及第四卷、第六卷中的許多文章,都有這樣的理論性質。都是將闡釋與建構有機結合,使之成為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強勁邏輯力量的美學理論范疇或命題。
我所說的闡釋,不是一般的訓詁釋義。訓詁釋義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且是專門的術業。這也是闡釋的前提。闡釋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真正的闡釋是在原典的理解與解釋中生發出新義,如《十三經注疏》就已經是在進行闡釋。再如魏晉時期著名玄學家王弼,就是通過《周易略例》《老子注》來闡明其“貴無”的玄學本體觀。朱熹的《四書集注》,也是通過對“四書”的闡釋來表達他的理學思想體系。闡釋又是與建構并行不悖的。在闡釋中建構,這是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的治學方法。魏晉時期玄學家郭象的《莊子注》,在這方面是最為典型的。在對莊子各章的闡釋中,郭象建構了他的“獨化”論的玄學思想體系。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也都是以對先秦儒家經典的闡釋來建構其理學學說的,如他們的“萬物一體”思想,都是在對孔子、孟子“仁”的觀念的闡釋中予以貫通的,且賦予了新的內涵。清代思想家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通過對《孟子》的字義疏證闡釋,表達了自己的反理學的思想。
張晶的美學研究,正是以闡釋與建構并行的方法進行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文獻多半處于自在狀態,對于某一范疇,人們往往并不進行義界的厘清和邏輯的梳理,而是直接運用。盡管其基本的內涵是相近的,但每一位文論家使用時的語境及涵義,往往有很大差異。第二卷中收入的《神思:藝術的精靈》一書,頗為鮮明地體現出闡釋與建構并行的方法論特征。張晶是在其他研究者對于“神思”的闡釋基礎上,加以辨析并提出自己的界定,認為“神思”是藝術創作思維的根本范疇,包含了想象、靈感構思等多種思維元素。該書的其他章節,則是揭示與闡發“神思”所蘊含的各種審美的內涵,如第二章“神思的感興發生機制”、第三章“神思的虛靜審美心態”、第五章“神思與審美意象”、第七章“神思與審美情感”、第八章“神思的藝術直覺與審美理性”、第九章“神思與作家的主體因素,等等。由這些內容不難看出,《神思:藝術的精靈》這部美學著作,對“神思”作為《文心雕龍》創作論的核心篇章,在闡釋的基礎上做了美學層面的全面建構。
這樣的闡釋與建構,體現在該書諸多審美范疇或命題的研究中。有些是明顯具有中國美學色彩的,如“審美感興論”“審美靜觀論”“審美物化論”“審美化境論”等;有些則是作為美學的基本范疇加以建構的,如“審美驚奇論”“審美回憶論”“藝術媒介論”“論審美抽象”“論審美享受”“論審美構形能力”“審美境界與道德境界”“審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等,都是從學理層面,對于一些重要的審美現象進行熔煉與提升,這些都是以往的美學理論序列中未曾有過的。對于那些具有中國美學色彩的范疇,作者是在對諸多相關文獻的闡釋中將其提升到普遍美學意義的層面,使本來處在較為局部的、感性狀態的范疇,升華到具有美學學理性和現代性的層面。
闡釋與建構,可以是一體兩面的。遍觀中國思想史、美學史,“通”與“變”之間多是通過闡釋與建構實現的。沒有建構的闡釋,是缺少思想歸趨的;而不是建立在闡釋基礎上的建構,則是缺少根基的,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當代的一些美學文藝學研究名著,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王運熙、顧易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葉朗的《中國美學史大綱》,葛路的《中國古代畫論體系》等,都是闡釋與建構互動的產物。
對于當代中國的美學理論發展來說,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美學理論不可能不借鑒西方的哲學美學理論系統,這是不言自明的;但中國美學又有數千年的文藝理論作為基礎,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色。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如何才能成為當代美學發展的資源?所謂“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的具體路徑何在?我以為,闡釋與建構的辯證運用,應該是值得倡導的思維方式。張晶在這方面是有著自覺的理念和成熟的想法的,在他的文選中,探求這種路徑的文章成為作者的理論追求坐標。如:《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審美關系的特征》《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及其實現》《中國古代詩論的美學品性及美學學理建構意義》《中國古代論詩詩的理論特質》《中介的尋求與打通:古代文論進入當代文藝學之途徑》等,都體現了這種理論自覺。
前些年在古代文論領域有所謂“失語癥”之說,后來又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討論,在我看來,也許這都是來自學界內部的一種焦慮。當代的學界有很多時新的話語,對傳統的文論和美學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古代文論或美學似乎大多數情形下都在自說自話,而缺乏對當代美學和藝術理論的影響力。讀張晶的美學論著,他在談論古代美學的話題時,總使人感到現實的關切;而在建構具有美學普遍價值的問題時,又使人感到傳統的深厚和立足的堅實。其實,在當代,經過二十世紀哲學美學的長足發展,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豐富的美學蘊含,還有從其中可以生長的新的理論要素,才能更充分地得以發顯。黑格爾所說的“密納發的貓頭鷹”,恰恰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對于當代的審美文化,張晶十分關注并有大量的論著,試讀一下第六卷中《圖像的審美價值考察》《審美文化的歷史機遇》《審美文化視域中的國學內涵》《日常生活作為藝術創作審美感興的觸媒》《文藝美學的當代建構及其意義》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就可以感受到他對當下文化和藝術問題的密切關注。
當然,我在閱讀這套書感到在理論上非常“過癮”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夠滿足的遺憾,那就是在這些得到深入的闡釋與建構的范疇之間,整體的聯系是未曾看到的,也許,《美學與詩學》的缺憾也就在于此。然而,張晶在他的“學術文選”中所運用的基本研究路數——闡釋與建構,對于當代美學來說,確乎是一條篤實的、“靠譜”的研究之路!這其實早已為許多學者的研究所證實,但張晶的研究所顯露出來的,是在古代文獻和當代美學之間的“無縫對接”,使中國文藝理論呈現出更強烈的現代意味。
[《美學與詩學——張晶學術文選》(六卷),張晶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