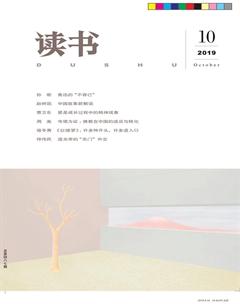荊軻刺秦王:幸好是插曲
裴登峰
在我國歷史上,荊軻刺秦王,堪稱大事,家喻戶曉。人們言及荊軻,腦海中自然會浮現出燕太子丹率眾賓客與其訣別的慷慨悲歌場面。《戰國策·燕策三》這樣描寫: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嗔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人們對此津津樂道,夸張渲染,甚至演繹出了帶有荒誕色彩的故事。司馬遷曾感慨:“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荊軻論》五篇”。自注:“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其文已佚。后來吟詠其人其事,成為歷代文學作品中的題材。人們大多持欣賞、肯定態度。對荊軻未完成刺秦“驚天偉業”,心存遺憾,感慨良多。荊軻也被涂抹了“悲情英雄”色彩,成了壯志未酬的“遺憾者”的代名詞。
但事實上,荊軻是被“逼”出來的豪杰,其行為是“不得已而為之”。戰國三大刺客,豫讓為了報答“知伯以國士遇臣”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殺趙襄子,體現“士為知己者死”的執著信念。聶政深感“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他為了回報韓國權臣嚴遂“看得起自己”的厚遇,覺得“應該”去刺殺韓傀。雖是被嚴遂利用,無關乎“正義”,但聶政卻是出于自愿。豫讓與聶政,都體現著一定程度的俠義精神。荊軻的行為動機,與他們不可同日而語。
起初,荊軻由衛至燕,“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后來好友田光告訴他,已在燕太子丹面前,舉薦他去“圖國事”。在田光自殺以激將后,“荊軻遂見太子”。雖然“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苦勸,但荊軻開始并不情愿,不為所動。“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于是,“太子丹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后許諾”。這實際上是強人所難,強加于人,非荊軻本意。即便如此,“久之,荊軻未有行意”。面對一再催促,“荊軻怒叱太子曰:‘……仆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訣矣!遂發”。荊軻明知此去必死,但若不去,太子丹也不會放過他。兩者結果相同,索性不如刺秦王而死。荊軻是被逼無奈,走投無路,身不由己才去刺秦王。談不上重義輕生、反抗暴秦、勇于犧牲,并非充滿豪情、義無反顧的“義士”或“高大”英雄。司馬遷撰《太史公書》,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許多地方或以簡短議論,或以敘述甚至抒情口吻,表明態度。有時一字含褒貶。在《史記·王翦列傳》里言:“燕使荊軻為賊于秦。”用一“賊”字,或許表明著情感色彩。《資治通鑒》刪去了易水送別場面,可能表明了司馬光并不稱道的態度。
荊軻為何失敗?曾在邯鄲“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的魯勾踐,認為“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鹽鐵論·論勇》載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陶淵明《詠荊軻》嘆惋、贊賞道:“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說法,頗為新鮮:
余謂荊軻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
實際上,荊軻本人在“第一現場”“第一時間”,對此已回答。“事所以不成者,以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因為此前太子丹設計的第一步計劃為:“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此舉不行,“因而刺殺之”。由荊軻現場行為看,應該也是想“活捉”秦王。但第一步不成功,哪還再有機會?此事由在現場、目睹事件全過程的侍醫夏無且,講述給公孫季功、董生。后者“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司馬遷據此記載,應具真實性。
若荊軻成功,我國的歷史就要改寫。但荊軻若成功,對社會、百姓,果真是好事?荊軻刺秦王在公元前二二七年,此時韓已為秦所滅,其他五國都還在抵抗。秦國內部,大將王翦、辛勝、楊端、李信等手握重兵,正在外攻城略地。秦還有一個大將桓齮,被趙國名將李牧打敗后降燕。“父母、宗族,皆為戮沒。”秦王還用“金千斤,邑萬家”懸賞其人頭。楊寬《戰國史》以為《史記·刺客列傳》里的樊於期即桓齮。荊軻告訴樊於期:“愿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樊於期自殺。“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荊軻于是捧著人頭,“與燕督亢之地圖”,藏著“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的徐夫人匕首,去刺殺秦始皇。但荊軻若刺殺成功,秦國很有可能出現內亂,進而波及天下。對此,太子丹是清楚的。“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問,諸侯得合縱,其破秦必矣。”如此,燕與其他諸侯國,得以茍延殘喘,這是太子丹想要的結果。蘇洵《六國論》不無遺憾地設想: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但試想:即使秦內亂,即使諸侯又合縱破秦,但天下大勢得不到扭轉,混亂分裂格局不會改變。不能解蒼生之苦,不能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只能順延已持續了幾百年的戰亂局面,推遲孟子所說“定于一”的歷史進程。這無益于時代,無益于社會,無益于百姓。戰亂多一日,民眾苦海深一重。誰也不愿意再繼續維持這種拉鋸爭戰的慘烈局面。對其他諸侯國君臣而言,秦是最大敵人,但對天下生民而言,無休止的戰亂,才是最大敵人,最致命禍患,最慘烈現實。越早結束戰亂,百姓越早脫離深重災難。所以,荊軻失敗,對社會、對天下蒼生而言,未嘗不是好事。荊軻的行為加速了燕亡,也加速了秦統一天下的步伐,客觀上又做了件好事。
人們對荊軻抱以同情、惋惜之情,很大程度上,是對秦抱有偏見,不愿接受來自西域的“虎狼之國”統一天下的事實。秦在征戰殺伐的兼并戰爭中,確實殘暴至極。如公元前二九三年伊闕之戰,秦將白起大勝韓、魏聯軍,斬首二十四萬;公元前二七三年華陽之戰,白起大勝趙、魏聯軍,斬首十五萬;公元前二六0年長平之戰,白起坑殺趙降卒四十五萬;公元前二三四年平陽之戰,秦將桓漪大勝趙軍,斬首十萬。面對暴秦,人們希望荊軻刺殺成功,在情理之中。
但話說回來。春秋戰國“無義戰”的幾百年問,有哪個諸侯國君,不是“樂殺人”者?“嗜殺人”者?有哪場大戰役,不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堆起累累白骨?齊國在公元前三一四年攻下燕國,“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使燕國百姓“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試想,在當時只能以戰爭平息戰爭的環境、形勢下,有哪個諸侯國君能不靠血腥殺戮,而憑借善良、仁慈,在溫情脈脈的人道牧歌聲中實現統一?這絕不是說秦國的行為合理,但在亂世年問,面對“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的現狀,誰能及早結束生靈涂炭的戰亂局面,統一天下,讓社會安定下來,讓百姓過上太平日子,誰就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誰就是時代的強者與英雄,抑或救星。這是民心所向,社會期盼,歷史呼聲。秦能統一,非老天青睞,“賦予”其使命,而是靠一場場征戰取得的勝利,憑借武力硬生生“打”出來的結果。李白《古風》云:“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秦統一與“天下應該統一”的“大勢所趨”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聯。正因如此,秦始皇堪稱“千古一帝”,“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但統一之后,秦“仁心不施”,“樂以刑殺為威”。從思想文化發展史角度看,人們能接受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的黃老文化,能接受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自由、豐富、開放、多元文化,能接受以仁義禮智信及忠孝等豐富內容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能接受外來的、倡導人們積德行善,有著悲憫情懷、敬畏意識的佛教文化,唯獨不能認同、接受以暴虐、專制、集權、愚民、利己、享樂為核心的秦國文化。李斯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的焚書,“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的坑儒,“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極端文化禁錮,試圖摧毀思想的土壤,打碎文化的基石,摒棄精神的家園,遠離心靈的故鄉,毀壞文化的“根”與“魂”,割斷賡續的文化臍帶與血脈,撲滅氤氳的文化香火,建立異樣、另類的“秦文化”,讓后代人找不到思想的出發點,無心靈立足點,精神歸屬地,成為文化上的游子和流浪者,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上,雖然弟子對孔子評價很高,孟子也努力推崇其為圣人,但春秋戰國分裂、混亂時代,孔子并未受重視,儒家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在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由于歷代統治者的尊奉,使得民眾膜拜,孔子地位歷久彌高,以至于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孔子生而為圣。《三國志·魏志·文帝紀》云:“昔仲尼大圣之才,懷帝王之器,……可謂命世之大圣,億載之師表者也。”清人皮錫瑞《經學通論》“序”言:“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合此而無以自立者。”在中國歷史上,誰要撼動孔子的圣人地位,誰要對“六經”不敬,誰就是在人為制造精神的荒漠,會激起民族的集體憤怒情緒。不僅情感上不能接受,而且會成為眾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這是一種濃厚的深層民族文化心理。秦始皇正好犯了此大忌。他以征戰殺伐統一天下,也要以暴力強勢思維,建立具有鮮明秦國特色的專制文化,讓儒家文化“斷裂”,扮演了民族公敵角色,故成為人們一個不得解的厭惡心結。
人們同情荊軻,還應該與反感秦始皇個性、心術、人品有關。為統一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的秦將王翦云:“秦王怛(驕橫、粗暴)而不信人。”其他負面評價,如“秦王懷貪鄙之心”;“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再加上筑長城成為歷代人心頭恐怖的夢魘,揮之不去的陰影,始皇自然就成了一個被妖魔化的暴君,一個草菅人命、戕害生命的屠夫。對他無好感,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所以對秦統一天下,耿耿于懷,希望統一天下的不是強秦,遺憾荊軻未能成功。
但客觀、辯證、歷史、公允地看,不應將秦統一天下的功績與統一后的暴虐混為一談。任何時候,秦統一天下的歷史意義都值得肯定。而秦能統一天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開放、包容的人才文化的成功,是持續不斷的變法、改革、創新的成功。李斯《諫逐客書》給秦始皇“上課”,告誡他不要數典忘祖時指出:“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枝于晉。”秦自穆公始,眼光向外,形成了地不分大小,國不分強弱,人不拘身份,天下之才,“為我所用”的“大人才”戰略。秦國養成了廣攬天下賢能,集天下人智慧而取天下的好風氣、大格局,取得了“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的好結果。任用客卿,“使秦成帝業”。沒有放眼天下,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的大胸懷、大境界、大氣象,很難“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人才文化的核心,在思想、智慧、謀略,其他一切都建立在此基礎上,一切成功均在此前提下。《史記-秦本紀》言獻公慕求“賓客群臣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實際就是求天下“最強智慧大腦”。即使到了公元前二二五年,在已露統一曙光前夕,秦伐楚,因不用老將王翦之計而大敗后,秦王還親赴頻陽,登門向王翦檢討謝罪,并再次起用老將滅楚。秦的成功,印證了“得士則倡,失士則亡”的道理。
戰國士人按地域分布、聚集,先后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五大學術中心”。《漢書·藝文志》言“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魏國形成了以儒家子夏為首的“西河學術中心”;齊國有淳于髡、鄒衍、慎到等“不治而議論”的辯士組成的“稷下學術中心”;楚國相繼有以屈原、宋玉、景差等文學之士為主的“蘭臺學術中心”,以儒家荀況為首的“蘭陵學術中心”;秦國有以呂不韋為首的“咸陽學術中心”。儒家的“王道”“仁政”,設想很美好,但那是天下統一、社會穩定后,理想的政治綱領。在弱肉強食的兼并戰亂年間,高喊“仁者無敵”,顯得蒼白無力。《史記》所記孟子“迂遠而闊于事情”的認識,實為的論。齊、楚也都有統一天下的可能,但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言:“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而文學顯然無助于平定天下。反觀秦國,呂不韋以富賈之身,棄商從政,以“仲父”之尊,最講究實用哲學。他緊緊抓住統一天下是歷史、社會、民眾最大期盼、最迫切要求的時代“最大政治”,以滅六國、定天下為目標,抓住了時代的“牛鼻子”,點中了時代的“穴位”。雖“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但“四大公子”之門,魚龍混雜,不乏雞鳴狗盜之徒,難成大器。不像秦國那樣,匯集了一批文能運籌帷幄,武能攻城略地的能臣驍將,時代精英。
同時,“戰國七雄”中,魏用李悝、趙用公仲連、楚用吳起、韓用申不害、齊用鄒忌進行改革,但沒有連續性,更沒有形成傳統。秦國先后任用客卿商鞅、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持續變法、改革、創新。秦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