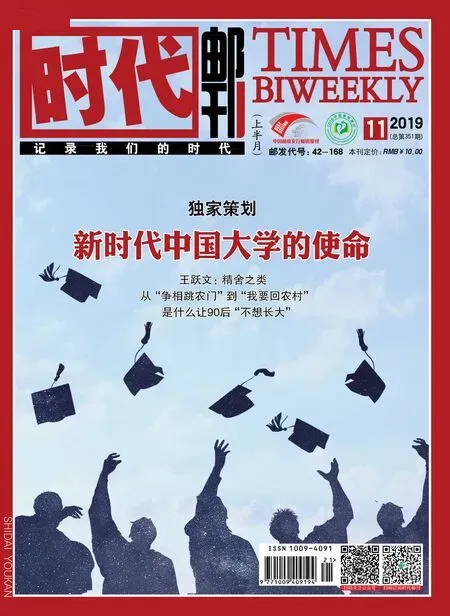讀完博士干什么
□李雅娟
近年來,中國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連年攀升:2004年,有2.3萬名博士畢業,博士人數首次在《中國統計年鑒》中作為單獨門類統計;2018年,博士畢業人數突破6萬。
在傳統觀念中,獲得了博士學位,就應以學術為業,但這一觀念正日益受到挑戰。《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近幾年來,中國每年新增博士畢業生人數比新增高校教師多兩萬人左右,這意味著約1/3的博士畢業生沒有獲得高校教職。
拿到了人類社會的最高學位,在學術圈外,博士該何去何從?
學歷市場的贏家,就業市場的“萌新”
馬上能夠順利拿到畢業證和學位證,手握兩所高校offer的物理學博士孟溪,儼然是博士畢業生中的贏家。但參加完論文答辯,她卻突然感覺情緒跌入了谷底。她曾以為自己想當一名高校教師,從事科研工作,然而這樣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讓她感到恐慌。
讀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單純。“當時年紀小,總覺得這輩子起碼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她就這樣開啟了讀博之路。至于未來找什么工作、就業市場情況如何,她自嘲道:“以我當時的心智,根本不可能想到這些。”
讀博期間,她跟導師交流最多的就是實驗情況。而工作打算以及就業市場行情,則很少進入他們的討論范疇。過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單休的實驗室生活,一位師兄提醒她:“趕緊做簡歷,準備找工作吧!”
于是孟溪開啟了“找工作模式”,但實際上,她無法花太多時間聯系工作:寫畢業論文已經占用了她絕大部分的精力。她曾連續一個多月熬到凌晨兩點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開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識到,那件灰色套頭衫自己已穿了十來天。
她的導師則認為,“博士畢業理所應當去高校”。孟溪的師兄師姐畢業后,基本都走了這條路。孟溪原本也以為自己愿意當一名大學教師。今年春天,孟溪的論文盲審和畢業答辯都很順利,也有兩所高校給她發了offer。眼看再過不久就能拿到學位證,但她突然感覺自己像是被擊垮了,眼淚會不由自主地涌出來。
前幾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議,同一所離家較近的高校簽了約。但高校里的績效考核卻讓她擔憂:學校明確表示不會提供科研啟動經費,而且要在入職之后才能知道具體的考核標準,但她已經聽過好幾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
孟溪有一個朋友在山東某高校任教,入職后才發現校方提高了考核標準。朋友向她抱怨:“安家費沒落實多少,別的(待遇)也沒漲,倒是考核標準漲了。”
但蘭州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馬軍認為,當前博士生的就業情況仍比較樂觀。“在高校里,除了國家提供的基本工資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較多,每年收獲的科研績效是非常可觀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沒有上限。”
多元化就業趨勢初現
任奇在博士畢業后到某國企工作。作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業中做科研不必擔心偏離實際——國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產,而且可以提供一線數據作為參考。再者,國企資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學那樣絞盡腦汁地申請課題基金——企業內部就可以為他提供數百萬元的研究經費。
但任奇很快便意識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齡。任奇本科畢業后,因成績優異,被保送為本校的直博生。跟讀完3年碩士再讀博的同學相比,27歲就拿到博士學位的任奇,已經有很大的年齡優勢。盡管如此,任奇進入國企工作后,還是尷尬地發現自己屬于“大齡新人”。
上聲字的曲字調值和字腔的基本音勢都呈狀的高—低—高勢。專用腔格是罕腔法,符號是。譜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罕腔的專用符合來標記,另一種是以實音來標記。由罕腔而來的上聲字腔譜面只有一個升勢的腔尾,其腔頭的降勢通常都用符號表示,演唱的效果相當于下滑音。
任奇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如果在企業發展的話,博士只適合走技術路線,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線,可能已經晚了。但他又意識到:在仿照公務員系統運轉的國企中,幾乎所有的資源都圍繞行政管理權力運轉。這就意味著,如果他未能得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職位,對于做科研也不利。
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營企業成為部分博士畢業生的新選擇。在清華大學的就業重點單位榜單上,華為公司連續3年都是“收割”畢業生最多的單位,最近兩年,榜單上還出現了騰訊、阿里巴巴等“新興勢力”。不過,上述企業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計算機、應用數學、人工智能等近年的熱門領域。另外,還有一些博士選擇到黨政機關工作。2018年,福建省委組織部一舉招攬了30名清華博士畢業生,僅次于華為公司的31人。
從國內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不難發現博士生就業多元化的趨勢。5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簽三方就業的博士畢業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國企、私企就業的比例明顯上升。這背后是嚴峻的學術圈就業形勢: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學術職位的數量卻相對穩定。供大于求的形勢之下,“非學術職業”就成為博士畢業生主動或被動的選擇。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認識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當老師,有人到企業工作,有人到中學當老師。“形勢就是這樣的,高校沒有那么多職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較苦。如果特別喜歡做學術的話,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掙錢的話,那就可以進企業。”馬臻說。
馬臻還發現,大部分博士生找工作都比較容易,只需投遞簡歷,再花少量時間面試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學位本身就有足夠的分量。馬臻的一個博士生找工作時,對方非常信任這名學生:“能拿到博士學位的至少不傻,有專業能力。”馬臻認為,機會永遠是屬于強者的。
學術圈外,博士何為
近年來,中國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連年擴大,2018年9.55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人數再創新高。博士帽多了,一些并不指向學術生產的工作崗位也開始要求博士學歷。有些高校招聘學生輔導員時要求博士學歷,而在以往,這個崗位主要是針對本科或碩士畢業生。
1979年,美國學者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描述了“文憑通貨膨脹”的現象,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
但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一種矛盾的現象。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卿石松指出,企業是我國研發經費支出最多的部門,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中擁有博士學位的還不到1%。就傳統的博士“生產”目標——培養學術接班人——來說,博士數量可能過多,但如果換個角度看,知識經濟時代需要高級人才,要推動科技和產業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他認為,如果將企業需求考慮在內,目前的博士人才數量仍然不足。
張恬在讀博之前,就是奔著工業界去的。面對幾份offer,她沒有太多猶豫便選定了這所位于美國東海岸的州立大學。在業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張恬通過學校和學院組織的講座開始接觸業界。
今年暑期,張恬申請到波士頓一家公司的實習崗位。她原以為,公司里的研發工作相對簡單,博士期間學的很多知識可能用不上。但她開始工作后就發現,這家公司在研發很多新產品,她面臨著許多未知。
跟讀博時做的課題相比,公司的課題難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戰。在這里,張恬的研究能在較短時間內就看到答案,“反饋來得很快”,這讓她覺得“自己的活兒沒白干”。相比之下,讀博時的研究就像一個人在廣闊的沙漠里踽踽獨行,不知還有多久才能看到綠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沒有綠洲。張恬說,相比學校,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錯率比較低。
卿石松認為,到企業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業文化和商業環境,例如要更多考慮經濟效益;但在校期間,學術能力仍應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自身通用能力的培養,如溝通能力、跨學科合作能力等。
作為宏大結構之中的個體,博士生們能做的也許就是更早地規劃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