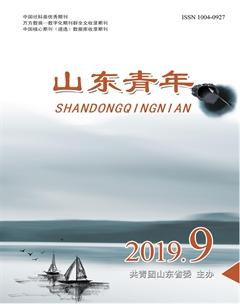淺談專名的指稱問題
盛郁鳳
摘 要:在名稱理論中,專名的指稱問題一直頗受爭議。穆勒和克里普克持專名直接指稱對象的觀點,而弗雷格、羅素等人則通過摹狀詞確定專名的指稱。本文通過對專名指稱理論發展歷程的簡單梳理及分析,試圖將摹狀詞與真正意義上的專名區分開,并論證專名和對象之間對應關系的唯一性。
關鍵詞:專名;摹狀詞;指稱;涵義
專名的相關研究是語言哲學中頗受重視的一部分,而專名的指稱理論涉及名稱和對象,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涉及與涵義及指稱與涵義關系等相關問題。指稱理論最終要解決的是名稱和對象之間如何關聯的問題。本文將通過對這個領域發展歷程的梳理,解決以下幾個問題:名稱何以被賦予對象?名稱如何指稱對象?名稱和對象之間的關聯方式是唯一的嗎?何種關聯方式較為合理?
一、專名指稱理論的發展歷程
對專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邏輯學家穆勒(J.S.Mill)。在《邏輯體系》中,穆勒將名稱分為內涵名稱和非內涵名稱,并把專名歸入非內涵名稱:“只有那些沒有任何內涵的對象名稱才是專有名稱,嚴格來講它們沒有意義。”①非內涵名稱的指稱是某個個體或屬性,它與內涵名稱的區別在于:內涵名稱暗含某種屬性,如“白色的”暗含白色物質共有的屬性;而非內涵屬性可以表示一種屬性,如“白色”表示一種屬性,但不暗含白色物質共有的屬性,因為“白色”不是白色物質。②因此,專名作為非內涵名稱,只有指稱而無內涵,僅僅是對象的一個簡單符號,通過這些簡單符號,人們在表達時就有明確所指,即便它們并不知道這些對象為何有這些名字。
弗雷格(G.Frege)與穆勒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專名既有指稱,也有涵義。其關于同一性的著名論證對他的這一觀點給予了有力支撐。具有“a=b”形式的陳述比具有“a=a”形式的陳述包含更高的認知價值,因為后者是先驗有效的,而前者告訴我們:(1)不同符號或名稱表示相同的事物;(2)符號或名稱的區別實際上是表達方式的區別;(3)不同名稱可以指稱相同,但表達方式不同,即涵義不同。我們對對象的認識就是我們的表達方式,也是對象的涵義。涵義不是認識的全部,我們幾乎不可能達到對某一對象的全部認識。因此“a=b”的價值在于,不同主體對統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認識,這樣也就能不斷擴大主體的認識。③
在弗雷格看來,專名的指稱是由其涵義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弗雷格把專名的外延擴展至所有表示單一個體的復合符號,導致真正意義上的專名和限定摹狀詞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而正是在這個模糊地帶,羅素(B.Russell)創立了摹狀詞理論。
羅素區分了專名和限定摹狀詞,認為專名的涵義由相關的限定摹狀詞給出,或者說,專名只是縮略的摹狀詞。他的這一區分同時還解決了空專名的問題,將專名拆分為兩部分:存在一個對象,對象擁有某個性質(或擁有某個名稱)。
專名的指稱也由相關的限定摹狀詞給出。羅素的這一指稱理論被稱為描述指稱理論:摹狀詞具有描述功能,專名通過摹狀詞對對象的特征描述而獲得指稱。這么看來,專名的涵義和指稱都與摹狀詞密切相關,可以說都是基于摹狀詞才擁有意義。那么專名和摹狀詞之間的本質差別又被取消了,一切關于摹狀詞的疑問都同樣是專名的疑問。同時,羅素忽視了弗雷格區分涵義和指稱的意義,而將涵義和指稱通過摹狀詞等同起來,這一做法是一切麻煩的根源所在。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回答與專名相關的摹狀詞的選擇問題。選擇的標準是什么?需要選擇多少數量的摹狀詞?簇摹狀詞理論由此誕生,由維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提出,又經斯特勞森和塞爾得到完善。該理論指出:一簇摹狀詞一起表達專名的涵義,其中大多數摹狀詞所指向的對象就是專名的指稱。這一理論在羅素的摹狀詞理論基礎上邁進了一步,但在選擇標準和數量問題上仍未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克里普克的因果歷史指稱理論另辟蹊徑,從專名的命名入手尋找出路。在《命題和必然性》中,克里普克區分了嚴格指示詞和非嚴格指示詞,區分的依據是詞項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是否都指示同一個對象④。專名作為嚴格指示詞,其確定性得到了肯定。克里普克的這一觀點既是對描述指稱理論的反駁,也選擇了穆勒在專名意義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在闡述“確定指稱與實際上把一個術語定義為另一個術語的意義的做法是相反的”
⑤時,他就已經清楚表明指稱和名稱之間的唯一對應關系是最重要的,而無需通過涵義去不斷檢驗這種對應關系是不是正確和唯一的。
二、專名與指稱之間的唯一對應
將摹狀詞與真正意義上的專名區分開來是重要的。如羅素所言,嚴格意義上的專名是指稱單個對象的名稱,是一個簡單符號。所謂簡單符號,即不可進行分析、其部分不再是符號的符號⑥。專名與通名的本質差別在于,專名在語言表達中的作用僅僅是作為符號的名稱和其所指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不管該對象為何叫這個名字,從何時起叫這個名字,只要當這個名字已出現,傾聽者就能意識到說話者所指的對象,這就夠了。
而摹狀詞因其描述功能而使得涵義決定指稱,從而導致指稱的不確定性。當人們用摹狀詞進行表達時,心靈首先考慮的是摹狀詞各個部分單獨的涵義,再根據這些涵義復合而成的涵義進行指稱。一旦對象的屬性改變(而這是時常發生的),原先的摹狀詞就實際上不再指稱該對象。這顯然也不符合語言表達對專名的要求。
因此,若將專名和摹狀詞嚴格區分開,就會發現各自在語言表達上的優勢。專名與指稱緊密相聯,且唯一對應,這種確定性本就該是專名的特性之一。當然,這一區分之所以必要是基于專名問題的語境前提的,在其他名稱或詞項的指稱問題中摹狀詞仍然發揮重要作用。
[注釋]
① 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London: Ballantyne Press, 1886:P21.
② 參見John Stuart Mill.: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London: Ballantyne Press, 1886:P19.
③ 參見弗雷格:《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王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第95~96頁。
④ 參見克里普克:《命題和必然性》.梅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29頁。
⑤ 參見克里普克:《命題和必然性》.梅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41頁。
⑥ 參見羅素:《數理哲學導論》.晏成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178頁。
[參考文獻]
[1] John Stuart 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J]. London: Ballantyne Press, 1886.
[2] 弗雷格.弗雷格哲學論著選輯[M].王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3] 羅素.數理哲學導論[M].晏成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 克里普克.命題和必然性[M].梅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5] 馮棉.名稱的涵義與指稱——從穆勒到克里普克[N].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3).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上海? 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