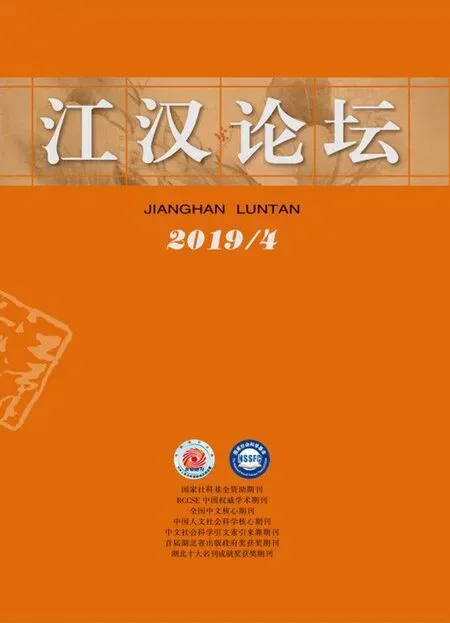關于西周王朝青銅原料與鑄造作坊的多視角考察
易德生
從法理上講,由王畿和諸侯封國構成的西周王朝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結構是以王畿為中心,王畿四周是拱衛中央王朝的諸侯國①;諸侯國之外或之間錯居著叛服無常的方國或所謂的蠻夷部族,更遠的地方則是蠻荒的所謂“四海”之地。在這種基本的政治框架之下,西周社會在宗法制度、禮樂制度和貴族等級制度為主導的軌道上運行。青銅禮樂器和兵器作為體現“祀與戎”的物質化載體②,在西周社會占有極重要的位置;西周時期無疑仍處于中國青銅時代的興盛階段。既然如此,我們需要思考如下重要問題:鑄造這些青銅器物的青銅原料③,是如何被控制和流通的,使用這些原料的銅器鑄造作坊是以何種屬性存在,是私有還是國有?這些問題偶爾被提及但似乎很少被學界系統地論述過,然而又是非常重要的涉及西周經濟、政治制度的問題。
一、西周中央王朝和諸侯國對青銅資源的控制
談到青銅原料,首先必定會涉及到青銅工業的上游產業——銅礦、錫礦等青銅資源及其開采冶煉。西周時期,無論是中央王朝還是諸侯國,應該是國家直接占有銅礦等礦山資源,并且控制著青銅資源的開采和冶煉。這種對銅礦等礦山資源的國家壟斷制度,嚴厲禁止私人對銅礦等青銅資源的開發。天子和諸侯國君對青銅資源的控制,實際上是從原料上游方面控制了青銅兵器及禮器的生產,從而也控制了“祀與戎”這樣的軍國大事。我們從《周禮》④、《左傳》等一些先秦文獻的記載中,能隱約看出這種國家對銅礦等重要戰略資源的占有和壟斷⑤。
《周禮·地官》提到“礦人”,“掌金(銅) 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管子》雖然成書于戰國時期,但是其某些記載無疑有春秋及更早時期的制度。《管子·地數》說,“茍山之見其榮(即礦苗——筆者按)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這種對礦山“封禁”的做法可能具有普遍性。《管子·輕重乙》記載:“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從這段話看出,管子建議私人可以開采礦山,國家征稅即可,而不建議國家用早期的老辦法來開采礦山。老辦法應是西周及春秋時期的辦法,是指國家不但壟斷礦山資源,而且還組織工匠及奴隸等人員進行開采。
對于西周中央王朝來說,不僅對王畿內的礦山資源有占有和控制權,對諸侯國的重要礦產資源也應有占有和管理的權利。《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責:“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周禮·夏官》提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很明顯,大司徒及職方氏之職責,要周知九州及諸侯國的山林、川澤名物,自然也包括對諸侯國重要金屬礦產資源的掌握。
上面是從王權或國家占有資源的角度來說的,實際上,從礦產開發技術的難度和需要組織大量勞動力的角度看,銅礦等青銅資源的開發也只能靠國家來實施,私人缺乏開發的能力,因此也就談不上占有。從商周古銅礦遺址的開采遺跡及煉渣遺物來看,銅礦的開采及冶煉是一項高度繁難的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從辨認礦物和探礦,到建構地下采礦區的井巷支護系統,再到選礦冶煉,幾乎每個環節都需要高技術的運用、大量勞動以及人力的組織。⑥我們以西周大冶銅綠山古銅礦為例。開采礦石一般是由淺到深,從露在地表或較淺的礦體先開采,然后再開采更深的礦體。由于出露地表的礦體總是有限,更多的礦石是隱伏在圍巖或淺層礦體之下的,因此,當表層礦體采完,則會采用坑采(又稱地下開采)的方法。在深入地下的坑采過程中,自然會形成采空區,為了保確保采礦區不致坍塌和開采工匠的安全,商周工匠發明了復雜的井巷支護系統。與支護系統相配合,還必須有排水、礦物運輸、照明等一系列的作業進行配合。⑦銅礦的冶煉需要對冶煉溫度、冶煉化學氣氛的控制和掌握,這在當時無疑都是較尖端的技術。總之,銅礦的開采和冶煉是巨大的系統工程,凝聚著多種技藝和工藝,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人工組織能力,有勢力的大貴族難以做這樣的事情,即使擁有技術和人力,也會因為成本太高而不愿去做,因此,只有王朝的天子和諸侯國君以國家的名義,才有能力組織人力進行礦產的開采和冶煉。
中央王朝對青銅資源和青銅原料的控制狀況,某些科技考古的成果也會給我們吐露重要信息。崔劍鋒等對夏、商及西周王朝出土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和晉國、燕國、盤龍城遺址出土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做了對比分析。⑧由于角度不同,崔氏得出了一些有關青銅原料產地的結論。我們則根據書中的這些數據及其對比圖⑨,明顯可以看出,西周王朝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和晉國及燕國都有很多重合之處。這種重合,可能表明了如下的事實。
首先,西周王朝不但開發了金屬礦山資源,而且,可能還大量地把冶煉好的青銅原料(包括青銅器),輸送給親近的諸侯國,從而造成王朝與諸侯國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高度重合。這意味著,西周時期,存在中央王朝向一些諸侯國(尤其是沒有礦產資源的諸侯國或缺乏銅礦開采冶煉技術的諸侯國)提供金屬原料的情況。這種提供金屬原料的行為,本身是宗主國對諸侯國進行控制和表示恩惠的一種方法。正如許多西周銅器銘文所揭示的,天子賞賜給臣下“金”或“貝”,而臣下則鑄銅器“對揚天子休”,以示感恩和榮耀。其次,從數據中還可看出,晉國和燕國除了一部分銅器鉛同位素比值和中央王朝的重合外,也有一部分顯得較分散,并不重合。這也許表明,一些金屬資源豐富的諸侯國應該也擁有自己的青銅工業,在中央王朝的特許下,能夠獨立進行金屬礦山資源的開發及冶煉,能自己生產青銅原料并進行青銅器的鑄造。
新近的鉛同位素考古成果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⑩郁永彬等對西周早期曾國葉家山墓地出土的129件銅器,湖北隨州羊子山12件銅器、河南洛陽北窯墓地出土的17件銅器、 陜西周原周公廟、孔頭溝和李家鑄銅遺址等出土的31件銅器或銅塊進行了鉛同位素比值的檢測分析;同時,將這些數據和北京琉璃河墓地、山西晉侯墓地、晉國邦墓區、橫水墓地、大河口墓地銅器、部分海外博物館藏銅器以及陜西周原出土銅塊的鉛同位素數據行進了比較。結果發現,這些諸侯國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和來自陜西周原、洛陽等王畿地區的的鉛同位素比值都有一定程度的重疊。他們因此認為,王畿地區和諸侯國的銅器至少有一部分原料來源可能相同,王朝控制著青銅原料并輸入諸侯國的可能性很大。?
二、青銅原料的控制及流通
要考察西周王朝青銅原料的控制及流通方式,必然會涉及到西周時期的工商業狀況,故這里需要對西周的工商業及經濟制度做一簡略分析。
盡管直接記述西周社會性質的資料不多,但是從先秦文獻的記載和戰國時期社會巨變往前推斷來看,我們認為西周社會不應是奴隸制,而是封建領主制?,這種制度與建國前云南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地區和西藏的領主農奴制度頗有相似之處?。這種社會最根本的經濟制度是孟子所說的“井田制”;同時,莊園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其最顯著的特點。自然經濟導致市場需求狹小,工商業不太活躍,西周時期是工商業緩慢發展的一個階段。
1.西周工商業是以國有和貴族所有為主導
西周乃至春秋前期,和農業相比,工商業受到更多的管制和束縛,社會工商業的主流應是“工商食官”?。對“工商食官”的具體內涵和所體現的社會性質,學界討論頗多?;但一些學者根據“工商食官”一語,認為西周時期不存在獨立性質的私人工商業,這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筆者認為,對于“工商食官”的“官”字,其含義似應理解為“公”,而“公”在春秋及以前是可以指稱國家或貴族的。王玉哲認為,在《詩經》中,“公”字大都做“貴族”、“統治階級”或“官”解釋,所謂“公田”,并不是公眾集體所有的田,而是“官田”,是屬于貴族的田。貴族之田名為“公田”,直到漢代還有這種習慣稱呼。?《國語·周語上》記載,“古者……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供)其上”。這里的“上”,無論理解為國家或貴族領主,都是合適的。如果從“公”或“上”這樣的意義來看“工商食官”這句話,則可以理解為西周的工商業主要掌握在國家和貴族領主手中,“食官”的工匠及商人或被官家豢養,或依附于貴族。?
貴族擁有采邑或祿田,這是貴族的生存之本。西周時期是否有貴族經營工商業,是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認為,雖然制度規定了貴族的大致社會經濟地位,但是具體到個體,即使同一等級的貴族,也有賢愚、勤惰和相對貧富之分。舉例來說,土地交換在西周已經存在?,一般情況下,由于種種原因(包括犯罪、疾病等),失去土地的貴族肯定要比獲得其土地的同等級貴族要相對貧窮一些。因此,我們認為,西周時期應有一些善于經營的貴族控制其采邑里的工匠和商奴,由工匠制作產品,同時役使商奴經商,把多余的手工產品用于交換和牟利。《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意思是選立三卿,需要他們擁有大量的錢財,這多少表明當時有貴族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積累大量財富后更容易當高官。銅器銘文常透露出貴族擁有百工及兼營工商業的跡象。陜西出土的五祀衛鼎、九年衛鼎及衛盉,其做器者為裘衛,從銘文看,他既是個貴族,又似乎是個兼營獸皮等皮制品的工商業者?。公臣簋(西周晚期)銘文云:“虢仲令公臣司朕百工”?,即大貴族虢仲命令公臣管理他的許多工匠。貴族經營工商業及奴役工奴、商奴的事例在人類學(民族學)中常可看到。據馬曜、繆鸞和調查,云南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在農奴封建領主制度下,有“滾很召”階層。按當地語言,“滾很召”意思是國家或貴族所屬的家奴。這些家奴有的要負擔貴族家內的勞役,有的是工商農奴。這些工商農奴的勞役包括“榨糖、熬糖、煮酒、熬鹽、紡紗、織布、染布、蓋房子、做生意、趕馱牛馱馬”等。?
盡管西周時期的工商業以國有和貴族所有為主,但該時期也應存在獨立的或半獨立的平民工商業者。?周王朝剛建立時,其統治者就鼓勵殷遺民去經商。《尚書·酒誥》中對殷遺民說:“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詩經·大雅·瞻卬》說:“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是指貴族階層也知道商業利潤高,甚至可能開始經營商業了。高明在總結了一些金文資料后認為,西周商業同手工業一樣可分為兩類,一是“工商食官”制度下的官府商業,一是民間經營的私人商業。民間大商業者(包括沒有官職的貴族)往往從事利潤高昂的商業,而小商人多經營民間生活用品。?總之,“工商食官”并不意味著當時社會沒有平民性質的獨立工商業者,只不過由于游離于國家和貴族之外的平民階層較少,所以這類工商業者確實比較少而已。這類工商業者主要從事日常生活必須品的制造和買賣。
由于存在公私工商業,西周時期自然存在商品交換的媒介——貨幣。該時期充當貨幣的物品有多種,但以貝(海貝)幣和金幣(指銅或青銅做成的貨幣)為主。貝幣以朋為計算單位。金幣有兩種,以青銅模仿海貝形狀做的貝幣(所謂“金貝”) 和青銅稱量貨幣(圓形或方形銅錠)。金幣或青銅原料以寽(鋝)或鈞為計算單位。寽和鈞大致相當于當今的多少斤,學界爭論較大,限于篇幅,暫不討論。銅器銘文中常見賜“金”的記載,這里的“金”或是指青銅稱量貨幣,或是指沒有固定重量的青銅原料塊,但是都可以做為交換的媒介——貨幣。
2.國家控制青銅原料的生產、出售和最終回收
如前所述,銅礦等青銅資源及其開采冶煉是由國家壟斷和控制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認為,青銅原料也應被國家所控制。青銅時代,“祀與戎”是國之大事,青銅禮器是宗法制度和禮樂文明的物質載體,戰爭武器也是由青銅制作的,再加上青銅原料又可以鑄造金屬貨幣,也即是說,青銅原料本身既是財富又是財富的衡量尺度,因此,天子或國家,控制了青銅原料的生產和流通,實際上也就是控制了權力和財富。這樣極為重要的、具有戰略性地位的物資,自然不容貴族和私人來經營,因此,貴族所經營的工商業中,應沒有青銅原料的經營買賣,而只能是國家控制著青銅原料流通的各環節,包括即最初的產出、出售和最終的回收。
為了保證青銅原料控制在國家手中,周王朝或諸侯國家可能設有專門的國有機構。國家通過這樣的機構,控制著青銅原料最初的產出、買賣和最終的回收。一類機構是用來鑄造、貯存和支出金幣的,這類機構某種程度擔負著相當于現代中央銀行、或者國庫的功能,類似《周禮·天官》中的“外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鄭玄注“布”即“泉”,即錢,也即貨幣。孫詒讓說,外府是九府之一,“凡圓法鑄造及賦入之泉布(即錢幣,筆者按),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外府屬天官統轄,而天官直屬于天子。另一類機構是來征收、保存和回收青銅原料及青銅器物的,這種機構類似《周禮·秋官》中的“職金”一職。“職金”的職責是,“掌凡金(即銅,筆者按)、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西周金文和文獻中都提到用罰金(青銅貨幣)來贖罪。如侜眷匜銘文說,“(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罰汝三百鋝……罰金”?。《尚書·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鋝),閱實其罪”。“職金”也提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可見,西周以來,一直有用“金”或貨幣來贖罪的傳統和法規。
雖然青銅原料及金幣的產出、出售和回收被國家控制,但是,它們作為一種財富和財富的衡量尺度,猶如后世的黃金,個人一旦擁有,也能通過它們實現貢獻、賞賜、交換、支付及財富保值等功能,它們可以在個人之間流通。各等級貴族獲得青銅原料的途徑主要應是賞賜(饋贈)、俸祿和交換。金文中有大量這樣的記載,即天子或諸侯國君,或者上一級貴族,賞賜臣屬或下層貴族“金”若干,被賞賜的人表示感謝并往往鑄造銅器以示紀念和榮耀。另外一種方式則是用貝幣、土地、玉或其他珍貴物品和其他人或國家某些機構交換而來。還有一種方式,某些在國家機構中任職的貴族,部分俸祿以金幣的形式獲得,這在《周禮》中也有所記載。如《周禮·地官》“泉府”一職,“凡國之財用取具焉”,賈公彥疏:“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為具焉。”?總之,青銅原料一旦被貴族或個人所有,可以在民間及私下進行相互饋贈、交換等,但是其最初的產出、出售和最終的回收仍掌握在國家機構中。
三、西周時期國有鑄銅作坊和貴族鑄銅作坊并存
鑄造青銅器,雖然總體上要比青銅資源的采冶要容易且人力要少很多,但是在當時,要鑄造出精美的青銅器尤其是禮器(無疑是重要的奢侈品),同樣也是復雜的事情。首先,鑄造過程中,要經歷很復雜的諸多技術環節,如熔煉精銅、配制合金、制范作模、制作烘范窯、澆鑄成形、鑄后加工等?,其中某些環節在當時屬于高科技(如陶范的成分配制、銘文的鑄造等),靠這些高科技才能順利地鑄造出缺陷少而且精美的銅器;其次,鑄造青銅器仍然需要有一定數量的、需要分工合作的工匠,其成本和花費并不小。因此,西周時期鑄銅作坊并不多,并且絕大多數應是國有鑄造作坊。這種國有作坊的存在,首先是以國家的力量保證滿足天子、國君及大大小小貴族對青銅器物的需求;其次是來保證戰爭時期青銅兵器和車馬器的需求;還有,較大規模的、含有更多高難技術鑄銅作坊的存在,本身就是顯示統治者神圣和權威的一種象征。
國有鑄造作坊首先應包括中央王朝直屬的作坊,或稱之王室作坊。王室作坊無疑集中在都城區域。考古發現,成周洛陽有北窯鑄銅遺址?,宗周豐鎬雖然沒有發現類似洛陽北窯那樣規模較大的鑄造遺址,但是長安張家坡、馬王村西周早期遺址中出土有陶范殘塊,這表明西周都城豐鎬一帶也存在鑄銅遺址。?更多的西周鑄銅遺址在陜西周原發現?。對于其所有制屬性,下面會做具體分析。
除了王室作坊,我們認為至少到西周晚期,多數諸侯國也應存在國有作坊。即使在西周早中期,一些與周王朝關系密切的重要諸侯國,尤其是姬姓和姜姓諸侯國,也可能在王朝的幫助下建有國有鑄造作坊。松丸道雄對西周時期某些青銅器的銘文作了研究后認為,西周銅器中大多數為王室工房所作,但是,存在若干諸侯國的青銅鑄造工房或作坊;并且隨著周王室統治力的衰退,諸侯國的青銅鑄器在不斷增加,而王室制作的青銅器也漸次失去中心位置?。張昌平對位于隨(州) 棗(陽)走廊的噩國及曾國早期(葉家山出土)的銅器進行了細致的考察,他認為,曾國和噩國具有獨立生產青銅器的能力。總體來說,西周時期諸侯國獨立生產青銅器,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
既然西周時期存在王室鑄造作坊及諸侯國的國有作坊,那么自然會想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西周僅僅只有國有鑄銅作坊嗎?是否存在私人鑄銅作坊呢?對這個問題,似乎還沒人系統研究過?。前面已經說明,西周社會工商業由國家和貴族主導,我們由此認為,西周時期(主要是西周晚期)應該是存在私人鑄銅作坊的,只是數量很少,且可能只有勢力雄厚的大貴族才會擁有鑄銅作坊。
我們來看看陜西周原考古所發現的鑄銅遺址情況。周原地區鑄銅遺物的分布點很多,比較大的鑄銅遺址有周公廟遺址?、岐山孔頭溝遺址?、李家?、齊家北和齊鎮?等。據研究,從地理分布看,周公廟、孔頭溝和扶風李家鑄銅遺址自西至東依次排列,相隔僅10千米左右。另外,根據遺存分布、鑄件種類、制作工序等情況可以推測,這些相距不遠的鑄銅遺址,無論在制作工序還是在鑄件器類上,都沒有進行分工,各自相對完整且獨立地進行鑄銅作業。?既然這些鑄銅作坊沒有很明顯的分工,也就是說同質化現象嚴重,那么說這些作坊都屬于西周王朝國有,情理上似乎不通。因為如果都是國有作坊的話,這些作坊應該有所分工才對,比如有的作坊生產禮器,有的生產武器等等,不然相互之間會產生競爭和沖突。曹瑋認為,西周時期的周原是非姬姓高級貴族的云集之地?,我們認為周原的鑄銅遺址至少有部分可能是貴族私家所擁有。另外,如果周公廟遺址是周公采邑的話?,則周公廟鑄銅作坊則可能為周公所有。象周公這樣的大貴族,應具備擁有鑄銅作坊的實力。
金文中有用“貝”去鑄造或訂做青銅禮器的記載。如遽伯簋(西周早期)銘文說,“遽伯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用貨幣“貝”可以到鑄造作坊來“作”銅器,實際上就是“買”或“訂做”銅器,訂做銅器的作坊首先應是國有作坊,但也可能包括貴族私人作坊。容庚認為西周晚期存在銅器的買賣。?王冠英也認為,西周時期銅器等貴重禮器可能存在買賣、交換情況。?朱鳳瀚在一篇文章中認為,由于流動性的自由鑄銅工匠在西周還不一定出現,因此,大的世家貴族可能擁有鑄銅作坊,并且一些貴族會以貨幣或以物易物的方式,來購置或訂制青銅禮器。?
總的結論是,西周時期,王畿及諸侯國內的銅礦等青銅資源及其開采、冶煉皆為西周王朝所控制,在王朝的特許下,某些諸侯國家也可能支配自己疆域內的青銅資源。青銅原料的生產、出售和回收等流通環節,應由國家專門機構來管理,私人包括貴族不能進行青銅原料的買賣等經營活動,但是青銅原料及金幣(由青銅原料制成)可以在民間交換、流通。西周時期存在兩大類青銅鑄造作坊,一是國有作坊,包括天子作坊(王室作坊)和諸侯國君作坊;二是有實力的貴族也可能擁有私家作坊。貴族如果需要青銅器,往往通過貨幣(如貝)或以物換物的方式,從國有鑄銅作坊或貴族的私有作坊進行購買或訂做。
注釋:
① 為了和諸侯國相對應,本文有時稱呼西周王朝為“中央王朝”。
② 《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③ 指經冶煉而成的銅、錫、鉛等金屬原料,習慣稱為“銅料”、“錫料”及“鉛料”,較為普遍的形式是以方形或圓形的金屬錠形態保存和流通。
④ 顧頡剛認為,《周禮》不出于一人一時,可能成書于戰國時期,但是保存有早期的一些制度。《周禮》可能成書于戰國,也是多數人的觀點。張亞初等認為,從金文官制和《周禮》官制的比較來看,完全肯定和否定《周禮》是不妥當的。分別見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1979年第6輯;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版,“前言”。
⑤ 從《史記·貨殖列傳》等文獻來看,只是到了戰國時期,才開始出現私人開發銅礦、鐵礦等礦山資源的活動,出現以“冶鑄”起家的所謂“豪民”。
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主編:《銅嶺古銅礦遺址發現與研究》,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黃石博物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⑦ 黃石博物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⑧ 崔劍鋒、吳小紅:《鉛同位素考古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崔劍鋒、吳小紅:《鉛同位素考古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頁。
⑩ 本文是在20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所提出的核心觀點沒有改變,新出的科技考古的成果仍印證了筆者的觀點。可參看拙作:《商周青銅礦料開發及其與商周文明的關系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5月。
? 郁永彬、陳建立、梅建軍等:《關于葉家山青銅器鉛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幾個問題》,《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 關于西周基本社會制度,我們暫大致同意翦伯贊、趙光賢、瞿同祖等人的觀點。詳見翦伯贊:《先秦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趙光賢:《周代社會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馬曜、繆鸞和:《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 (修訂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多杰才旦主編:《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版。
? 《國語·晉語四》云:“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
? 斯維至:《論“工商食官”制度及新興工商業的作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9頁。
? 某些考古學家在討論手工業專業化時,按工匠的身份和產品的昂貴程度,分為獨立式手工業(independent production)和依附式手工業(attached production),隸屬于官府和貴族的手工業顯然是依附式手工業。
?? 趙光賢:《從裘衛諸器看西周的土地交易》,見氏著:《周代社會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附錄四。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版,編號:4187、10285、3763。
? 馬曜、繆鸞和:《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 (修訂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6頁。
? 所謂半獨立的工商業者,是指其人身仍隸屬于領主,但在繳納了一定的租金或所生產的物品后,可以半獨立于領主而進行工商業活動。
? 高明:《從金文資料談西周商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
? 孫詒讓:《周禮正義》卷12,中華書局1987年版。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譚德睿:《商周青銅器陶范處理技術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4期;廉海萍、譚德睿等:《二里頭遺址鑄銅技術研究》,《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等。
?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窯村西周遺址1974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7期;洛陽文物工作隊:《1975—1979年洛陽北窯西周鑄銅遺址的發掘》,《考古》1983年第5期。
?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 (兩周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頁。
? 狹義周原主要指周代周原遺址,大致包括岐山縣和扶風縣。本文提到的周原是廣義的,其范圍包括鳳翔、岐山、扶風、武功4縣的大部分,同時還包含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4縣的小部分。見史念海:《周原的變遷》,《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76年第3期。
? 樋口隆康主編:《日本考古學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香港東方書店1990年版,第282、315頁。
? 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文物》2011年第11期;《論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曾國青銅器的生產背景》,《文物》2013年第7期。
? 袁艷玲:《周代青銅禮器的生產與流動》,《考古》2009年第10期。
? 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所獲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雷興山、種建榮:《先周文化鑄銅遺存的確認及其意義》,《中國文物報》2007年11月30日等。
? 種建榮、張敏等:《岐山孔頭溝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性質初探》,《文博》2007年第5期。
? 周原考古隊:《陜西周原遺址發現西周墓葬與鑄銅遺址》,《考古》2004年1期;《2003年秋周原遺址(IVB2區與IVB3區)的發掘》,《古代文明》2004年第3卷等。
? 魏興興、李亞龍:《陜西扶風齊鎮發現西周煉爐》,《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1期;雷興山、種建榮:《先周文化鑄銅遺存的確認及其意義》,《中國文物報》2007年11月30日。
? 近藤晴香:《大周原地區鑄銅遺存與西周的政體》,《三代考古》第6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 曹瑋:《周原的非姬姓家族與虢氏家族》,見氏著:《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 曹瑋:《太王都邑與周公封邑》,《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3期。
?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頁。
? 王冠英:《任鼎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2期。
? 朱鳳瀚:《衛簋與伯犭臣犬諸器》,《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