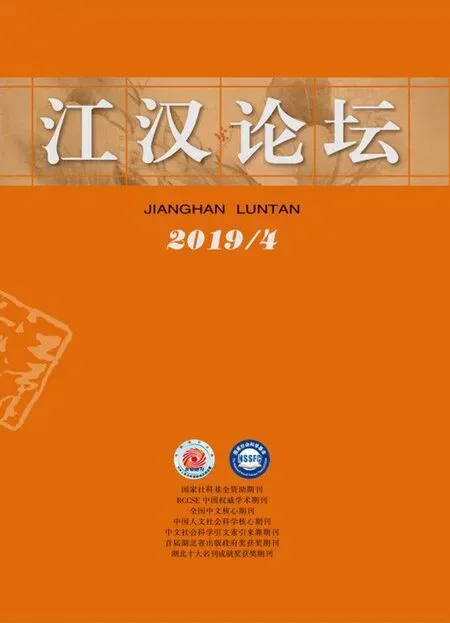區隔視角下農村“光棍”陷入貧困的過程與邏輯
——基于秦巴山區J村的調查研究
陸漢文 董苾茜
一、問題的提出
據有關研究估計,到2020年底,我國將存在3000萬隱性“光棍”。①他們主要集中在農村,且與貧困問題密切交織在一起。已有一些研究開始關注并嘗試解釋農村“光棍”的貧困問題,這些研究基本上呈現兩種解釋取向:一種是個體條件取向,將“光棍”的貧困狀態歸因于其身體缺陷、能力不足等。另一種是社會結構取向,認為是家庭、社會等外力作用導致了“光棍”的貧困。例如,有研究將“光棍”的貧困視為代內剝削的結果——農村家庭中的長子因需承擔養老等家庭責任,未能充分發揮其勞動價值,進而陷入貧困。②有研究則提出“分家散財論”——兄弟分家使有限的家庭財產一次次縮水,越晚成家的兒子從家庭中獲取的資源越少,越有可能陷入貧困。③有研究觀察到“光棍”在村莊中的“邊緣人”、“退出者”、“沉默者”處境,認為“光棍”被邊緣化的過程使其喪失社會支持,進而陷入貧困。④基于對田野經驗的把握,本文認為“光棍”的貧困狀態是社會建構與自我建構共同作用的產物,嘗試在該群體與村莊其他“在場者”的互動情境中探討其陷入貧困的過程與邏輯。
在說明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與關系時,不少研究者習慣于用韋伯的市場地位概念分析不同群體或階層社會資源與生活條件的差異,建立由收入、財產、職業聲望、權力與教育所構成的垂直分層體系。這種路徑在社會生活逐步“多元化”與“個人化”的趨勢下受到不少質疑,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到“水平的”區域、性別、年齡、種族的區隔的重要性。這正是布迪厄提出區隔思想的價值所在。布迪厄充分挖掘了生活品味的區隔功能,將品味和習性引導下的生活風格視為塑造區隔的關鍵。在他看來,生活風格是習性的有系統的產物,這些產物按照習性模式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被認識,它們變成了社會定性(“高雅的”、“庸俗的”等)的區隔符號系統。這種符號系統構成了個人和社會群體自我區分和表演的方式,也構成了社會區隔的原則。⑤從田野調研的經驗來看,盡管“光棍”在資本擁有量、社會地位等垂直的階層屬性上與已婚群體存在差別,但僅從資產、收入來區分“光棍”群體與其他群體,并不能充分把握他們的特性。“光棍”群體在生活處境、風格上與已婚群體存在鮮明差別,其內部則具有明顯的共同特征。借鑒布迪厄的區隔思想,將生活風格、品味、文化整合到一個解釋框架中,用以揭示“光棍”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分化,可能更符合該群體的特征和村莊情境。
二、“光棍”的日常生活風格:與已婚男性的比較
本研究的經驗材料來自秦巴山區J村的駐村調研。該村轄3個村民小組,共176戶,554人。全村“光棍”數量為48人⑥,占到該村30歲以上全部男性數量的19.7%;其中44人被納為貧困戶,占全村貧困戶總數的39.6%。按照布迪厄的思想,生活風格是習性的圖式系統的象征體系,是個體生活經驗在其思想和行動圖式中的積淀的外化,構成了外界辨識行動者分化與差異的標識。研究“光棍”的日常生活風格呈現,是探討“光棍”在村莊場域中與其他群體分化的邏輯起點。以下依據J村的田野材料,對30位“光棍”及30位已婚男性的居住條件、飲食消費、形象管理和信息接觸等進行比較分析。
1.居住條件
住房是婚姻市場中的重要籌碼,這一因素在J村顯得尤為突出。被調查的30位“光棍”中,有半數以上在提到自己過往的戀愛和相親經歷時都指出,“女方嫌我住處偏遠”或“沒錢修繕房子,太破舊了,人家不愿住進來”。
調查發現,“光棍”居住的房屋普遍存在著結構老化、設施簡陋、位置偏遠(到鎮上的距離更遠)等問題。據統計,房屋建筑結構為土坯、磚木、鋼筋混凝土的,“光棍”分別為9人(占30.0%)、16人(占53.3%)、5人(占16.7%),已婚男性分別為2人(占6.7%)、19人(占63.3%)、9人 (占30.0%);擁有水沖式衛生間和家用電器三件及以上的,“光棍”分別為2人(占6.7%)、17人(占56.7%),已婚男性分別為6人(占20.0%)、24人(占80.0%);住宅到鎮上的平均耗時(以摩托車為交通工具),“光棍”為58.2分鐘,已婚男性為43.4分鐘。可見,“光棍”的居住條件明顯比已婚男性差。例如,LQX(54歲)的獨居住所位于半山腰(從村委會開車前往需要20分鐘),是上個世紀40年代建造的土坯房,面積約40多平方米,未分隔飲食和起居空間。屋內兩面墻壁被柴火熏黑,僅有的幾樣家具(床、櫥柜、矮方桌、幾只靠椅)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破損。整個屋子內只有一個照明燈泡。據LQX介紹,該土房為其父母結婚時所建,LQX在此出生、長大。他現在幾乎不怎么打掃屋子,村里不會有人到他家做客,他也極少去其他村民家走動。像LQX這樣不要求或放棄居所日常打理的“光棍”并非個案。他們中的部分人在相親階段曾把屋子收拾得整潔、干凈過,但在逐漸失去迎娶媳婦的希望以后,便放棄了對房屋的精細打理。一方面,在他們的觀念中,家務活是女人干的,所以他們幾乎不主動打掃屋子;另一方面,自己的房屋在婚姻市場里已失去競爭力,結婚失敗似乎已成定局,也只有“破罐子破摔”了。用J村另一位“光棍”LYM的話說,“一個人的生活,怎么過不是過啊!”
2.飲食消費
J村家家從事傳統農業生產,村民的食材來源主要以自己(家)種植或養殖為主。被訪談者中,有19位(占63.3%) “光棍”的食材以自己種植(養殖)為主,該村已婚男性相對應的數據為15人(占50.0%)。相較之下,“光棍”在飲食上自給自足的程度更高。這是交通不便等客觀條件限制下的必然選擇,是一種“必然趣味”(沒有選擇的選擇)。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必然趣味只能產生一種自在的生活風格,這種生活風格只是由于匱乏,才被它與其他生活風格形成的被剝奪關系從否定方面這樣確定。”⑦
控制飲食在現代人尤其是城市人的觀念中,為保健、健美之必要,即管理身體(身材)之必需。在布迪厄看來,控制飲食是一種為了將來的欲望和滿足而犧牲眼前的欲望和享樂的“節制”趣味,與“民眾階級自發的唯物主義對立,民眾階級拒絕進入邊沁的快樂與痛苦、利益與代價的計算”⑧。調研數據顯示,J村“光棍”較之于已婚男性更不會控制自己的飲食,并且更不講究飲食健康,每周吃剩菜的平均次數達到6.6次(已婚男性為3.4次)。
3.形象管理
“展示自我和外表是支配身體和表現身體的合法方式,身體是符號的持有者,也是符號的生產者,這些符號由與身體的關系記錄在它們可被感知的實質里……身體很可能得到與其主人在其他基本屬性的分布結構中的位置嚴格地相稱的一種價值”⑨。在不同場域中,管理自我形象的外化形式存在差別。本研究將“光棍”與已婚男性對自我形象的管理操作化為他們在自身干凈與整潔以及服飾裝扮上的實踐。
由于J村村民的職業分化并不大,“光棍”與已婚男性在服裝樣式上并無明顯的區分,但在自身干凈與整潔上則存在差異。“光棍”群體(尤其是年齡稍長者)更容易漠視自己的身體呈現出來的狀態,更容易忽略對自身形象的管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手指甲縫里都積了污垢,頭發沒怎么梳理過,衣服上有污漬,會在接受訪談期間用手擤鼻涕,然后甩在地上或擦在衣服角。他們更少使用清潔產品清洗身體,洗澡、刮胡子等的頻率更低。被訪談者中,使用清潔產品清洗身體的“光棍”數量為22人(占73.3%),已婚男性為27人(占90.0%);在夏季一周甚至十天才洗一次澡的“光棍”為18人(占60.0%),已婚男性為12人(占40.0%);一周甚至十天才刮一次胡子的“光棍”為24人(占80.0%),已婚男性為17人(占56.7%)。另外,“光棍”在服飾裝扮上的消費也相對更少。
4.信息接觸
結合村莊的實際,本研究主要從移動媒介的使用上考察“光棍”與已婚男性在信息接觸上的差別。調查表明,J村“光棍”相較已婚男性對媒介的關注度更小,通過媒介與外界接觸的頻率更低。被訪“光棍”中,有12人(占40.0%)不會使用微信、QQ等聊天軟件,有12人(占40.0%) 不會用手機瀏覽新聞,有10人(占33.3%) 不用手機上網,被訪已婚男性中相對應的數據分別為9人(占30.0%)、7人(占23.3%) 和6人(占20.0%),差異比較明顯。
以上比較分析表明,J村“光棍”的日常生活風格與其他人所認可并執行的一套文化規范和約束機制是相悖的。這種風格并非“光棍”與生俱來,而是他們的發展經歷所塑造的。例如,“光棍”不重視自身形象管理大多是結婚希望徹底破滅之后的結果,而缺乏女主人的監督和照顧,則進一步強化了他們自身生活的“失控”狀態。當“光棍”所秉持的生活風格成為一種負面因素時,這種風格進一步扼殺了他們未來的成婚機會,并逐漸積淀為生活慣習。
三、區隔:“光棍”與其他群體的關系及其建構
居住條件、飲食消費、形象管理、信息接觸是日常生活實踐的基本面向,這種日常生活實踐不僅塑造了群體分化,而且構成社會分化的表達渠道和強化機制,突出了“光棍”與其他群體的邊界和區隔。在J村,這種區隔主要表現在日常生活、儀式性人情往來以及村莊公共參與等方面。
1.日常生活的區隔
在J村,相較于“光棍”,其他群體尤其是居住地理位置距離較近的群體來往互動比較頻繁。他們習慣于在村莊公共領域中展現自我,熟悉與自身處境相似的人,以此來加強對自身位置的認同。這些都會轉化為村民個體社會心理層面的結構關系認知,他們的日常生活判斷和選擇會受到這種認知的指引。
對于“光棍”來說,他們中的大部分與其他群體的住宅距離較遠。在J村,隨著自身經濟條件的改善,不少原先居住地理位置較偏僻的家庭都搬遷至村莊居住相對密集的區域。居住的位置決定了外出打短工、購買生活用品、孩子上學以及與村中其他人來往的便利程度,因而住宅的地理位置也成為談婚論嫁時考慮的重要因素。J村不少“光棍”居住的位置都較為偏遠,這一方面構成了其娶不到媳婦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光棍”與其他人來往的心理距離。實地調查中,許多“光棍”都表示自己平均每周“串門子”的次數只有一兩次,不會去其他鄰居家吃飯、聊天,也不會邀請鄰居來自己家做客。說到原因,有代表性的說法是,“我什么好煙好酒都沒有,拿什么款待人家”,“你看,家里連個坐的干凈地方也沒有”,等等。
對于其他村民來說,“光棍”并不在他們主動來往的對象范圍內。他們不會邀請“光棍”到自己家中,也不會主動去拜訪“光棍”。他們與“光棍”的交情通常止步于見面打招呼或簡單寒暄。缺乏認同和信任是一些村民對“光棍”的區隔化最直接的體現。例如,不止一位已婚男性被訪者提到,某“光棍”出現在公共場合時衣衫不整,T恤的扣子不扣嚴,褲子的腰帶和拉鏈也是松的,看村中年輕女性時眼神有點怪。在任八年的村支書LSJ則認為,“這種心術不正的‘光棍’在本村是極個別的,而大部分村民都因為這個對幾乎所有的‘光棍’心懷戒備。”可見,單個不符合文化規范的形象的出現,在其他人的心中打上了關于所有該身份的人的形象烙印,從而造就了對“光棍”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指引著村莊中的其他人與“光棍”保持交往的距離。
2.人情往來的區隔
在J村,村民們都有自己的人情圈,而部分“光棍”隨著與其他村民日常生活交往區隔的加深而呈現出漸漸縮小甚至退出人情圈的趨勢。在J村“光棍”中,與父母或其他家人一同居住和半工半農者的人情圈規模未見明顯縮減。和家人共同生活的“光棍”的人情圈承續著自身家族人情來往的任務。半工半農的“光棍”則因務工需要,保持著與外界的人情紐帶。而獨居的、只事農務的“光棍”,則幾乎失去了參與人情交往的主觀意愿和內在動力。
一般來說,儀式性人情發揮著村莊社會整合的功能,村民之間的關系在人情往來中得以建構和維系。而對“光棍”的刻板印象,導致部分村民保持著與“光棍”交往的距離,因而在請客等事宜上也會對“光棍”群體有所回避。還有村民站在體恤“光棍”的角度提及,“‘光棍’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不好意思要‘光棍’的禮金。又怕因拒收禮金而顯出對他的歧視,所以干脆就不請了。”
在儀式性人情活動中,大部分家庭在投入與回報行動的交替中總能維持著總體費用的平衡。“光棍”在村莊儀式性人情的大圈中處于邊緣位置。首先,“光棍”(尤其是獨居的“光棍”)在人情交際中的劣勢體現在其投入與回報的明顯不平衡上。一般家庭請客、辦酒席的次數要遠多于“光棍”,婚事、喪事、添丁、祝壽、升學、搬遷發生在一個普通家庭的概率遠遠大于無妻無子的“光棍”。因而“光棍”參與人情往來的活動注定在總體上呈虧錢狀態。退出或縮小人情圈成了經濟條件有限的“光棍”的理性選擇。另一方面,被邀請參加宴席并不總能給“光棍”帶來美好的情感體驗,尤其是在參加年齡相仿的男性的婚宴、孩子的滿月宴等場合,在人家生活的圓滿和自身生活的殘缺的對照中,“光棍”只能獨自體驗心中的失落和苦悶。
3.村莊公共參與的區隔
在J村,“光棍”對政治和公共事務的參與缺乏積極性。“在所有村里人里面,對村里頭的事情最漠不關心的就是‘光棍’。”村支書LSJ在訪談中說,“入黨不積極,參加村里組織的技能培訓不積極,參加其他活動也不積極,連讓他申請貧困戶,享受國家政策都不積極!他們的申請材料都是拖到最后才交,這還是我親自登門磨破嘴皮的結果。”
J村48位“光棍”中,有44位(及其家庭)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為111戶)。這些受國家精準扶貧政策幫扶的“光棍”是村民經過民主評議選出來的,他們在經濟收入上位于村莊社會的最底層。為什么“光棍”在申請貧困戶的過程中缺乏積極性?調查發現,一方面,大部分“光棍”都對自己的生活現狀表示滿意,這一點本文將在接下來的部分具體闡述;另一方面,不知曉、不熟悉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因而很難將國家扶貧政策與自身利益聯系起來,是他們主動意愿薄弱的重要原因。訪談中,有30%的貧困“光棍”說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年被定為貧困戶的,20%的貧困“光棍”說不出自己的幫扶責任人的名字(經核實,排除幫扶負責人未與該“光棍”接觸的情況),還有20%的貧困“光棍”不知曉對困難群體的幫扶政策。連自己的直接利益都不去主動爭取,村莊的其他政治活動,如村委會班子選舉、黨員評選等更是難見“光棍”的身影。
四、區隔階段論:農村“光棍”陷入貧困的實踐過程
一些研究“光棍”群體的學者將“光棍”的貧困處境視為被社會排斥的結果,這只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上文對“光棍”社會區隔的剖析清晰地表明,“光棍”還有一個主動與其他群體區分的動機與過程。他們正是在被隔離與自我隔離的雙重作用機制下,在弱勢累積的過程中落入了貧困的陷阱。
1.區隔第一階段:“人生任務”消解,發展目標缺失
為了全家人的未來而共同努力,正體現了家庭作為社會發展動力源泉的價值。一旦男性無法成家,并且自己也接受了這種局面,那么對于他們來說,為家庭而奮斗的目標消失了,同時也就意味著“過日子”的動力喪失了。成家、生子、教子不再構成他們的人生任務,而基于此的生活動力也就此消解。在農村,子女從出生到成年的近20年間,從日常生活支出到教育花銷,都是父輩沉甸甸的責任。此后,父輩還需要為子女(尤其是兒子)成家攢錢置業,以及幫助撫養孫子女。在J村,兒子娶媳婦的負擔包括彩禮、買(或建)及裝修房子、辦酒席等,一個普通家庭在這方面的花銷大概在20萬元左右。這些“任務”構成了已婚男性的責任和生活動力。
而對于“光棍”來說,他們只需要贍養家中老人,或只需顧及自身溫飽,所需的投入是極少的(大病患者或長期慢性病患者除外),“光棍”的拼搏動力因此也大為弱化。例如,WJP(32歲)身體健康,家庭原有四口人,父親、母親、兄長和他。初中畢業后,他跟隨父親和哥哥一起去秦皇島打工。那幾年間家庭收入比較可觀,村里一直有人給他們兄弟倆介紹對象。八年前,其兄長順利娶到了媳婦。不久后,其父親因病離開了人世。哥哥娶親加上父親得病,家里的積蓄花光,還倒欠親戚幾萬元。父親的去世給了全家人沉重的打擊,自那以后WJP便辭工回家和母親一起生活。原先積極給他介紹對象的人沒了蹤影。嫂子托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女孩,對方聽說他沒有穩定收入,又沒有錢蓋新房,就婉拒了。WJP還追求過自己的初中同學,對方在鎮上的小超市做收銀員。兩人交往了半年,最后因為女孩家里不同意,被迫分手了。至此,WJP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也沒有了發展的目標和動力。
2.區隔第二階段:自我區隔,退出村莊競爭
在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乎個人及家族的社會地位及聲望,競爭所獲的優越感也被稱為“有面子”。社會競爭不僅是個體在熟人社會中實現社會價值的必然路徑,也是個體認真“過日子”、追求上向流動的動力。“光棍”感覺“丟面子”以及退出村莊競爭,是從其“人生任務”消解開始的。由于沒有成家立戶,因而失去了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資格”,這使得“光棍”失去了與其他村民攀比、競爭的基礎,進而導致其走上了自我區隔的道路。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消極出世”:生活在“真空”或自我世界中的“光棍”,不在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不追求他人認同和肯定,也不會為了“面子”參與社會競爭。
“消極出世”也是“光棍”在自我形象管理、居住環境打理、飲食選擇等方面呈現出特異性的原因。因為缺乏保健和管理身體(身材)之社會性必要,“光棍”基本不會控制自己的飲食,也不看重食物的質量。因為很少與他人近距離接觸,他們也不用考慮自身的干凈與整潔。因為不主動串門,不邀請鄰居做客,他們同樣沒有必要認真打理住宅環境。
3.區隔第三階段:自我隔離與被隔離的雙重作用,發展機會減少
日常生活、人情往來與村莊公共參與等方面的區隔不僅共同消解著“光棍”在熟人社會中的競爭意識,同時也消解著“光棍”的社會網絡和人情紐帶,減少了他們發展的機會。
由于相對偏遠和封閉,J村的社會分化不嚴重,村民比較團結。作為村內相對弱勢的群體,“光棍”一開始也沒有受到其他村民的排斥與擠壓。但是,由于“光棍”不愿打理居住環境,不愿管理自身形象,不愿遵循大多數人奉行的自我約束規則與規范,結果只能是將自身從集體中分化出來,成為村莊中的“另類”群體。他們拒絕融入,從此失去接納;拒絕信任,從此失去信任;拒絕幫助,從此失去幫助。J村大學生村官ZJF(24歲)說,“這里一直延續著農忙時互助的傳統,就是如果你家地里頭的活忙不過來了,會請家中有剩余勞動力的鄰居幫忙。不會付工錢,但是會記下人家幫忙的天數。等到人家需要幫忙的時候,你也會主動去幫的。但是我們這里有幾個單身漢是例外的,他們的地少,一個人就忙過來了,根本不需要別個的幫助。所以你也別想找這幾個人幫忙。”這種情況下,萬一到了需要別人幫忙(如介紹工作)的時候,也就沒有人愿意幫他們了。本來就存在人力資本不足問題的“光棍”,因自我區隔而導致社會資本減少,因而更難踏上“發展的階梯”。因此,J村許多“光棍”都選擇長期呆在村中從事簡單生產,這正與他們缺乏社會資本及相關的發展機會有關。
4.區隔第四階段:慣習的形成與再生產
慣習是由積淀在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所構成的,其形式為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光棍”的慣習實踐決定了其生活風格。如前所述,“光棍”的住所經歷過干凈、整潔的階段,而在被相親對象拒絕后,他們不再認為在清理、打掃上付出勞動是值得且必要的,于是走向放任。而這種放任一旦成為慣習,便塑造、組織實踐,生產著歷史,用布迪厄的話來說,它是一種“外在性的內在化”。對于“光棍”來說,自我放棄構成了一種漫長的放棄活動,致使他們順應自身的條件和處境,放棄不去努力實現而被認為不可實現的所有希望。
調查發現,適應了自我放棄心態的“光棍”,呈現出對安于現狀的宿命型生活的滿意狀態,建構出一種貧困文化并沉溺其中。這種文化具體表現為聽天由命、消極無為的人生觀,安于現狀、好逸惡勞的幸福觀,不求更好、只求溫飽的消費觀等。以LJC(40歲)為例,他身體健康,初中學歷,種了三畝核桃,自家門口種了半畝菜地,偶爾去鎮上打短工,大部分時間泡在鎮上的麻將室里。在他看來,自己“不需要長期在外面干活啊,現在外面老板都黑得很,經常拖欠工資的。做短工多好,按工時結,當天干完當天領錢,不怕白出力”。“也沒必要和他們(有家室的男性)一樣累死累活地成天在外干活啊,一個人花掙那么多錢干嘛,又帶不進棺材!”又如,WDC(55歲)與80多歲的母親一同居住,身體健康。兩年前其母親中風導致偏癱,長期臥床。WDC家中原有7畝地,流轉給自家親戚了。2015年底WDC家被定為低保貧困戶,家庭生計來源為母親的養老金、兩人的低保收入以及逢年過節時村委會及幫扶干部送來的慰問金和慰問品。WDC只打理家門口的7分地,種了豆角、黃瓜等幾樣蔬菜。種菜以外的時間,他喜歡坐在門口曬太陽,發呆。他稱自己很享受并感恩政府讓他過上了這樣“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
五、小結與討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年均減少貧困人口1300多萬,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剩余1000多萬貧困人口多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最后兩年的脫貧攻堅面臨諸多特殊挑戰。農村“光棍”是一個特殊的困難群體,其陷入貧困的過程和原因對于認識我國剩余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特別是對于認識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具有啟示意義。通過比較農村“光棍”群體與已婚男性在居住條件、飲食消費、形象管理、信息接觸等方面的情況,本研究發現這些日常生活實踐不僅構成了“光棍”與其他群體的分化,也建構著“光棍”與其他群體的區隔。在區隔的第一階段,“光棍”因人生任務的消解而喪失發展目標和動力;第二階段,“光棍”由于丟了“面子”,一步步退出村莊競爭,走向自我隔離;第三階段,在自我隔離與被隔離的雙重作用下,“光棍”的個人發展機會減少;第四階段,區隔逐漸內化成“光棍”的慣習,“光棍”陷入貧困的“牢籠”。
既有的對農村“光棍”貧困成因的探索大體可區分為個體條件與社會結構兩條解釋路徑。第一種路徑聚焦于貧困的個體性原因,認為身體缺陷、人力資本匱乏以及懶惰、不思進取等因素導致了“光棍”的貧困;第二種路徑強調“光棍”的貧困是社會造成的,包括“代內剝削論”、“分家散財論”以及“社會排斥論”等不同觀點。前者無法解釋那些旨在提升“光棍”個人能力的扶貧政策未取得預期效果的現實;后者無法解釋在同樣的社會環境里、同一個村莊中,為什么大部分家庭沒有出現“光棍”現象。本研究認為,“光棍”的貧困問題是在特定的實踐過程中演化出來的,是“光棍”本人和其所處社區互動的產物。脫離“光棍”貧困的生成過程,就無法正確理解其內生動力不足的合理性,也不可能找到對其開展精準扶貧的路徑。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路,本研究建構了“光棍”自我區隔與社會區隔的分析框架,揭示出“光棍”在區隔歷程中陷入貧困的邏輯。
以往旨在化解農村“光棍”困境的對策主要集中在開展技能培訓、支持產業發展、提供就業服務等方面,但“光棍”群體常常缺乏參與相關扶貧項目的積極性、主動性。在扶貧實踐中,很多人將這種困境歸結為“光棍”群體“等、靠、要”的思想嚴重。本研究表明,“光棍”群體的貧困關鍵不在于“貧”,而在于“困”,因此治“貧”的措施必然得不到積極回應。解決“光棍”等群體的貧困問題應從治“困”入手,把他們從區隔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一條可行途徑是,引導“光棍”群體尋找和重新確定生活目標,如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公益事業建設等,讓他們在回歸社區和社會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除了娶妻生子可以讓生活變得有念想、有期待外,還有很多“事業”同樣可以成為超越個體生存的價值追求。不過,這是一項需要下“繡花功夫”的治“困”事業,由現有村治體系來承擔可能會面臨很多問題。設置專門的社會工作崗位,引入職業社工或志愿服務,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注釋:
① 劉燕舞:《幾千萬光棍的社會風險》,《南風窗》2014年第14期。
② 陶自祥:《代內剝削:農村光棍現象的一個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長子打光棍的調查》,《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③ 李艷、李衛東、李樹茁:《分家、代內剝奪與農村男性的失婚》,《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
④ 何紹輝:《社會排斥視野下的農村青年婚配難解讀——來自遼東南東村光棍現象的調查與思考》,《南方人口》2010年第4期;余練:《多重邊緣者:基于對D村光棍群體社會地位的考察》,《南方人口》2011年第6期;韓慶齡:《結構邊緣與文化排斥:農村“老實人”光棍的社會形成機制》,《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⑤⑦⑧⑨ 布迪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71、281、286、301頁。
⑥ 根據農村地方性共識,男性青年一般年齡超過30歲還未能婚配,就基本可以斷定,他們這一輩子都可能要過沒有妻子的單身生活。即使有少數男性有可能在超出30歲以后還能婚配,但因其數量很少,所以也不影響對“光棍”的界定。在本研究中,“光棍”就是指年齡超出30歲尚未結婚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