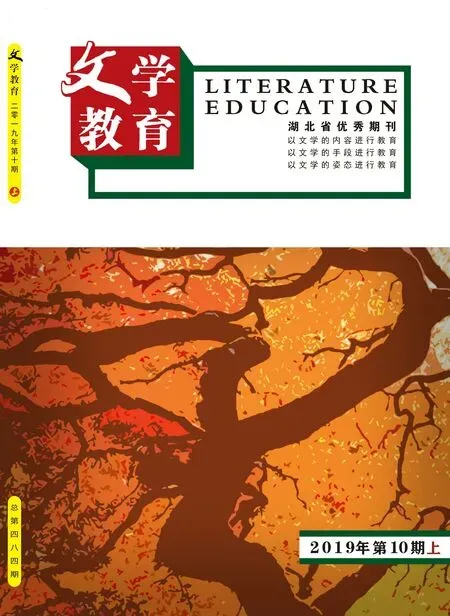《生死場》的文學地理學解讀
麥合普拜木·阿卜杜熱合曼
文學地理學是研究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學事象的分布,變遷及其地域差異的科學。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及其空間要素,結構與功能,內涵與價值,文學區的分異,特點和意義等。
《生死場》是蕭紅代表作,用充滿感情的筆調書寫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東北鄉村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與貧苦無告的生活,講述了人和動物相似的怵目驚心的“生”與“死”的凄涼。我國黑龍江這片黑土地上的呼蘭鎮獨有的生物,水文,氣候,地貌等要素在小說里充分得到了體現,使之富有了獨一無二的文學地理蘊含。
一.《生死場》中的自然地理空間建構
文學作為人類一種重要的精神活動內容與生命存在方式,毫無疑問會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開篇即云:“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①劉勰所講的“文”雖然包含了多種文體,但主要是指文學,而“天地”就是指自然環境。文學既然是與天地并生的,那么它與自然環境的聯系就是一種天然的聯系了。
地理空間是形成作家創作風格的自然環境,更是作家“精神原鄉”的生成背景。當年的北方農村,確實如《生死場》所勾繪的那般,都是泥土草房,籬笆墻,轆轤井,紙糊窗,寥落的屯子灑澆在荒涼的黑土的原野上。在《生死場》中,麥場,菜圃,荒山,墳場,鄉村,這些小空間都組成了故事的一個大空間輪廓。各種相對獨立的自然環境場景的參照構成了故事的章節,同時,也成為了故事的空間。在蕭紅筆下,生活在村莊這個大空間里的種種生物,如動物,植物,人物,他們的生存方式一直都要依賴大自然。
地理空間是人類生存活動的場所,“文學地理學”就是探討文學和人文地理空間的關系,關注人在地理空間中是如何以審美想象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生命表達。文學進入地理,實際上是文學進入到它生命的現場,進入了它意義的源泉。縱觀《生死場》就可發現,他的作品既有堅實的故事基礎,又有一定的場景基礎。在小說里蕭紅精心建構的“麥場”和“墳場”這兩個地理空間既是寫實的,又具有很強的永恒意味的象征性,與人物的命運緊密相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人,或者是動物的繁衍后代的對比性描寫想要揭示的并不只是貧苦中的人民的麻木性,人的生育和狗,豬的生殖的“共時性”,更是兩者間的“同質性”。
在這獨特的地理空間里“生”和“死”意識完全融為一體。這里人民的生活根本談不上自覺性的,甚至可以說是動物性的。很多生命猶如動物盲目地生出來,在大自然中毫無意義的生存下去,后來就麻木的走上了死亡之路。譬如,“刑罰的日子”這一節中,“生死場”的“場”里“生”與“死”集中體現了其特殊內涵。在這里,無論是人還是動物成產都是對母親的刑罰,人的生育甚至不如動物的,婦女們對無法抗拒的生育充滿恐懼。
再比如,當王婆三歲的女兒小鐘摔死在鐵犁上的時候:“……啊呀!……我把她丟到草堆上,血盡是向草堆上流啊!她的小手顫顫著,血在冒著汽從鼻子流出,從嘴里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斷了。我一聽她的肚子還有響;那和一條小狗給車輪軋死一樣。”②在這段描述中,可見王婆竟然對親生女兒悲哀和血腥的事件,卻根本不當一回事似的在敘說,“你們以為我會暴跳著哭吧?我會號叫吧?起先我的心也覺得發顫,可是我一看見麥田在我眼前時,我一點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淚都沒躺下。”③王婆講出來的這段敘述,鮮明的展示著她的價值觀,對王婆來說,人的價值遠遠不及于麥田,菜棵,茅草的價值。
二.《生死場》中的人文地理建構
人文地理學把政治地理,經濟地理成為廣義的人文地理;把文教地理(教育,人才,學風等)和風俗地理(方言,民俗,風氣,習慣等)稱之為狹義的人文地理。廣義的人文地理與狹義的人文地理都能對人類的生活和思想構成影響,但是比較而言,廣義的人文地理對人類的影響,遠不及狹義的人文地理那樣深刻和持久。
蕭紅代表東北文學區以及“東北作家群”,在全國有重要影響。東北古今文學的地域特色非常鮮明,在東北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一股頑強生命力是始終貫穿于其中的。這種生命力是人類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種存在。早期的人民,面對著荒蕪的土地,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在這里無法體會江南水鄉般的境界,這里的人們需要培養起一種頑強的意志和的心態,才可以熬過漫長的冬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少有人能夠只靠自身來生存和發展,群居的生活便給他們提供了這樣互助的機會,這樣便形成了東北人熱情且樂于助人的性格。
東北區域的特色,黑龍江冬季寒冷干燥的氣候,致使人們對抗的依戀。這里冬天沒有一家不會不靠燒炕,燒火爐抵抗寒冷,火炕就成為了人們存在與生活必不可少的空間,發揮著它獨有的社會屬性。“荒山”那一章節開頭就說:“冬天,女人們像松樹籽那樣容易結聚,王婆家里滿抗坐著女人。五姑姑編麻鞋,她為著笑,弄得一條針丟在席縫里,她尋找針的時候,做出可笑的姿勢來,她像一個靈活的小鴿子站起來在炕上跳著走。”在小說里的冬天,鄉民婦女聚在王婆的炕頭上,打發著冬閑季節。農民們不能種植,不能像其它季節一樣忙農務,因此,婦女們相當輕松的聚在一起,呈現出了炕頭上閑聊,編麻鞋的既熱鬧又輕松的氛圍。還有在“荒山”里,村里最美麗的女人月英患著癱病整整一年在炕的當心坐著,日日夜夜動彈不得。最后全身臟污,孤獨,無望,凄慘的死在炕上。
小說中人的吃住,生死都離不開炕,人出生在炕上,生病躺在炕上,死去時從炕上離開。其實這一切看上去似乎是平凡的事情,但都離不開炕所打造的世俗空間性和炕的神圣性。
三.特定地理環境下的女性形象書寫
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每一個民族的氣質中,都保存著某些為自然環境的影響所引起的特色(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譽為東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議的里程碑作品《生死場》,描繪的是呼蘭河之東的一個小屯。呼蘭河,是祖國北方的著名水系,它作為為松花江的支流,位于黑龍江省之腹地。呼蘭河小鎮是《生死場》的創作背景,也是蕭紅出生成長的環境。這一地理背景深深植根于作者的大腦,它已成為蕭紅情感的寄托,也為《生死場》的問世提供了肥沃的土地。
在《生死場》里農村底層的人民,在特定風物氛圍中,表現出了那塊災難深重的黑土地痛苦,無助,麻木的人性。小說的前半部著重書寫了當地鄉民在“自然暴君”和“地主暴君”的欺壓之下,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悲慘處境,作品主題意蘊豐厚,深沉。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廣大貧苦農民無力抗御自然災害的侵擾,更難以忍受封建地主階級的重壓與剝削。至于作品里的女人,處境就更難以言表了。她們除了抵抗“自然暴君”,忍受“地主暴君”以外,還要忍耐自己男人的種種欺凌。她們在作品中被塑造成了了眾多受男性世界壓迫,從而只能生活在暗天無日下的,命運悲慘的女性形象。
首先談談性格比較突出的女性王婆。她不像小說里的其他女性,在幾千年傳統的壓制下早已丟失了反抗的能力,默然忍受著一切。王婆在是一個嫁過3個丈夫的不幸婦女。為了擺脫丈夫的欺辱,尋求自己應有的權利,帶著兒女離開了第一任丈夫改嫁,并且在第二任丈夫死去后她又嫁給了趙三。之后,在日常的勞作與生活中,王婆也爭取與趙三在人格上的平等。王婆一生中有過三個孩子,但他們卻先后死去,這無疑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事。這三個孩子的死讓我們看到了王婆的堅強和其富有的反抗精神,也讓我們看到她是怎樣一步步由麻木走向了反抗。
整本小說中最令人不由毛骨悚然的無疑是對于王婆自殺的情景的描寫。她的兒子因為當“胡子”而被抓去殺掉。王婆這次沒能繼續將自己的身心一貫放在田地里,而是選擇了服毒自殺。她之所以選擇死是因為她最終感到了生的無意義和所受苦難的無價值,而不是因為她內心的軟弱或者對兒子之死過度傷心。王婆在兒子死后竟酗酒起來,她每天釣魚,全家人的衣服她不補洗,她只每夜燒魚,吃酒,吃得醉瘋瘋的,滿院,滿屋地旋走。王婆縱情發泄著她喪子的痛苦,而停止履行她本該的義務。她從不無條件順從丈夫,向男權社會低頭。她注重尋求自己的個人權利,表達自己的情感,敢于反抗。
其次,《生死場》中的其他女性,如金枝、月英、麻面婆等。無一不是對自己丈夫無條件順從的。金枝因婚前失節而倉皇嫁給了成業,婚后過著并不幸福的生活,經常挨打受罵,她也默默忍受下來了。后來即使女兒被暴躁的丈夫摔死,她也只是怨自己的命不好,生吞氣人地繼續過了下去。月英是打魚村最美麗的女人,可自從她患了癱病后,不能勞作的她便遭到了丈夫的冷漠對待,最后在丈夫的折磨下凄慘地死去。
綜上所述,作者成長的環境,曲折的人生經歷和特殊的生命體驗使她對周圍生命,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困境有了非同常人的關注。
四.結語
《生死場》中的地理空間的建構絕不僅僅是提供一個描述和反應意義上的地點,它對小說情節結構的設置和人物性格復雜性內涵及悲劇命運的展示都具有推進和渲染的作用。這里的地理空間還往往是作為一種精神建構而存在,是關于地理空間建構與生活表征意義的觀念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