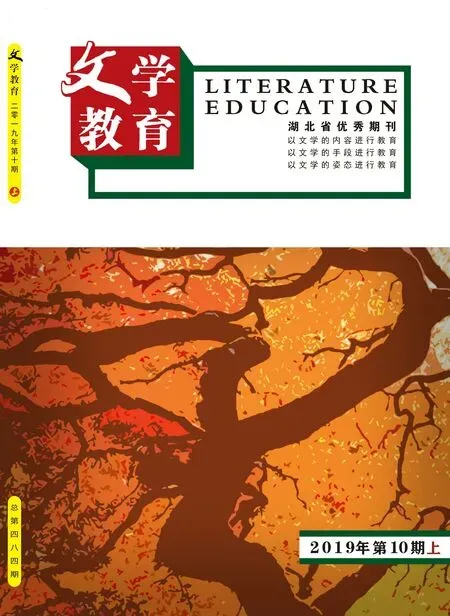黑格爾《美學》中的心靈觀
關雅玲
一.心靈觀與對人體心靈的肯定
“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在黑格爾的美學思想中,只有理念是最高的真實,是世界真正的本體。理念是概念與現象的統一,理念經過自在階段發展到自為階段,再進一步返回自身,達到自在自為的階段。這是黑格爾一直在遵循的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律,是黑格爾整個哲學體系的依據,而黑格爾的美學體系也是在此邏輯之下的產物。達到自在自為階段的理念,就可以說是絕對的理念。這種理念是無限的、絕對的、自由的、獨立自足的,種種普遍的精神力量存在于其中,蘊意著最高的真理,也是他所說的“絕對心靈”。
“心靈”一詞在黑格爾的《美學》中作為認識的主體,同時也作為認識的對象,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們要按照它的真正的實質去簡略地說明絕對理念,我們就應該說,它就是心靈,當然不是有限的受制約、受局限的心靈,而是普遍的、無限的、絕對的心靈,這絕對的心靈根據它本身去確定真實之所以為真實。”[1]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就是心靈,在普遍性、特殊性與個體性三個范疇之中,人類心靈擁有普遍性,并且它的具有普遍性的內在本質方面和特殊個體的外在現象方面可以相互滲透。因為在生命的有機體中,靈魂與身體的統一,就相當于內在本質與外在現象的統一,相當于概念與實在的統一。“靈魂把生命灌注在身體的各部分之中”[2],哭泣時全身肌肉的抽搐,開心時五官的舒展,全身每個部分都在展現著當時的感覺,但是作為整體的人的心靈是唯一的感覺主體。黑格爾的心靈觀遍布著他對于普遍性、特殊性與個體性的哲學思辨。
黑格爾的心靈觀也是他對審美主客關系的理解,對主觀的自確定作用的肯定。“心靈認識到它的有限性,這本身就是對它自己的否定,因此就獲得它自己的無限。”[3]“絕對本身變成了心靈的對象,因為心靈上升到了意識的階段,就在它本身中分辨出知識主體以及與此對立的知識的絕對對象。”[4]有意識的心靈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認識的對象。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理念就是絕對,就是心靈或精神,不是某個別人的心靈而是彌漫宇宙的、普遍的、絕對的無限心靈。這絕對心靈是自在自為的,憑自己的活動而自生自發自確定的。他是認識和實踐的主體,它認識與實踐的對象是由它自己生發的。“只有受到生氣灌注的東西,即心靈的生命,才有自由的無限性,才是在實際存在中對本身為內在的,因為它在它的外現里能回顧本身,停留在本身。”[5]因為只有心靈才是自由的、無限的,它自由自覺,思考自身,從而能以本身作為認識的對象。
黑格爾將人體奉為最完美的自然形式,首先是從人的身體構造方面,人的五官跟肢體作為部分,都有各自的特殊性,而人體生命機能使各個身體部分統一在一個軀體之上,人體就是整體與部分的統一。但這種統一又不是拋棄了各個部分的特殊性的統一,不是像自然界的礦物質一樣,每個結晶組合在一起成為了一整個的結晶體,但將結晶體的一小部分截取下來,結晶體與截取下來的結晶仍然保持著本來的性質而不發生改變,沒有灌注生氣的體系。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6]當手臂被砍斷,它便失去了生氣,既不是具有特殊性的個體,也不再是整體中的一個部分了。
黑格爾將人體的構造作為例子,來闡釋自己的整體與部分和部分與部分的哲學。但是人體要達到完美,在人體構造之外還應有生氣的灌注,有人類心靈的參與。人類的心靈作為最高實在,最高真理的研究對象,“‘人’這個概念包含感性與理性,身體和心靈這些對立面,但人并不是由兩兩并立、互不相關的對立面混合而成的;按照人的概念,人就是這些對立面所結成的具體經過調和的統一體。”[7]心靈的自確定運動使人實現自己,在無窮的生發之中又進行無窮的否定,以促成自我發展與更高階段的實現,這種從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個別性的發展進程,也是矛盾的和解過程。黑格爾對人的心靈的觀點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對人本身價值的肯定是每一個歷史階段向前運動發展的動力,正是因為人類心靈要求不斷追尋意義與價值,不斷解開現世的困惑,科學、哲學與藝術才能夠不斷與時俱進。
“人的全部心情連同一切感人最深的東西,人心里面的一切力量,每一種感覺,每一種熱情,以至胸中每一種深沉的旨趣——這種具體的生活就形成了藝術的活生生的材料,而理想也就是這種生活的描繪和表現。”[8]
黑格爾對于心靈的觀點由始至終結合著他的哲學思想體系。對人的價值的確定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而黑格爾的缺點在于將理念的自我深化運動圈囿于理念自身的運動,要依靠理念自身的自確定作用,使理念回到自身,達到主客觀在自在自為的更高階段的統一。
二.心靈的定性——靜穆與鎮定
黑格爾在《美學》中提到,理想的定性就是理念由普遍概念轉化為具體客觀事物,其中各部分受到不同的定性,彼此分立而且對立。這些差異面或對立面在藝術中應達到統一。[9]理念經過自我發展形成藝術作品。心靈的定性,也即理念達到自我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在普遍性實現自身于特殊個體之中,心靈于是成為一個統一體,成為絕對心靈。
黑格爾提到一種叫做“神性的東西”,也即是他所說的普遍力量,內化的心靈實體。這種心靈實體是理想藝術的領域。他說,“無論神性的東西怎樣具有統一性和普遍性,它在本質上也是具有定性的;它既然不只是一種抽象概念,也就應具有形狀可以供人觀照。”[10]于是,理想藝術首先體現于普遍的神性,其次體現于人的心靈活動,最后體現于人的一般生活和活動,這樣就達到了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從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個別性的藝術理想的自我深化運動,即心靈實現了自己,取得了定性存在。
心靈達到定性存在的狀態是自在自為的,即理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里,理想不僅外顯于現象世界,而且還能還原到它本身,并將外在世界也納入它本身。這種氛圍里的理想是“自由自在,自足自樂”[11]的。就像沐浴在“福氣的歌聲”里,始終有這種歌聲籠罩著心靈,就像一種無形的凝聚力將分散游離的靈魂團結在一個結界中。“外在形象無論多么廣闊,理想在它里面都不會喪失它的靈魂。”[12]它守住了自我的鎮定。因而,心靈的這種最高狀態的表現形態是理想的靜穆,“要想達到理想的最高度的純潔,只有在神、基督、使徒、圣徒、懺悔者和虔誠的信徒們身上表現出沐神福的靜穆和喜悅,顯得他們解脫了塵世的煩惱、糾紛、斗爭和矛盾。”[13]這種靜穆與鎮定體現在黑格爾對藝術作品的要求上,只有本身和諧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藝術,就連在嚴肅中也帶著和悅的基本基調,黑格爾稱這種理想的藝術形象為“有福氣的神”。而那些反映殘暴、災禍、嚴酷的暴力以及橫暴的強權,純然反面的東西令人覺得空洞無味與厭惡,單純的罪惡、嫉妒、怯懦和卑鄙惹人嫌惡。因此黑格爾反對莎士比亞的悲劇,并覺得《李爾王》中盡情渲染著罪惡,是時一種“對惡劣的幽默,一種離奇的滑稽”[14]。
而古希臘神話中的神,卻一直保持著他們不可磨滅的純潔無瑕的崇高性格,他們處在靜穆與不動情的狀態,擺脫了塵世的禁錮,沖破了外在條件的束縛,從而達到一個自在自為的狀態,一種靜穆的狀態。“這種永恒的無為自守的安靜,這種安息就是理想本身的定性。”[15]而這種靜穆怡悅狀態中含有能取得任何定性或發生任何動作的潛能,擁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正如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中所言,“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這種自然的流露是在強烈情感發生之后,進行了沉淀,最后流露出來的沉思之后的情感。“……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味的情感。這種情感成為思考的對象,知道由于一種反作用使那平靜逐漸消失,而相似于呈現在思考主體面前的那個情感的一種情感便逐漸產生出來,最后確實存在于心靈之中。”[16]
三.心靈的光輝——藝術理想
“美的根源在靈魂,統一的內在精神意蘊不僅表現于外在形象整體,而且也表現于其中各個部分,藝術仿佛把形象整體和各部分都化成眼睛,顯出心靈的自由與無限。”[17]絕對心靈成為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后,心靈便達到了無限與自由,這便是藝術達到理想美時,所呈現出來的心靈的無限與自由,仿佛是被上帝凝視時投射出來的圣光。“只有以神性及神性的東西為表現中心,藝術理想才會通過各門藝術及其作品展開為一個實現了的美的世界。”[18]“藝術美既不是邏輯的理念,即自發展為思維的單純因素的那種絕對觀念,也不是自然的理念,而是屬于心靈領域的,同時卻又不停留在有限心靈的知識和行動上。美的藝術的領域就是絕對心靈的領域。”[19]人的心靈是理念,是神性的承擔者,也就是說,只有表現出絕對心靈時,才顯現出了真實,藝術理想才呈現出美的狀態。
在黑格爾的美學體系中,達到絕對心靈的過程有三個階段,采取三個方式。最初級的方式是藝術,它以感性形象顯現真理;較高一級方式是宗教,它側重于膜拜者的主體虔誠心情。宗教是對藝術的否定,到了最高級的認識方式,即哲學,又否定了宗教側重主體意識的片面性,以自由思考把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都統一起來,才認識到理念。[20]因而讓心靈自身進行自由思考的哲學是最高形式。在藝術階段,要達到藝術的理想,也就是讓外在形象完善地表現內在本質。
黑格爾的這種藝術理想圍繞心靈,將絕對心靈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作為神性的東西,將一切藝術作品的最高形態都以此作衡量標準,只有達到這樣被上帝凝視而泛出圣光的狀態時,才是最美的藝術,達到最高的理想。
但是黑格爾忽視了并不是所有外在形象都能盡善盡美地表現內在本質,正如理想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始終如一的性格特征,這樣的人物在現實世界中其實是極其少數的。在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黑格爾仍然將概念凌駕于現實之上,“在概念與實在的統一里,概念仍是統治的因素”[21]。這其實是因為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局限,把主觀能動性視為理念自身的一個環節,認識客觀事物的內在概念,要依靠主觀自確定作用。因此,黑格爾的藝術理想才不容許邪惡方面的存在,從而斥責莎士比亞時代劇作中展現的罪惡,提出其藝術清洗觀。
黑格爾的心靈觀對人體心靈本身的肯定,對心靈在靜穆狀態中得到定性的思考,集中體現著他的藝術理想。他以其客觀唯心主義的視角感知萬物,認為只有生命的東西才是理念,只有理念才是真實,心靈便是在自我綜合、自我發展、自我深化的自確定運動中達到升華。他對心靈的感知也是處在他的審美主客關系,整體與部分和部分與部分,普遍性、特殊性與個體性的邏輯的思考范圍之下,對人類的靈魂與肉體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析,得到心靈的靜穆狀態的結論,一種被后世稱為“藝術典型”的藝術理想定性。在他的龐大的哲學邏輯統領下,他的心靈觀點從出生起便燭照著后世,讓后世不斷地思考、探究并發展。直到如今,也仍然是生生不息。
注釋
[1][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46.
[2]王元化.讀黑格爾《美學》筆記[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03):17-26.
[3][德]黑格爾(Hegel).美學[M] 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47.
[4][德]黑格爾(Hegel).美學[M] 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48.
[5][德]黑格爾(Hegel).美學[M] 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46.
[6]王元化.讀黑格爾《美學》筆記(續)[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04):3-15.p5.
[7][德]黑格爾(Hegel).美學[M] 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70.
[8][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83.
[9][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80.
[10][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82.
[11][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50
[12][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50
[13][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84
[14][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355
[15][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84
[16][英]拉曼·塞爾登.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M].劉向愚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5.P174
[17][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256
[18]石文穎.論黑格爾《美學》中的神性思想[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5(02):55-58.
[19][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48
[20][德]黑格爾(Hegel).美學 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1.P164
[21]王元化.讀黑格爾《美學》筆記(續)[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04):3-1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