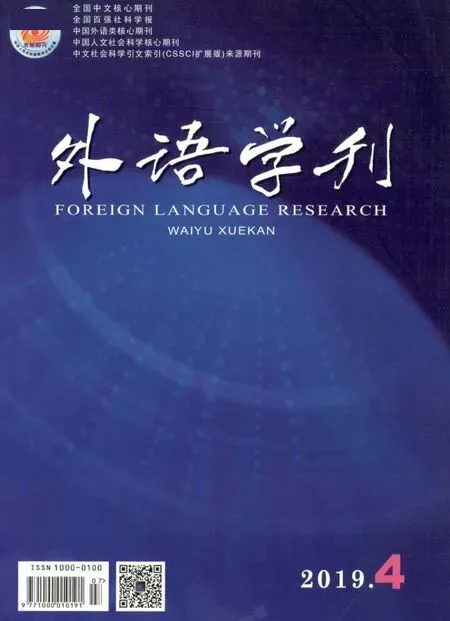譯介學與當代中國翻譯研究的新發展?
廖七一
(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 400031)
提 要:1990年前后我國的翻譯研究仍然是一種以文字轉換和翻譯技術為主導的模仿論研究范式。譯介學通過不斷質疑和反思傳統翻譯觀,逐步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并產生廣泛的學術影響。譯介學以跨學科研究的視野,賦予翻譯研究更多的文化內涵和理論品格,從而拓展中國譯學研究的視野,提升翻譯研究的學術內涵,開啟中國譯學研究新觀念,拓展翻譯研究的領域。譯介學在影響眾多翻譯研究學者的思路與方法的同時,也改變著當代中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發展方向。
1979年之后,國內翻譯研究發展的重要趨勢是從單一的語言內部研究向多學科、跨學科發展,從字詞句向社會文化發展,從形而下向形而上發展。回顧幾十年來翻譯研究的發展歷程,相信每位學者都會感覺到“譯介學”的影響和貢獻。謝天振從比較文學介入翻譯研究,對傳統的翻譯觀念和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創立譯介學的理論體系,將翻譯文學置于特定的文化時空中進行考察,翻譯研究從此走出“原地循環”的研究模式(史國強2011:22)。譯介學不僅是翻譯研究轉型的重要推動力量,拓展翻譯研究的學術空間,同時也改變中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走向。
1 譯介學生成的歷史語境
1990年前后中國的翻譯研究或沉溺于“信達雅”的詮釋與論爭,或斤斤于字當句對的轉換,主流的翻譯批評仍然集中于文本和翻譯技術層面。劉靖之主編的《翻譯論集》(1981)、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翻譯理論與翻譯技巧文集》(1983)、《翻譯通訊》編輯部編選的《翻譯研究論文集》(1984)、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王壽蘭編選的《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1989),等等,這些論文集收錄的文章絕大多數仍然是翻譯家的經驗之談和對翻譯的感性思考。雖然也有學者提到要從語言學、美學、闡釋學、哲學和文化研究等理論上觀照翻譯和翻譯活動,但仔細閱讀之后發現,真正超越文本、超越翻譯技巧、有理論深度的文章比例并不大;特別是上升到文化層面和思想層面的翻譯研究尚不多見。
1991年,南木在為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作序時稱:“淺見以為,翻譯這門事業是否已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看來還有進一步探討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簡述如次。翻譯同語言和數學近似,它既不隸屬于經濟基礎,也不隸屬于上層建筑,既非自然科學,也非社會科學,而是人類用以交流思想、傳遞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學科中研究翻譯的各個邊緣交叉部分統統都加起來,也并不足以成為認定這門學問就是一門獨立科學的充足理由”(南木1991:51)。南木的觀點帶有普遍性。他不僅否認數學和翻譯的學科地位,而且將翻譯僅僅視為“交流思想、傳遞信息的工具”,沒有區別作為實踐活動的翻譯與作為學科的翻譯研究。對于今天眾所周知的一些譯學概念,他也認為“有欠妥之處”,明確指出如“語言決定思想和世界觀,翻譯要不增、不減、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譯者是仆人等觀點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應’論等等,便值得商榷”(同上:52)。上述譯學概念當然可以商榷,但問題在于這些觀點反映出國內譯界對西方的翻譯研究少有接觸,認識還比較粗淺,局限在傳統翻譯技能的層面。
對當時翻譯研究的現狀,楊自儉有非常清醒的認識:“縱觀我國語言研究與翻譯兩個領域,應該說歷史悠久,著述甚豐,但要說出幾本有份量的理論著作卻十分困難。這是輕視理論研究的傳統所致,具體說就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對自己的實踐從理論上進行規律性的總結和理論性的闡釋,所以難有重大的理論建樹”(楊自儉1993:12)。他甚至告誡翻譯研究者“抽出部分精力對你的實際工作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和探索,這不僅能提高你的理論思維能力,而且會使你的實際工作更有成效”(同上)。
楊自儉對譯界理論意識薄弱的批評非常具有前瞻性。不可諱言的是,當時國內譯學界對翻譯學科的預期與設想還比較膚淺,翻譯界基本上是模仿論范式的一統天下。翻譯被等同于一門技藝和語言轉換;評判標準仍然局限在近百年來的信達雅;絕大多數研究成果關注的仍然是忠實再現、譯文的風格、神韻、譯者的素養和態度等形而下的層面。
2 拓展中國譯學研究的視野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譯介學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謝天振從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中被邊緣化的現象切入,質疑學界對翻譯文學的定位與評價,進而質疑傳統翻譯觀念。他認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郭箴一的《中國小說史》等都將翻譯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給以專章論述”。然而,自1949年以后,在各種新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翻譯文學卻不再享有這樣的地位,它只是附帶地被提及,沒有專門的論述,當然更沒有專門的章節。對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種大起大落的現象,迄今未見有任何解釋。也許人們根本否認“翻譯文學”的存在;也許人們從來就不認為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謝天振1990:56)。與此同時,謝天振開始追問翻譯的本質。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文學翻譯存有一種偏見,總以為翻譯只是一種純技術性的語言文字符號的轉換,只要懂一點外語,有一本外語辭典,任何人都能從事文學翻譯。這種偏見同時還影響了人們對翻譯文學家和翻譯文學的看法:前者被鄙薄為‘翻譯匠’,后者則被視作沒有獨立的自身價值”(同上 1994:176)。
謝天振認為,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系統中應該有自身的重要地位。翻譯文學“被賦予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在人類的文化生活中發揮著原作難以代替的作用”(同上:178),因而將翻譯作品的評價提升到文化意義的高度。他獨到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眼光使譯介學從一開始就具備跨學科的研究視角,超越傳統譯界狹隘的視野,提出若干年后人們才接受的翻譯的文化意義:翻譯文學“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同上:179-180)。不難發現,譯介學研究的本質不在于簡單的文字轉換,也不是簡單的文學作品的再現,它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是原文在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是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同上1999:1)。這是傳統的翻譯學者很少想過、更沒有嘗試去回答的問題。
一個理論體系的創立首先表現為對傳統觀念的質疑和批判。謝天振的“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啟迪與沖擊——論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與比較文學的學科困境”“國內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如何看待中西譯論研究的差距——兼談學術爭鳴的學風和文風”“論譯學觀念現代化”,等等,提出一系列的新觀念新思想和新的研究途徑,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方平曾高度贊賞說“面向社會成見的挑戰”意識和“寬廣的學術視野”(方平 1999:9);朱徽稱《譯介學》具有“批判傳統謬見”的現實意義(朱徽2000:59)。臺灣學者認為,閱讀謝天振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能容易地“獲得全新的觀念,乃至調整閱讀的視野”(盧康華1995:216)。譯介學對傳統的翻譯觀念形成強烈沖擊,不僅改變國內譯學界長期以來熱衷于“信達雅”的詮釋和解讀的風尚,還使國內的翻譯研究從技能的討論轉向理論的探索,從而開啟現代翻譯研究的新局面。
3 提升翻譯研究的學術內涵
由于翻譯與實踐的密切關聯以及中國譯學界實用理性的傳統,翻譯研究一直存在十分突出的重實用和實踐的傾向。強調翻譯的實踐性、強調翻譯實踐對理論概括的積極意義本無可厚非。然而,中國譯學界似乎存在根深蒂固的漠視,甚至鄙視理論探討和理論建設的傾向。謝天振就曾尖銳地指出:長期以來,我國的翻譯界有一種風氣,認為翻譯研究都是空談,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并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文章卻沒有多少出色譯作的譯者,言談之間就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風氣所及,甚至連一些相當受人尊敬的翻譯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著名的翻譯家就這樣說過:“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謝天振 2001:2)。
謝天振明確提出國內翻譯界存在3個誤區。第一個誤區是將對“怎么譯”的研究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的全部。自古以來,中國傳統譯論從“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依實出華”“五失本”“三不易”到“信達雅”“神似”“化境”,幾乎都圍繞“怎么譯”展開(同上:2-3)。對翻譯技巧的研究與探討固然重要,但翻譯技巧的探討與翻譯經驗的總結必須上升到理論層面,應該發現其中的規律。此外,理論研究必須超越“狹隘的單純語言轉換層面”,而從“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研究翻譯”(同上:3)。
第二個誤區是對翻譯理論實用主義的態度,片面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認為凡是理論都應該對指導實踐有用;否則就被譏之為“脫離實際”,是無用的“空頭理論”(同上:3)。隨著學科的發展與成熟,學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細”,必然會出現主要從事或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專家。我們應該鼓勵有興趣、有抱負的學者從事翻譯的理論研究,特別是純理論的研究。霍姆斯(J.Holmes)就曾指出,翻譯研究可分為純學術性的翻譯研究和應用性翻譯研究;翻譯理論的功能除指導具體的翻譯實踐外,還具有描述翻譯現象、解釋和揭示翻譯的規律和本質、預測翻譯可能性的功能(Holmes 2000:176)。
第三個認識誤區是國內翻譯界習慣強調“中國特色”或“自成體系”,而忽視翻譯理論的“共通性”和“普遍規律”。翻譯既然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交流活動,必然有自己的內在規律。西方翻譯研究近年來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是探索翻譯規范(translational norms)和翻譯普遍性(translational universals),強調從個體上升到整體、從局部上升到全球。堅持“中國特色”或“自成體系”顯然有悖于世界翻譯研究這個學術共同體的發展趨勢。謝天振明確指出,片面強調“中國特色”和“自成體系”可能“導致拒絕甚至排斥引進、學習和借鑒國外譯學界先進的翻譯理論;或是以‘自成體系’為借口,盲目自大自滿,于是把經驗之談人為地拔高成所謂的理論,從而取代嚴格意義上的理論探討”(謝天振 2001:4)。正如有學者所言,過分強調特色會“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坑”(張南峰2000:224)。謝天振超越當時盛行的“有無之辯”(即有沒有翻譯理論、或翻譯理論有無意義)與“中西之爭”(即西方的翻譯理論有無普適性,是否適用于中國的翻譯實際),突破民族本位的局限。
謝天振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翻譯研究都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理論,用巴恩斯通的觀點來看,所有的那些研究“只是應用于文學的翻譯原則與實踐史罷了”(謝天振2001:5)。這也是許多翻譯理論家所謂的“前科學”(pre?scientific)階段。其后,西方翻譯理論有了長足的發展,研究領域也大大擴展,譯作的發起人、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等都成為研究的對象。不僅討論文本之間的忠實與等值關系,而且注意到譯作在“新的文化語境里的傳播與接受,注意到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傳遞行為的最終目的和效果,還注意到譯者在這整個翻譯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同上:4)。“把翻譯研究的重點放在翻譯的結果、功能和體系上,對制約和決定翻譯成果和翻譯接受的因素、對翻譯與各種譯本類型之間的關系、翻譯在特定民族或國別文學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譯對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影響所起的作用給予特別的關注。”(同上:4)翻譯理論的建構和翻譯研究的發展要求一部分學者“盡快擺脫‘匠人之見’”而成為翻譯研究的“建筑大師”(同上2003:256)。謝天振對“術”與“學”的關系的論述振聾發聵;對改變尋章摘句式的批評風氣,無疑有強烈的針對性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4 開啟中國譯學新觀念
2004年,《中國翻譯》刊發一篇編者按語,稱中國翻譯研究面臨的困境是“窄”與“薄”。“窄”主要指“研究的路子窄,體現在創新意識不夠,走別人的老路,缺乏理論框架與體系的突破”(編者2004:1);“薄”則指“理論底子薄,跨學科知識嚴重欠缺”,強調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方法和新的突破”。編者按認為,“學術創新貴在有探索意識和勇氣,選題沒有魄力,沒有創意,只求保險,學術建樹就無從談起”(編者 2004:6)。在編者按語之后刊發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謝天振的“論譯學觀念的現代化”(謝天振 2004:7)。該文不僅是從研究觀念上對譯學發展進行論證,突出地表現謝天振跨學科和理論建構的學術意識,更重要的是對學術創新的回應。謝天振認為,“翻譯所處的文化語境已經發生變化,翻譯研究的內容也已經發生變化,然而我們的譯學觀念卻沒有變化,我們的翻譯研究者隊伍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我們不少人的譯學觀念仍然停留在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以前”(同上:7-8)。也就是說“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個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文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中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在譯入語社會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著有時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同上:8)。謝天振還認為,翻譯的文化語境也已經從口語交往階段、文字翻譯階段發展到今天的文化翻譯階段,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翻譯研究的走向。不了解世界范圍內譯學研究的趨勢與動態,“再不迅速實現譯學觀念的現代化轉向”,無疑會成為我國譯學理論建設和翻譯學科建設的“瓶頸口”,“勢必阻滯中國譯學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對我們整個翻譯事業帶來不利的影響”(同上)。這無疑對翻譯研究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應該指出,譯介學的傳播與影響推動翻譯研究的理論建構和學派創新。譯介學理論、翻譯文學和翻譯文學史的概念體系,在大陸、港臺和海外都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賈植芳就曾對謝天振的《譯介學》給予積極肯定,稱其“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大量豐富的實例,把翻譯文學作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進行分析、評述,從而得出與文學史的編寫、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關系的重大結論……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新層面,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賈植芳1999:4)。可見,稱《譯介學》在中國翻譯研究中具有原創性,絕非溢美之詞。
如果從現代譯學發展的眼光來分析霍姆斯劃時代的文獻《翻譯研究的名與實》,我們會發現,翻譯作品的傳播、接受和影響似乎并沒有在其中占有應有的地位。當然,我們不能苛求霍姆斯在三十多年以前就預見到翻譯研究今天的發展。但時至今日,“譯介學”仍無法找到相應的英文術語,這讓謝天振面臨杜撰術語Medio?translatology的尷尬。西方至今仍然沒有與譯介學理論相關、較為系統和完整的專著問世。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開創嶄新學術領域、建構全新學派或理論所面臨的艱難。
在新近出版的《譯介學導論》中,謝天振闡述譯介學對翻譯研究“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謝天振2007:8)。首先,譯介學擴大并深化對翻譯和翻譯研究的認識;其次,創造性叛逆的研究肯定并提高文學翻譯的價值和文學翻譯家的地位;第三,界定、論證翻譯文學的歸屬問題;第四,譯介學對編寫翻譯文學史的思考展現出廣闊的學術空間(謝天振2007:13-14)。從當前國內學者翻譯研究的選題來看,我們就會發現此言不虛。許多學者從“創造性叛逆”“文化誤讀”等術語體系中得到靈感、受到啟發。這些術語已成為翻譯界流通最為廣泛、使用頻率最高的核心術語之一,《譯介學》也成為國內翻譯研究參考最多的中文文獻。有學者統計,“《譯介學》自1999年問世以來,至今已連續印刷4次……被引用率在國內翻譯界和比較文學界都名列前茅”,“CSSCI刊物引證的次數每年就都超過18次”。國家社科項目課題指南、國家“十一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06-2010)也都“把譯介學列為重點研究課題之一”(蔡韻韻 2011:575)。
5 拓展翻譯研究的領域
譯介學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完善與豐富,逐漸成為翻譯研究的一種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指導,不斷地被譯界應用于新的研究領域:翻譯史的編寫和文化典籍的外譯。
首先,譯介學理論被成功地應用于文學翻譯史的編寫。有學者指出,謝天振首次“分析翻譯文學的性質、歸屬和地位”,并“從理論上探討撰寫‘翻譯文學史’的方法論問題”(查明建2000:127)。眾所周知,國內已經出版過不少的翻譯文學史或文學翻譯史,僅在2005年就出版過4部翻譯史和3部翻譯家專論。但從整體上看,“翻譯史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文獻和史料意義”(廖七一2007:41);這也是翻譯史編寫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編者要么缺少宏觀的理論框架,無法從浩瀚的史料中發現或概括出翻譯發展的脈絡和規律,要么缺少對所涉及的史料有理論深度的梳理,某些翻譯史幾乎成了翻譯事件流水賬。謝天振認為:以敘述文學翻譯事件為主的“翻譯文學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文學史,而是文學翻譯史。文學翻譯史以翻譯事件為核心,關注的是翻譯事件和歷史過程歷時性的線索。而翻譯文學史不僅注重歷時性的翻譯活動,更關注翻譯事件發生的文化空間、譯者翻譯行為的文學文化目的,以及進入中國文學視野的外國作家及其作品。翻譯文學史將翻譯文學納入特定時代的文化時空進行考察,闡釋文學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形態、達到某種文化目的的翻譯上的處理以及翻譯的效果等,探討翻譯文學與民族文學在特定時代的關系和意義。(謝天振 2007:162-163)
正是按照這一指導思想,謝天振和查明建主編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具有典范的意義(謝天振 查明建2004)。這是因為,第一,這部翻譯文學史的編寫是對譯介學理論系統的史學嘗試,闡明“翻譯文學”與“文學翻譯”的區別,分析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本土文學之間的關系、翻譯文學與本土文化多元系統的關系,回答翻譯文學史的性質、學科地位和構成要素等基本問題。第二,這本翻譯文學史成功地應用“線”與“面”相結合的編排方式,在客觀描述翻譯文學事件發展線索的同時,強調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系統中的傳播、接受與影響。第三,承認和肯定翻譯家、文學社團和“披上了中國外衣的外國作家”的主體地位。第四,將翻譯文學史“看成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學交流史、文學關系史和文學影響史”(耿強2007:86)。這一嘗試不僅體現出謝天振“獨有的闡釋學意識”和“史家理論上的前見”(同上:85),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學界對翻譯文學的認識、評價與定位,確立了翻譯史編寫的新范例。
在當下“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熱潮中,譯介學成為翻譯界一種理論指導和思想武器。其實早在2008年謝天振就開始關注并發表有關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文章。通過這些著述,謝天振將譯介學的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對典籍外譯的本質、意義、途徑、特征、方法和認識誤區等進行系統和深入的闡述與論證。謝天振認為,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是一項跨文化工程,我們“一定要跳出簡單的兩種語言文字轉換的層面,一定要把翻譯的問題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會背景之下,去審視、去思考”,“才能深刻認識翻譯與語言文字轉換背后的諸多因素之間錯綜復雜的微妙關系,我們才有可能抓住‘中國文學、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謝天振2013:47)。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譯入”與“譯出”的差異,不能將照顧“接受群體的閱讀習慣和審美趣味”視為“對西方讀者的曲意奉迎”,要了解主流文化向非主流文化流動的譯介基本規律;重視文化交際中的“時間差”和“語言差”(同上 2014:5-8)。
通過梳理佛經翻譯的歷史,謝天振強調要“摒棄‘以我為中心’的思想”,認清“適應”和“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同上:8),“發現外譯文化與對象國文化之間的共同點,構建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親緣關系”(同上:10),“讓中國的專家、學者、譯者參與到英語國家對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活動中去”(同上:8)。可以說,謝天振從譯介學原理出發,不僅敏銳地發現當下中國文學文化外譯中的偏頗與局限,更從理論上分析了產生失誤的原因,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具體可行的譯介策略。
6 結束語
謝天振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1992年在《外國語》上發表《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1994年在臺灣出版《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1999年出版《譯介學》,2007年出版《譯介學導論》。最近幾年來,更是接連推出《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2011)、《翻譯研究新視野》(2014)、《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2014)、《超越文本 超越翻譯》(2014)等專著和個人論文集,對譯介學理論進行進一步的豐富與完善。現在譯介學已經成為國內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法國的“創造性叛逆”等譯介學思想也曾傳入日本,并較中國為早,但“卻沒有枝繁葉茂,至今尚無‘學名’;‘創造性叛逆’這一核心概念,也未能有效普及”(高寧 2016:142)。而在中國,譯介學卻“生根發芽,迅速成長”,成為“中國當代譯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引起整個人文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同上)。究其原因,有學者認為,“日本缺乏像謝天振這樣致力于譯介學研究的大家”(同上),應該說此言不虛。在過去的20多年中,譯介學的觀念引發多次論爭;有人給予高度肯定和支持,但也有人質疑,甚至反對;至今仍有不同的解讀和理解(王向遠2017:62-69)。謝天振曾比較系統地回應這些質疑,并指出若干對譯介學的誤讀(謝天振2012:34-36)。不可否認的是,譯介學及其引發的種種論爭改變了學界對許多翻譯核心概念的認識與界定,擴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促進了翻譯研究的理論提升。由于謝天振身兼比較文學學者、翻譯家、翻譯理論家、翻譯教育家和翻譯學科的規劃者、組織者和建設者等多重學術身份,其影響遠非單純的翻譯家所能相比。他將翻譯研究與批評的“目光引向翻譯的現實,關注翻譯在譯入語語境中的地位、傳播、作用、影響、意義等問題”,“突顯并肯定文學翻譯家的勞動價值”,并將關注的重心“從原文文化轉向譯入語文化”(謝天振 2012:38-39)。可以說,譯介學在影響眾多翻譯研究學者的思路與方法的同時,也改變著當代中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