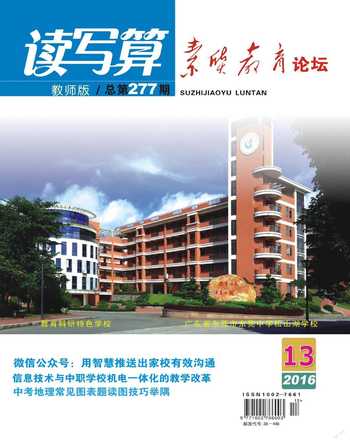小學(xué)數(shù)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教師如何有效提問
王仕靜
中圖分類號:G623.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13-0053-01
有效提問是小學(xué)數(shù)學(xué)課堂教學(xué)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效提問是組織課堂教學(xu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教學(xué)內(nèi)容得以實(shí)施的媒介,是教師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參與的有效手段,是溝通教學(xué)信息、聯(lián)系師生思維活動的紐帶,是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一種交流方式。也是溝通教師、教材、學(xué)生之間聯(lián)系的主渠道和“鋪路石”,更是提高教學(xué)效率的基礎(chǔ)。所以,精心設(shè)計(jì)課堂有效提問是提高數(shù)學(xué)課堂效率的一條重要途徑。
一、有效提問要選擇好問題
數(shù)學(xué)來源于生活,又運(yùn)用于生活,則數(shù)學(xué)課堂的提問要符合學(xué)生的認(rèn)知發(fā)展水平和實(shí)際生活經(jīng)驗(yàn)。不要過難或過易,要因人施問。過難,學(xué)生覺得高不可攀,喪失信心。過易,學(xué)生會認(rèn)為“小菜一碟”,難于引起學(xué)生的思考,久而久之,學(xué)生的思維會變得懶惰。所以教師設(shè)置問題時,要關(guān)注學(xué)生的“最近發(fā)展區(qū)”,所設(shè)置的問題要有針對性,使學(xué)生通過思考后,就能得到答案,這樣,才能培養(yǎng)學(xué)生積極思考的好習(xí)慣,才能充分調(diào)動學(xué)生思考的積極性,并使學(xué)生體驗(yàn)到成功的喜悅,從而進(jìn)一步培養(yǎng)學(xué)生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的興趣。
二、有效提問要把握時機(jī)
1.從教材內(nèi)容的角度來說,提問應(yīng)選擇的最佳時機(jī)是教材的關(guān)鍵處、教材的疑難處、新舊知識的結(jié)合處、教材的精華處、教材的深奧處。學(xué)生學(xué)習(xí)新知識都有一定的難度,新知識的疑難之處就是教材的深奧之處。這樣的地方學(xué)生理解困難,教師有計(jì)劃地精心設(shè)計(jì)系列問題,有利于減緩坡度,突破難點(diǎn)。
2.從學(xué)生角度來說,最佳提問時機(jī)為:
(1)當(dāng)學(xué)生的思維困于一個小天地而無法突圍時,教師要精心設(shè)問,引導(dǎo)學(xué)生沖出困境,從新的角度思考問題,找到答案。
(2)當(dāng)學(xué)生受舊知識的影響,無法順利實(shí)現(xiàn)知識遷移時,要精心設(shè)問,幫助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知識遷移。
(3)當(dāng)學(xué)生疑惑不解時,要恰當(dāng)設(shè)問,幫助學(xué)生解惑,弄清問題,理解新知識。
(4)當(dāng)學(xué)生有所領(lǐng)悟,心情振奮,躍躍欲試時,要通過設(shè)問,給學(xué)生表現(xiàn)自己的機(jī)會,使他們品嘗成功的喜悅,激發(fā)他們的學(xué)習(xí)熱情。
(5)當(dāng)學(xué)生胡思亂想、做小動作、精力分散時,要通過設(shè)問,引起學(xué)生注意,把他們的精力引導(dǎo)到學(xué)習(xí)上來。
三、有效提問要留給學(xué)生探索的思維空間
課堂提問還得給學(xué)生留有一定的探索思維空間。例如,在教學(xué)《分?jǐn)?shù)與小數(shù)的互化》時,在學(xué)生經(jīng)歷了借助計(jì)算器對自己喜歡的分?jǐn)?shù)化成小數(shù)時,就可以這樣向?qū)W生提出:面對分?jǐn)?shù)化成小數(shù)的兩種結(jié)果,有限小數(shù)和無限小數(shù),同學(xué)們會有什么疑問產(chǎn)生呢?讓同學(xué)們大膽猜猜看,一個分?jǐn)?shù)能否化成有限小數(shù),與分?jǐn)?shù)的哪部分有關(guān)?學(xué)生們紛紛進(jìn)行猜測:有的認(rèn)為與分子有關(guān),有的認(rèn)為與分母有關(guān),還有的認(rèn)為與分子、分母都有關(guān)。“一個分?jǐn)?shù)能否化成有限小數(shù),與分?jǐn)?shù)的哪部分有關(guān)?”在這兒由一個問題引發(fā)了學(xué)生的許多猜想,問題新穎,學(xué)生感覺也很新奇,從而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
四、有效提問要面向全體,尊重學(xué)生的個別差異
提問活動是全體學(xué)生同教師的信息交流,提問要面向全體學(xué)生,讓每一個學(xué)生都有答問的機(jī)會。例如,對優(yōu)等生提問有一定難度的問題,如理解性的、發(fā)散性的、綜合性的問題,激勵其鉆研;中等生則以一般性問題,助其掌握、鞏固知識、提高學(xué)趣,培養(yǎng)良好的思維情緒;而后進(jìn)生宜問一些淺顯的,如簡單判斷性、敘述性的、比較直觀的問題,并設(shè)法創(chuàng)造條件啟發(fā)其思考,使其在成功中勃發(fā)思維的激情。
五、有效提問問題應(yīng)少而精,促進(jìn)學(xué)生思維的發(fā)展
課堂有效提問是小學(xué)數(shù)學(xué)教學(xué)中進(jìn)行啟發(fā)式教學(xué)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有效教學(xué)的核心,也是教師們經(jīng)常運(yùn)用的教學(xué)手段。但是,也經(jīng)常在課堂教學(xué)中出現(xiàn)低效的、重復(fù)的提問,以問代講形成滿堂問等現(xiàn)象還經(jīng)常見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課堂教學(xué)效益的提高。所以我們要盡量了解學(xué)生的思考過程,減少問題的量,努力提高問題的質(zhì)量。通常可以設(shè)計(jì)、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你是怎樣想的?為什么要這樣做?你的理由是什么?與其他比較,有什么相同?你要怎樣改呢?你還有更簡便的方法嗎?哪些正確,哪些還有問題?像這樣的問題應(yīng)該怎樣解決呢?等等,只要我們引導(dǎo)得法,就能達(dá)到問得好、問得精、問得新、問得有價值的目的。
六、有效提問要以問引問,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力
課堂中以問引問能激發(fā)學(xué)生的探究欲望,讓學(xué)生用自己喜歡的方法把問題轉(zhuǎn)化加以解決,又會產(chǎn)生出新的問題。當(dāng)學(xué)生提出問題時,老師不急于回答而是又要把問題踢回給學(xué)生,這樣能引發(fā)學(xué)生深入的思考,然后通過實(shí)際操作、討論、交流和分析,讓學(xué)生自己解決新的問題,以問引問,來促進(jìn)學(xué)生的思維,使學(xué)生積極參與到課堂學(xué)習(xí)中來,既落實(shí)學(xué)生的主體地位,又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